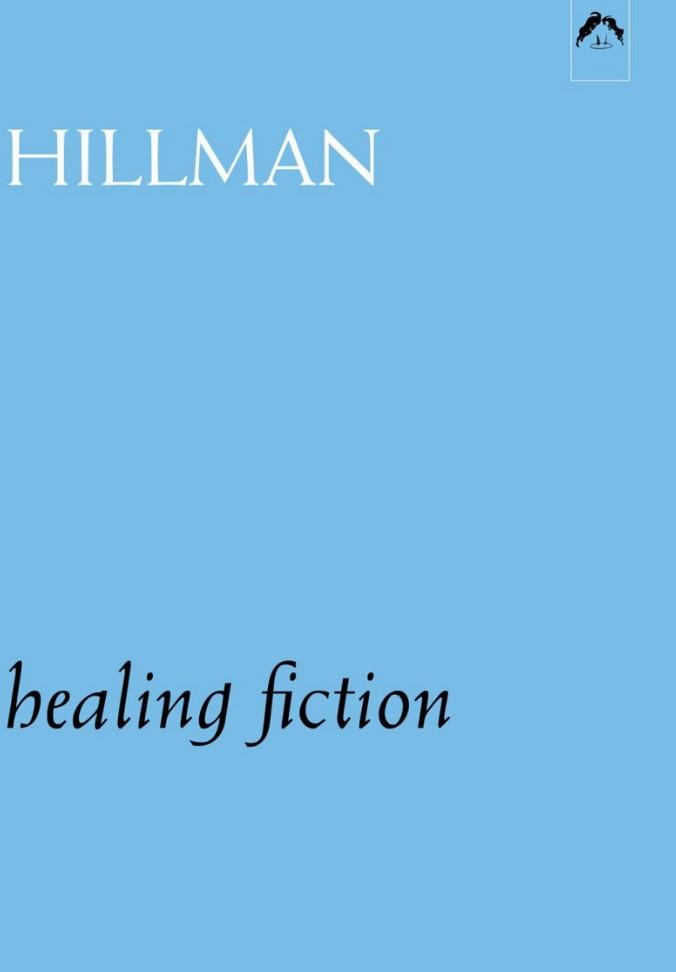版权
Healing Fiction_ On Freud, Jung, Adler
版权所有 © 1983,詹姆斯·希尔曼 保留所有权利。
ISBN 978-0-88214-597-6(Kindle 版本 2012,v. 2.0)
由 Spring Publications, Inc. 出版 康涅狄格州普特南 网址: www.springpublications.com
最初于 1983 年由 Station Hill Press 在纽约州巴里敦出版。
《案例史的虚构:一个循环》是应詹姆斯·B·威金斯的要求撰写,并发表在他编辑的《宗教作为故事》(纽约:Harper & Row,论坛书籍,1975)中。
《图像的潘达EMONIUM:C. G. 荣格对‘认识你自己’的贡献》首次在托马斯·卡帕辛卡斯组织的圣母大学会议(1975年4月)上提出,以纪念荣格诞辰百年;该文章最初以英文发表在《新卢加诺评论》第三卷第3/4期(1970年)第35-45页,并由已故的菲利普·沃尔夫-温德格译成德文,收录于阿道夫·波特曼和鲁道夫·里斯玛编辑的《埃拉诺斯年鉴》第44卷(1975年),莱顿:Brill出版社,1977年。
《心理治疗的自卑情结》首次出现在阿道夫·波特曼和鲁道夫·里斯玛编辑的《埃拉诺斯年鉴》第46卷(1977年),法兰克福:Insel出版社,1981年。
这三篇文章都为本书出版进行了修订和扩展。在此感谢詹姆斯·威金斯、托马斯·卡帕辛卡斯、詹姆斯·菲茨西蒙斯、菲利普·沃尔夫-温德格和鲁道夫·里斯玛对各章节原版的帮助,以及米歇尔·马丁对最终版本的帮助。
詹姆斯·希尔曼 《治愈的虚构》 SPRING PUBLICATIONS, INC. 康涅狄格州普特南
案例史的虚构: 与弗洛伊德的一轮对话 虚构的弗洛伊德 1934年,意大利实用主义哲学家和作家乔瓦尼·帕皮尼(Giovanni Papini)发表了一篇与弗洛伊德的奇特访谈。这篇访谈以直接对话的形式呈现,仿佛弗洛伊德在私下里坦白了他工作的全部内容。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话:
每个人都认为我坚持我的工作具有科学性,并且我的主要目标在于治愈心理疾病。这是一个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严重误解,而我无法纠正它。我成为科学家是出于必要,而非自愿。实际上,我本质上是一名艺术家……这一点有不可辩驳的证据:在所有引入精神分析的国家中,精神分析被作家和艺术家比医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事实上,我的书籍更像是想象的作品,而不是病理学的论著……我通过间接的方式赢得了我的命运,并实现了我的梦想:成为一名文学家,尽管在外表上仍然是一名医生。所有的伟大科学家都有幻想的成分,但没有人像我一样将现代文学潮流带来的灵感转化为科学理论。在精神分析中,你可以找到三种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文学流派——海涅、左拉和马拉美在我的作品中融合在一起,这些都受到我的老导师歌德的庇护。[1]
在这次访谈中,弗洛伊德揭示了更多关于他的导师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治疗实际操作的内容,比那些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详尽阐述还要多。精神分析是一种在创作领域内的想象力叙述工作,这简单地意味着“创造”,并且我认为这是通过想象力将思想转化为语言的过程。我们的工作更具体地属于创作修辞学,即通过语言进行想象的说服力,一种在说话和倾听、写作和阅读中的艺术技巧。
通过将深层心理学置于诗歌和修辞的宇宙中,我承担了我在1972年特里讲座中所做出的一个转变的后果。[2] 在那里,我尝试了一种既是灵魂心理学也是想象力心理学的心理学,这种心理学的出发点既不是大脑生理学、结构语言学,也不是行为分析,而是想象力的过程。也就是说:一种假设心灵具有诗意基础的心理学。任何关于这种心灵的案例史都必须是对这一诗意基础的想象力表达,是一种想象力的创造,一种诗意的虚构,正如帕皮尼所说,它伪装成医学科学的语言,无论是讲述者在他的故事中还是听众在他的记录中。
在著名的1905年出版物《一个歇斯底里病例分析的片段》[3](Dora的故事)的序言中,弗洛伊德写道:“我意识到——至少在这个城市——有许多医生选择不将这类病例史视为神经症的心理病理学贡献,而是当作一本供他们私人娱乐的‘秘史’。”他还想象到“未经授权”的“非医学读者”会转向这个故事。
早在那时,“读者”就已经出现在弗洛伊德——作为作者——的幻想中。在他的后续工作中,我们常常遇到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侦探小说风格的对读者的呼吁,提醒读者之前几页提到的内容,或者警告读者某个观点值得记住,因为它会在后面再次出现,或者表现出对读者的疑惑、困惑、甚至震惊的关注——也许是因为某件事情被大胆直白地揭露。
弗洛伊德对他在发表Dora病例时采用的复杂伪装秘密的联想并不是针对性心理病理学(克雷夫特-宾格并没有对读者或病例表现出这种关心),也不是针对家庭医疗顾问(蒂索特在其关于手淫的可怕警告中提供了许多案例),也不是针对法医精神病学,或者是带有裸体男女全身正面图并用黑色矩形遮住眼睛的医学病历(仿佛他们看不见我们,我们也看不见他们)。
不,弗洛伊德的联想是与文学有关的,为此他总是使用一个表示情感重要性的外来词——roman à clef,意为“一部由作者伪装的真实人物和事件的作品”。这不是正是弗洛伊德所做的吗?因此,非医学读者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他的脑海,因为在弗洛伊德的心中,他已经把自己与小说作家联系在一起。授权和医学读者、未经授权和文学读者这两种类型的读者指的是弗洛伊德自己幻想中的两个形象。
为什么弗洛伊德在试图撰写心理案例报告时陷入了医学与文学之间的纠结?他是否在努力寻找一种没有现成模式的写作形式?他的思维在科学和人文学科两大传统之间来回摇摆,这种摇摆不得不发生——不仅仅是因为医学是对他文学天职的神秘伪装,最终被帕皮尼讽刺地、托马斯·曼兄弟般地、官方授予歌德文学奖所承认——更可能的是,这种困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弗洛伊德正在发明一种 更可能的是,这种困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弗洛伊德正在发明一种新的体裁,这种体裁将承载他的新视野进入世界。除非能找到一种合适的“叙述”形式,赋予其医学实证的说服力(即使不是实质),否则他的精神分析在医学界无法取得进一步进展。弗洛伊德将两者纠缠在一起,因为他同时从事着虚构和案例史的写作;自那时以来,在我们这个领域的历史上,它们变得不可分割;我们的案例史实际上是一种书写虚构的方式。
对“Dora”的分析——作为我们领域中的第一部重要心理案例史——就像它呈现为一种医疗技术一样,也吸引了我们对其文学技巧的关注。我所说的“技巧”是指“风格作为一种刻意的程序,工艺性”[4];我遵循T. S. 艾略特对技巧的看法,他认为作家更像是冷静的科学家,而不是衣衫褴褛的疯子。而正是这个关于技巧的文学问题——冷静或凌乱——使弗洛伊德与斯特克尔、赖希和格罗斯疏远,反而让他更接近亚伯拉罕和琼斯。
案例史的虚构:一个循环 1934年帕皮尼的访谈揭示了什么? 1934年,意大利实用主义哲学家和作家乔瓦尼·帕皮尼发表了一篇与弗洛伊德的奇特访谈。这篇访谈以直接对话的形式呈现,仿佛弗洛伊德在私下里坦白了他工作的全部内容。通过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到弗洛伊德对自己工作性质的深刻反思,尤其是他对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复杂关系的理解。
弗洛伊德的自我定位 在这段对话中,弗洛伊德强调自己本质上是一名艺术家,而不是出于自愿的科学家。他认为自己的书籍更像文学作品而非病理学论著,并指出精神分析在文学和艺术圈中比在医学界得到了更好的理解和应用。这表明弗洛伊德意识到自己作品中的文学特质,并将其视为表达内心世界的有效方式。
精神分析的文学特质 弗洛伊德提到,精神分析融合了十九世纪三大文学流派——海涅、左拉和马拉美——并在歌德的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这一观点揭示了精神分析不仅仅是科学理论的应用,更是文学和想象力的结合。因此,精神分析可以被视为一种“创造”,即通过语言将内心的想象转化为文字。
案例史的双重性 弗洛伊德在其著名的1905年出版物《一个歇斯底里病例分析的片段》(Dora的故事)的序言中,提到了读者的不同反应。他意识到有些医生将此类案例史视为供私人娱乐的“秘史”,而非神经症的心理病理学贡献。这反映了弗洛伊德对不同读者群体的敏感度,以及他在写作时如何平衡医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
文学技巧的重要性 在对“Dora”的分析中,弗洛伊德不仅展示了医学技术,还展示了文学技巧。他使用“技巧”一词来指代“风格作为一种刻意的程序,工艺性”。这种技巧使得精神分析既具有科学的严谨性,又充满了文学的艺术性。正如T. S. 艾略特所认为的那样,作家可以像冷静的科学家一样进行创作,而不是表现得像个狂人。这种文学技巧的问题——冷静或凌乱——使得弗洛伊德与某些同行如斯特克尔、赖希和格罗斯保持距离,反而让他更接近亚伯拉罕和琼斯。
通过这些讨论,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弗洛伊德的工作及其对精神分析的影响。弗洛伊德的作品不仅是科学的探索,也是文学的表达,这种双重性在他对案例史的处理中尤为明显。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学科,不仅依赖于严格的科学方法,还受益于丰富的文学想象力。
技巧也指形式价值 技巧还涉及到形式价值。看看弗洛伊德在Dora案例史中的形式。首先是故事本身。E. M. 福斯特说:“小说的基础是故事,而故事是一系列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5];我们阅读故事是为了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福斯特称之为简单的原始好奇心。弗洛伊德在这个层面上与我们相遇——悬念、暗示、隐藏和一个引发好奇的场景设置,即临床咨询(他这个案例的第一部分称为“临床图像”)。在这里,我们被另一种叙事技巧所吸引,这种技巧我们在约瑟夫·康拉德的作品中也能找到:故事的不连贯性,需要作者(和读者)将其拼凑起来,并且主要人物(Dora)同时在两个层面上讲述故事。
弗洛伊德使用了其他手法:背景中的谦逊叙述者与其面前揭示的重大事件相比显得微不足道;随着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逐步深入发现;一开始就宣布的时间限制,“只有三个月”;序言中对即将揭示的性细节的诱惑(“我仅仅为自己保留妇科医生的权利”,带有年轻女孩与医生的色情回响);然后是对医学界的敏感道歉:其他专科医生无法检查结果;不是逐字记录,而是事后凭记忆写成;“因省略技术而产生的简化”(即他在治疗案例中实际做了什么)。这些道歉绝非小事!因为在这里,尽管展示了他对实证主义要求的意识,我们的作者还是避开了那种他在脑病理学和可卡因实验早期工作中已经非常熟练的写作方法。作为科学中的实证证据,病例史必须提供一些公共验证的手段。它不能仅仅是记忆中的记录,除非它只被视为逸事回忆:而且整个治疗技术——弗洛伊德的主要遗漏——必须属于记录的一部分。我们期望确切了解医生做了什么。弗洛伊德只模糊地告诉我们一部分。
当着手展示“神经症障碍的内在结构”(这是他对这个案例的意图)时,弗洛伊德可以选择维萨里或巴尔扎克的方式[6],即解剖学家或道德家,前者揭示身体病态的内在结构,后者揭示心理、道德或心理病态的内在结构。他可以从外部或内部来处理这个问题,或者如法国作家阿兰所说:
人类有两面,适合历史和虚构。所有可观测的人类行为都属于历史领域。但他的浪漫一面(作为虚构的小说)包括“纯粹的情感,即那些由于礼貌或羞耻而不便提及的梦想、快乐、悲伤和自省”;表达这一方面的人性是小说的主要功能之一[7]。
阿兰提到礼貌和羞耻,弗洛伊德写道:“患者……保留了一部分……因为他们还没有克服他们的怯懦和羞耻感。”[8] 弗洛伊德的案例史充满了虚构的元素;它们表达了人性的虚构面,其浪漫的一面。
在历史与虚构、外部与内部之间的双重困境中,弗洛伊德巧妙地达成了妥协,形成了他的案例风格和我们新的心理治疗写作体裁。他给了我们“纯粹的情感……梦想……自省”,但他从外部做这件事,作为病态结构的医学病理学家,这是他的第一个职业。我们没有像读小说一样进入案例的内部,同情Dora,而是保持在外面,揭露组织,与弗洛伊德一起分析。作为读者,我们认同主要人物,但不是她的主观感受和痛苦。我们更认同“神经症障碍的内在结构”,即她所体现的概念,性压抑及其动力。因为我们的兴趣不知不觉地从揭示一个主体转移到展示一个客体,从研究性格到分析性格,并通过性格展示作者的倾向目标。(因此,他告诉我们的更多是关于她的梦境和材料,而不是她个人的情况。)
我们可能被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吸引,并被作者的技巧所吸引,但这并不是弗洛伊德所关注的故事,而是情节——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一点。
此外,故事的情节——发现病态因素及其治愈过程——与患者的个性几乎没有关系。高戏剧性的行动独立于她的特定个性展开:她是否有勇气?她是否小气?她的良心本质是什么?她的致命弱点在哪里?她在危机中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塑造故事的发展?尽管看起来很紧张,分析的行动并不受她的影响。故事可以同样继续下去,无论谁是患者。患者和医生都可以被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十年的另一位患者和另一位医生取代——实际上就是这样,因为这就是作为科学方法的心理分析。案例只是一个例证,所以人物不能也不应该影响其行动。不是人物和故事,也不是行动,揭示了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是心理动力学的情节。人物是普遍情节中的事件,因此相对次要。
技巧也指形式价值(续) 此外,故事的情节——发现病态因素及其治愈过程——与患者的个性几乎没有关系。高戏剧性的行动独立于她的特定个性展开:她是否有勇气?她是否小气?她的良心本质是什么?她的致命弱点在哪里?她在危机中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塑造故事的发展?尽管看似紧张激烈,分析的行动并不受患者的影响。故事可以同样继续下去,无论谁是患者。患者和医生都可以被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十年的另一位患者和另一位医生取代——实际上就是这样,因为这就是作为科学方法的心理分析。案例只是一个例证,所以人物不能也不应该影响其行动。不是人物和故事,也不是行动,揭示了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是心理动力学的情节。人物是普遍情节中的事件,因此相对次要。
在弗洛伊德的写作中,读者的兴趣逐渐从对个体的具体描述转向对某种普遍机制的理解。我们更多地关注的是通过Dora这一角色所体现的心理动力学原理,而不是她个人的经历或感受。这种转变使得案例史不仅仅是对某个具体病例的记录,而是一种展示作者理论观点的工具。
弗洛伊德的叙事策略 弗洛伊德的叙事策略不仅仅是为了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更是为了引导读者进入一种特定的思考模式。他使用了一系列技巧来达到这个目的:
悬念与暗示:通过设置悬念和暗示,弗洛伊德激发了读者的好奇心。例如,在《Dora》案例的第一部分“临床图像”中,他通过临床咨询的场景设置,逐步揭示信息,使读者不断猜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多层叙述:Dora的故事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个是显性的外部事件,另一个是隐性的内心活动。这种双层结构需要读者自己去拼凑完整的图景,正如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中常见的那样。 谦逊叙述者:弗洛伊德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谦逊的背景叙述者,与他面前揭示的重大事件相比显得微不足道。这种方式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同时也让读者更加专注于内容本身。 时间限制:在案例开始时就宣布的时间限制(如“只有三个月”),给故事增加了一种紧迫感,同时也暗示了治疗的有限性。 预示与道歉:在序言中,弗洛伊德预示了即将揭示的性细节,并以一种带有色情回响的方式提到“妇科医生的权利”。同时,他对医学界的敏感道歉,表明了他在写作时的复杂心态。这些道歉不仅是对实证主义要求的回应,也显示了他对传统医学写作方式的偏离。 省略技术细节:弗洛伊德省略了具体的治疗技术细节,这使得案例史更像是一个文学作品,而非严格的科学记录。这种做法不仅增加了故事的神秘感,也让读者更关注心理动力学的情节。 案例史的双重性质 弗洛伊德的案例史具有双重性质,既是医学文献,也是文学作品。他巧妙地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平衡,创造了一种新的写作体裁。他展示了“纯粹的情感……梦想……自省”,但却是从外部视角出发,作为病态结构的医学病理学家。读者没有深入到个案的内部,同情Dora,而是保持在外面,揭露组织,与弗洛伊德一起分析。
这种写作方式使得读者能够认同主要人物,但不是她的主观感受和痛苦。相反,读者更认同“神经症障碍的内在结构”,即她所体现的概念,性压抑及其动力。我们的兴趣不知不觉地从揭示一个主体转移到展示一个客体,从研究性格到分析性格,并通过性格展示作者的倾向目标。因此,弗洛伊德的案例史不仅仅是对某一具体病例的记录,更是一种展示作者理论观点的工具。
心理动力学的情节 最终,弗洛伊德的案例史强调的是心理动力学的情节,而不是具体的故事情节或人物行动。人物在故事中只是普遍情节中的事件,因此相对次要。这种写作风格不仅揭示了弗洛伊德对心理分析的独特理解,也为后来的心理治疗写作提供了新的范式。
通过这种复杂的叙事手法,弗洛伊德不仅展示了他对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的深刻见解,还创造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作品。他的案例史不仅是对具体病例的记录,更是一种探索人性深处的心理动力学的尝试。这种双重性质使得弗洛伊德的作品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文学价值。
妥协是弗洛伊德的公式 妥协是弗洛伊德对梦的本质、自我、症状的公式,也是他构建自己梦理论的方式——通过对当时领域内相互冲突的理论进行妥协性整合[9]。正因为他的案例写作是一种妥协,我们不能简单地跟随那些认为弗洛伊德“本质上是一名医生”并拥有文学天赋的人,或认为他是“本质上是一名作家”而恰好出现在医学领域的人。他的风格成功之处在于面具,正如托马斯·曼反复强调的那样,这个面具对于作者来说至关重要,它使得作者能够在隐藏自己的同时揭示自己。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种双重运动最好理解为:它是无意识的文学表达(小说家的风格)与有意识的物理医学类比(妇科医生的比喻)之间的妥协。显性的材料是医学的,但潜意识的意图——需要通过医疗实证方法的转换和压制来实现——却是诗意艺术的。他的案例史是成功的症状形成,经过升华和转换,成为一种新的叙事体裁;它们就像梦一样:艺术、症状形成和梦,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都是两种不可调和的需求之间的妥协,提供了一种对抗对他最深入从事的虚构写作意识的防御机制。
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实证基础”中,还有两个重要的长篇案例史——“五岁男孩的恐惧症”(1909年)和“一个偏执病例的评论”(1911年)。像第一个案例“Dora”一样,这两个案例也有了更富虚构色彩的标题:“小汉斯”和“Schreber案”[10]。在这里,弗洛伊德离开了作为实证病史的要求,自由地进入了他的新体裁。他成为一名解释性的评论员,置身于实际治疗操作之外。弗洛伊德并没有亲自分析小汉斯或Daniel Schreber,而是分析了汉斯父亲讲述的故事以及Schreber自传中的故事。
我们还没有到达弗洛伊德不再需要以他实践中的人物为基础进行写作的阶段——或者根本不需要任何实践。他在三部作品中尝试了这种风格:关于Jensen的《格拉迪瓦》(1907年)、关于达芬奇(1910年),以及关于米开朗基罗的《摩西》(1914年),最后一部匿名发表,并带有欺骗性的编辑伪装。(这些文章的写作时间与他主要的案例史平行。)《格拉迪瓦》研究是对完全虚构的梦境的分析,即小说中的梦境。然而,弗洛伊德最主要的冒险进入完全虚构的故事领域是《图腾与禁忌》和《摩西与一神教》。这些都是宗教虚构作品,展示了弗洛伊德的科学(不同于荣格在其关于飞碟、共时性和炼金术的作品中展示的宗教虚构)。对于《图腾与禁忌》和《摩西与一神教》,永远无法产生实证证据。弗洛伊德放弃了实证的伪装,我们看到他作为一名纯粹虚构的作家。自那时以来,我们所有人在这个心理治疗领域中,不再是医学实证主义者,而是故事工作者。
这段文字探讨了弗洛伊德在其著作和案例史中如何通过妥协将文学与医学相结合,以及这种结合如何影响了后来的心理治疗实践。它还讨论了弗洛伊德从医学实证主义向虚构写作的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对后世的影响。
理论与情节 阿兰(Émile Chartier)[11] 给出了关于虚构本质的另一个重要线索:“……在小说中……一切都是基于人性……一切都是有意图的,即使是激情和犯罪,甚至是苦难。”
情节揭示了这些人类意图。 情节展示了所有事情是如何联系在一起并有意义的。只有当一个叙述在人性深处获得内在连贯性时,我们才有了虚构;而为了这种虚构,我们必须有情节。福斯特 [12] 这样解释情节:
情节是……一系列事件的叙述,重点在于因果关系。 “国王死了,然后王后也死了”,这是一个故事。“国王死了,然后王后因悲伤而死”,这是情节。故事回答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情节告诉我们为什么。
构建情节是从问“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转向问“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的这类虚构中,情节就是我们的理论。它们是我们将人性的意图组合在一起的方式,以便我们能够理解故事中事件序列之间的“为什么”。
弗洛伊德在他的案例史中主要目标是解释原因。 他所有的叙事技巧都只是为了情节服务。弗洛伊德设计了一个适用于所有他故事的情节。虽然情节本身很简单,但它需要复杂化、神秘化和幻想。弗洛伊德的艺术性是由他的理论所决定的。我们必须有隐藏和闪回早期回忆及屏幕记忆。情节必须随着移情和阻抗的复杂交织、性格发展的倒退以及故事前进中的关键节点而变得浓重。这种由情节结构产生的丰富性对我们的记忆和智力提出了要求——福斯特认为这些都是情节所必需的。弗洛伊德的情节非常简洁:没有松散的结尾。这种情节上的简洁性在理论上被称为优雅。每个弗洛伊德式的叙述都以相同的方式结束,并可以拆解以展示对“为什么”的一种解答。这个谜团是压抑(有许多变种),接着是激情、犯罪和苦难(症状形成),作者的介入(压抑的移情),通过长期的认知解除压抑(心理治疗),最终是治疗的结局。
当荣格指责弗洛伊德的因果图式过于简单时,他实际上是在批评弗洛伊德的情节构建。人类生活中的情节并不与个人的故事平行展开。 我生活的展开和其情节的发展是两种不同的过程。只有弗洛伊德能用时间顺序来回答“为什么”:首先发生了什么,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还有其他答案,不仅仅是物质和动力因:它还问目的(终极因)以及在故事中起作用的是什么样的原型观念、神话或人物(形式因)。荣格说,我们必须看人物的意向性和他们前进的方向,因为这是影响故事形状的主要因素。每个人都在写自己的故事,既向前也向后,随着他个体化的过程。荣格赋予个体性格远比叙事或情节更重要的权重。
这段文字探讨了弗洛伊德和荣格对情节的不同理解,强调了弗洛伊德的情节构建如何反映了他对因果关系的关注,而荣格则更注重个体性格及其发展方向对故事的影响。
情节的选择逻辑 如果“情节源于作家行为的选择逻辑”[13],那么荣格认为弗洛伊德过于选择性和逻辑化,试图用同一个模子塑造所有的鞋子。虽然一切可能基于人性,但人性本身却是建立在超越人性的事物之上。荣格的情节(他的原型理论)本质上是多样化的和丰富多彩的。个体化表现出多种形式,没有预定的动力,也可能永无止境。
荣格的案例中充满了许多色彩斑斓但无关紧要的线索。 它们不像弗洛伊德的案例那样引人入胜,正因为他的情节选择逻辑较少,因此也不那么具有必然性。只有当它被投射或以英雄冒险或朝圣者旅程的模式阅读时,个体化的情节才能吸引读者。但这只是个体化的一种原型模式,一种选择逻辑的方式。
阿德勒的著作之所以没有弗洛伊德那样的吸引力,原因之一是阿德勒的情节消除了复杂性。阿德勒的情节——像弗洛伊德一样单一,为所有人设计了一种情节——不允许太多的次要发展:象征、防御、伪装、移置、反应形成、编码信息和审查。心理斗争的主要对手(自我、本我、超我)被取消了,因此对读者的智力和记忆力要求也减少了。
弗洛伊德以理论的形式呈现了他关于人性的情节,这个理论使用了医学、生物学和经验主义的语言来描述力比多。他的双重写作风格要求在某一层次上是情节和神话,在另一层次上则是理论和科学。但对于我们这些读者来说,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基本不安并不是因为它无法验证,而是因为它无法令人满意。我们不接受它,并不是因为它作为关于人性的假设在实证上失败了,而是因为它在诗意上失败了——它不足以作为一个足够深刻、包容和美学的情节,为我们的分散生活叙事提供动态连贯性和意义。
弗洛伊德的一个情节是以一个神话命名的,即俄狄浦斯。 通过这一举动,弗洛伊德也将心灵置于诗意的基础之上。他理解到,一个人生的整体叙述、我们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我们进入的梦境,都是由心灵深处的一个深刻神话的选择逻辑所构建的。
弗洛伊德“发现”的俄狄浦斯悲剧将心理学置于诗学的起点,与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使用神话相同。当我们打开这本书读到英文中的“情节”时,会发现每处出现的“情节”原词都是希腊语的mythos。情节就是神话。故事中“为什么”的基本答案可以在神话中找到。
但神话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也不仅仅是一个情节。它是人类与神祇互动的故事。处于神话之中意味着不可避免地与神祇力量相连,并且与它们进行模仿。一旦弗洛伊德和荣格开始用神话来理解人性,他们就从人性转向了宗教力量的本质。心灵的诗意基础表明,我们在生活中情节中的选择逻辑是神话和神话学的逻辑。
这段文字探讨了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对情节的不同理解,强调了弗洛伊德的情节选择逻辑如何影响其理论的表达,而荣格则更关注多样性与个体化的丰富性。同时,它还讨论了神话在心理学中的重要性及其对人性理解的影响。
经验性的虚构 我使用“虚构”一词,并提出案例史在三个意义上是虚构的:
作为事实历史的案例史,即对“任何事物经历的一系列事件的真实记录或知识”[14],是一种虚构,意指一种编造、谎言。但只有当它声称字面意义上的真实时,它才是谎言。早在记录案例史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就发现他并没有记录真正的历史事件,而是那些仿佛真的发生过的事件幻想。案例史的材料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心理幻想,这是主观的东西,正如前面提到的阿兰和福斯特所说的,属于虚构的领域。 即使今天我们使用录音机和来自整个家庭的公开信息,案例史仍然不能声称所讲述的内容是对事件序列的真实描述。这适用于任何形式的历史,尤其是案例史,原因如下:(a) 案例材料必须是自我的——关于梦、激情、幻想、愿望、痛苦等,这些都是作者无法直接见证的;(b) 这些材料特别具有虚构性(难以置信、不合逻辑),因为它们属于临床上称为歇斯底里、偏执、幻觉等超现实和奇异的事件类别;(c) 对案例史的外部佐证(由其他临床医生或家庭成员提供)仅限于有限的具体情况;(d) 任何被称为“历史”的东西都必须与时间性相关联,但正如弗洛伊德和荣格所坚持的,心理现实并不遵循时间规律。 作为虚构叙述的案例史,是指对一个叙事故事中核心人物想象中的内在过程的虚构描述。它的作者不是主要人物,因此它既不是自传,也不是传记,因为叙事事件根据情节的需求被严格选择。这种虚构形式的核心在于经验性的伪装。 关于心理治疗中的经验主义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我只想触及其中一点。根据A. J. 艾耶尔的说法 [15],哲学中的经验主义原因之一是“自我中心困境”。经验主义防止了唯我论;它通过指向公共的、可验证的事件来让我们走出思维的封闭圈子。经验主义不仅是对柏拉图主义(先天观念、普遍概念、演绎理想主义)的防御,从心理学角度看,它也是那种让我们感到安全远离唯我论及其孤立性和潜在偏执感的幻想。因此,由于心理材料本质上是主观的,而治疗情境则通过镜像或双重化(封闭容器)强化了这种孤立的主观性,转向治疗的经验主义是治疗唯我论的直接后果。案例史中的经验性伪装是对治疗所涉及的虚构力量的不可避免的防御。
这段文字探讨了案例史作为虚构的不同层面,强调了其在心理治疗中的作用及其与经验主义的关系。它解释了为什么案例史不能被视为完全真实的历史记录,而是包含了主观的心理幻想,并指出这些虚构如何通过经验性的伪装来对抗唯我论的影响。
案例史作为哲学意义上的虚构 案例史,作为字面陈述的呈现,被转移到无法反驳或验证的地方,在哲学意义上是一种虚构,即一种必须必然将自己置于真伪标准之外的公式,正如瓦伊亨格尔(Vaihinger)所说的“仿佛”虚构。[16] 在这里,虚构是心理构建,通过这些幻想,我们将一个人的生活或个体塑造成一个案例史。 我们将再次触及这三种虚构及其对心理治疗的相关性。但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新类型的虚构的全部现实性,它是在20世纪发明和发展起来的,在诊所、私人执业和福利中心由成千上万的手写成,有时出版,但往往不发表,主要存放在疯人院的档案中和分析师的阁楼上。夜晚,在写作室里,像弗洛伊德那样的孤独治疗师坐在那里,记录、口述、打字,沉浸在患者的故事及其共同的治疗幻想中。
所有这些故事,无论在哪里、由谁书写,无论是具有弗洛伊德的情节还是来自各种不同神话的情节,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主角进入治疗。治疗可能是故事的结局(如经典的回忆叙述——“这就是为什么我来找您,医生”)。或者,治疗可能是故事的开始,如弗洛伊德的案例,以角色进入咨询室为开端,例如1909年的“鼠人”案例。因此,我称这类作品为治疗性虚构。
就像侦探故事需要揭示凶手,英雄悲剧需要主人公的死亡,喜剧需要冲突的愉快解决一样,治疗性虚构是关于一个人来接受治疗的故事,更多的是关于治疗本身而非个人的故事。治疗要么是整个内容,要么是引导到治疗的故事。罗斯的《波特诺伊的怨诉》在体裁上属于治疗性虚构,尽管它与典型治疗性虚构的主要区别在于罗斯没有使用经验性的伪装。
通常,治疗是叙事事件所围绕的主题,就像朵拉的故事。通常,治疗也提供了聚焦和选择事件的手段,就像政治小说选择政治相关的事件一样。通常,故事的结尾会从治疗走向治愈和社会(或者对于反治疗的结局,则是一个“失败的案例”)。弗洛伊德在他的朵拉故事结尾写道:“自从她来访以来,已经过去了几年。在这期间,这个女孩已经结婚……并重新被生活的现实所接纳。” 由于这类故事是以治疗的眼光书写的,它们也被一种新的读者群体以同样的眼光阅读,他们实际上可以将莎士比亚、福克纳或自己的传记视为治疗性虚构的一部分。我们已经看到了弗洛伊德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那么,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段文字探讨了案例史作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虚构,并解释了其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及其文学特征。它指出,治疗性虚构不仅限于专业文献,而是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反映了治疗过程和结果,同时也影响了读者的阅读方式。
治疗中的故事 前来私人治疗的“高阶治疗群体”已经将他们的故事塑造成治疗性的体裁,也就是说,这些故事具有自我反思性,并集中在主角的“问题”上。而“住院患者”的故事形态往往需要倾听者的指导:有太多的主要角色(投射);事件没有根据治疗情节的经济要求进行选择;作为叙事基本要素的时间顺序可能完全缺失。尽管倾听者会将故事塑造成治疗性的体裁,讲述者的状态——即他成为住院患者的原因——在故事的形式中,尤其是其风格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患者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他们的故事。有些人讲故事是为了消磨时间,或者用故事来打发时间;有些人是记者,有些人则是像检察官一样构建控诉。偶尔,一个故事会变得完全隐喻化,其中昨天看到的一切——巨大的建筑工地、戴着安全帽的工头在控制室里、一个小女孩在一个闪亮的银色水坑中险些被推土机撞到、路过的行人出手相助——都指代患者心理内部的人物及其互动。
临床医生应该注意故事的讲述方式。旧的精神病学教科书,如尤金·布卢勒(Eugen Bleuler)的著作,提到风格有助于诊断。精神病医生被鼓励注意夸大的扩展性、散漫的叙述、头韵、双关、奇特的词语联想、夸张、古语、做作——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文学风格教科书中找到的术语。诊断部分基于一个人讲述故事的方式来进行。
心理学诊断也是一种“关于患者的讲述”。它是一种漫画式的简短人物素描——萨斯和戈夫曼可能会称之为“人物诋毁”——用临床专家的语言写成,供其他临床专家阅读。(当然不是给患者看的。)心理学诊断并不说明一个人拥有什么或是什么人。它描述的是他的Zustandsbild(临床图像)。它讲述了患者在临床作者面前的自我呈现。
临床作者将故事编入诊断,编入一个“异常的故事”。我所说的异常有两个含义:首先,这是一个带着对病态、偏差和奇异的关注所写的故事——就像哥特式小说或爱伦·坡的小说,以左拉的自然主义手法呈现。但与哥特式小说、爱伦·坡或左拉的小说不同——这是异常的第二个含义——这个故事自认为是真实的事实历史,从而偏离了故事的规范。诊断在其历史性上完全是字面意义的——当然,它们必须以这种方式讲述,以便将所描述的人组织成作者有权创造的特定虚构风格。诊断是高度创造性的写作行为。字面意义上故事的力量是压倒性的(所有伪装成“真实事实”镜子的想象性写作都是如此)。无论如何,字面主义是临床思维的主要工具。
这段文字探讨了不同类型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讲故事的方式,以及这些故事如何影响诊断和治疗。它强调了故事的风格和内容在心理学诊断中的重要性,并指出诊断本身也是一种高度创造性的写作行为,通过字面主义将患者的叙述转化为特定的临床图像。
诊断故事的力量 诊断故事的力量不容低估。一旦一个人被写入特定的临床幻想中,这个幻想带有其预期、典型性、性格特征以及丰富的词汇来帮助自我认知,这个人就开始将自己的一生重塑为这个故事的形状。过去也被重新讲述,并通过这个“异常”的故事找到了新的内在连贯性,甚至是必然性。诊断确实是一种“认识”(gnosis):一种创造与其形象相符宇宙的自我认知方式。
在每个案例中,故事都引导着治疗,正如我们所说。这也意味着我作为治疗师-作者现在已经进入了故事,实际上成为了其中的关键人物,尽管直到这次会面之前,这个故事的开端、发展、情节和风格与我毫无关系。我从未知道,也或许永远不会知道其他任何角色,不会参与它的其他场景,也不会得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或诊所所谓的“随访”。
然而,在“我”介入之前,治疗体裁的故事并不存在。因此,从患者跨过门槛进入治疗的那一刻起,一个全新的故事开始了——或者说,原来的故事以全新的角度被重新诠释为治疗体裁。这里开始出现所谓的“阻抗”,即患者试图遗忘、扭曲或隐瞒,以保留最初的版本。同时,这里也开始出现所谓的“反移情”,即治疗师-作者对故事的自我沉浸。
现在两位作者正在共同创作一个相互虚构的治疗故事,虽然按照惯例只有其中一位会实际写下它。两人都被故事深深吸引,成为其内部对象,他们的合作可能会变成一种“两人共病”,显示出情节对人物意志的强大控制力。
一位同事曾告诉我一个新患者在她挑战了患者故事的主题模式后离开了她。这位患者自认为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病例,三十六年来几乎持续接受了十五年的治疗;情况没有太大变化(酗酒、同性恋、抑郁、经济忧虑),他尝试过许多种治疗方法。我的同事说:“对我来说,你是新病例,我不接受你像你自己认为的那样病重。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通过拒绝他的构建网络,她也切断了他对支持性虚构的依赖。他没有再回来。他的故事对他来说仍然有意义:一个不可治愈的人,但仍然是治疗界的付费会员。他希望分析和分析师能符合他的故事。
第二个案例来自我的实践中:精神病发作、住院期间遭受医疗虐待、引诱和权利侵犯、休克治疗和“有益药物”。我把这个故事当作另一个女人可能讲述的过去:高中时坠入爱河并嫁给隔壁男孩,拥有一个疼爱她的丈夫、孩子和一只斯宾格犬,一个关于成功的幸福故事。换句话说,两者都是连贯的叙述,揭示了一个组织事件的主题动机。这两个女人,一个来自她的印花床单,另一个来自她的帆布紧身衣——用隐喻表达幻想——可能会走进治疗室,绝望地说出完全相同的话:“这没有任何意义;我浪费了我最好的年华,我不知道我在哪里,也不知道我是谁。”这种无意义感源于主题动机的崩溃:它不再将事件联系在一起并赋予其意义,也不再提供体验的方式。患者正在寻找一个新的故事,或者重新连接她的旧故事。
这段文字探讨了诊断故事对个体自我认知和生活叙述的深远影响,以及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和患者之间的互动如何共同塑造新的故事。它还展示了当原有的主题动机崩溃时,患者寻求新故事或重新连接旧故事的过程。
我相信她的故事是她赖以生存的虚构 我相信她的故事是她赖以生存的虚构,但她并未从中读出其炼金术般的可能性及其隐秘的意义。她以字面意义理解了用临床语言讲述给她的故事,一个关于疾病、虐待和浪费最好年华的故事。需要改变的是这个故事,而不是她本人:它需要重新想象。因此,我将她那些被浪费的岁月转化为另一个虚构:她了解心灵,因为她沉浸于其深处。医院曾是她的高级学校,她的入会仪式,她的宗教确认,她的受虐经历,以及她与心理现实的学徒期。她生存的资格和文凭是她的灵魂在这些心理恐怖中的耐力和受虐享受。她确实是一个受害者,但不是历史的受害者,而是她所构建的那个故事的受害者。
您可能已经注意到,我的同事挑战了一个关于疾病的故事,而我则确认了另一个,但我们两人都与呈现的虚构发生了冲突,从而开始了故事之间的争斗,这是面对面治疗和临床案例讨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在弗洛伊德与朵拉的案例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取走了她的故事,并赋予它一个新的情节,即弗洛伊德式的情节:这一情节的一部分是它对你有好处;它是最好的情节,因为它能治愈,这是治疗体裁的最佳结局。
在深度分析中进行的对话不仅仅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故事进行分析,也不仅仅是治疗过程中发生的其他事情——仪式、暗示、爱欲、权力、投射——它也是歌手之间的争斗,重现了我们人类所知道的最古老的文化娱乐形式之一。这正是为什么治疗声称具有创造性,我有意使用“创造”这个词来指有意义的想象力模式的起源,即诗性(poiesis)。成功的治疗因此是虚构之间的合作,是对故事的重新想象,使之成为一个更聪明、更具想象力的情节,这也意味着在故事的所有部分中都有一种神话感(mythos)。
不幸的是,我们这些治疗师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是歌手。我们错过了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叙述的方式局限于四种类型:史诗、喜剧、侦探小说、社会现实主义。我们接受一切——无论多么激情四溢和充满爱欲,多么悲剧性和高贵,多么古怪和随意——并将其全部转化为我们四种模式中的一种。首先,展示自我发展,特别是从童年时期开始,通过障碍和失败:英雄史诗。其次,讲述混乱的故事,混淆的身份和不确定的性别,愚蠢受害者的无能为力,但最终以适应的良好结局收场:喜剧。第三,通过线索和危机揭开隐藏的情节,由一位沉默寡言但目光敏锐、叼着烟斗的侦探不知疲倦地追踪问题的根源,有点像福尔摩斯或波洛:侦探小说。第四,详细描述琐碎的情境,真实再现生活,家庭作为不幸,环境条件作为另一重不幸,所有这一切都用忧郁的社会学术语和带有倾向性的全景镜头呈现:社会现实主义。
心理学应该直接转向文学,而不是不自觉地使用文学。文学对我们一直很友好,公开地吸收了很多精神分析的内容。文学界的人看到的是小说中的心理学。现在轮到我们看到心理学中的虚构了。
这段文字探讨了治疗师如何帮助患者重新构想他们的故事,以及治疗过程中故事之间的争斗和合作。它还强调了文学与心理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提出了心理学应更多地借鉴文学的观点。
例如,我们可以看看流浪汉小说模式(Picaresque Mode) 例如,我们可以看看流浪汉小说模式。其核心人物既不发展(也不退化),而是经历一系列片段式、不连续的事件。他的叙述突然结束,没有达成任何目标,因此结局既不是喜剧的圆满解决,也不是悲剧的致命缺陷。与其使用宏大的预定框架,成功与失败更多地通过日常体验的滋味来衡量。(对饮食、穿着、金钱、性等方面有精确的关注。)故事中有许多嵌套的故事,它们并不推动主线情节的发展,这表明心理历史在多个地方同时进行——与此同时,在农场上,在森林的另一部分——并在多个角色中同时展开。其他人物和主角一样引人入胜,正如我们梦中的其他形象和幻想中的角色往往比自我更深刻地影响我们的命运。这里没有持久的关系,而是强调面具和伪装,尤其是在皮条客、小偷、私生子、骗子和虚张声势的达官贵人的阴影世界中。这些角色反映了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流浪汉小说式的思考,揭示了每个既定立场的本质,但没有道德上的评判。尽管流浪汉小说中的角色经历了失败、抑郁和背叛,但他们并不会通过痛苦而获得光明。
从悲剧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个案史框架是一种浪费;心灵渴望更具形而上重要性的东西。从喜剧的角度看,需要有一个结局,某种形式的接受意识和社会适应,而这对于流浪汉小说中的人物来说总是充满敌意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从英雄的角度看,流浪汉小说是对个体化史诗的一种精神病态讽刺——但反过来,个体化可能就是一种对流浪汉小说的偏执组织。同样的故事如果用社会现实主义来讲述,就会变成一篇政治小册子,正如无政府主义和流浪汉小说最能在西班牙土壤中茁壮成长一样。
但我已经展示了:个案史有不同的虚构风格,可以用多种虚构体裁来书写。而当一个人能够将他的生活置于这种多样性之中,就像多神教的万神殿一样,不必选择其中之一时,治疗可能是最有帮助的。因为即使在我内心的一部分知道灵魂会在悲剧中走向死亡的同时,另一部分正在经历一个流浪汉小说式的幻想,而第三部分则投身于英雄喜剧般的自我提升。
这段文字探讨了流浪汉小说模式的特点及其在心理治疗中的隐喻意义,以及不同叙事风格如何反映个体内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它还讨论了不同的文学体裁如何影响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和表达,以及如何在治疗中利用这些不同的叙事风格来帮助患者。
体裁与原型 我的荣格派朋友沃尔夫冈·吉格尔里希(Wolfgang Giegerich)在分析埃里希·纽曼(Erich Neumann)的著作中揭示了其内部的原型模式,并指出:
某种“因素”显然阻碍了我们真正进入心理学的视角,使我们的思考变得不具心理学性,因为它让我们渴望甚至需要实证验证、科学真理和系统化。这个“因素”是我们被包含在伟大的母亲/英雄神话中,这种神话的本质是创造一种(神话般的!)幻想,即英雄般地从神话中突破到“事实”、“真理”、“科学”的可能性。
然后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主题,表明以进化术语叙述的文体属于英雄/伟大母亲视角下的一个体裁。这意味着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故事构想为从伟大母亲那里解放出来的战斗——正如荣格所称——我们实际上是在进行英雄行为;这些英雄行为反映在自我发展、自我力量和个人身份等概念中。从这种原型视角中产生的理论是纽曼的《意识的起源与历史》。这本书既不是对进步的信仰声明,也不是关于进化的科学作品。正如吉格尔里希所展示的那样,它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历史,而是一个故事。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由引人入胜的情节串联起来的原型幻想:自我作为一个普通人(Everyman)的发展,每个人都能与之产生共鸣。它的说服力同样建立在这种原型基础上——即原型的修辞——在这个例子中,将我们每位读者都置于一个从母性的脐带恐惧中解放出来的英雄之战的个体发生重演之中。
吉格尔里希将一种精神分析写作体裁与原型联系起来。在我的一篇短文中,我也试图展示,呈现心理学的某种风格,特别是荣格的心理学,通过图表、数字、晶体,引用内向性和缓慢的耐心,以及古老智慧和魔法的形象,如老智者的形象,都属于土星的长者意识。再次强调,这是原型的修辞。再次强调,这是一种决定我们情节和写病例史风格的体裁。
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在其《批评的解剖》中对体裁与原型的关系进行了最著名的探讨,他在其中将文学的四个古典体裁分别赋予一年中的四季,从而使文学遵循玉米神的周期。实际上,尽管弗莱的体系是四重的,但它仍然停留在伟大母亲神话、她的儿子神英雄和自然周期的单一神话之内。
比所有这些尝试更为根本的是可以从帕特里夏·贝瑞(Patricia Berry)的一篇论文中推导出的一种方法。她认为,叙事本身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自我的关注,因为叙事本质上是英雄原型的体裁。她写道:
叙事还受到治疗的强化。正如我们讲述梦境一样,我们也叙述我们的生命故事。不仅梦境的内容受到分析的影响,连我们回忆的方式也受到影响……由于叙述风格与连续性的感觉密不可分——在心理治疗中我们称之为自我——因此由于自我滥用连续性的情况也常常出现……叙事最重要的问题是:它倾向于成为自我的旅程。英雄总能找到自己处于任何故事的中心。他可以把任何事情变成一个如何成功并保持优势的寓言。故事中的连续性变成了他的持续英雄运动。因此,当我们以叙事方式解读梦境时,没有什么比将运动序列视为一种最终以梦者的应得奖励或失败告终的进步更符合自我的自然了。故事将一个人包裹其中作为主角的方式会把梦境扭曲成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自我只看到自己的关注点。
这段文字探讨了体裁与原型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精神分析和心理学写作中的体现。它还讨论了叙事在治疗中的作用及其对自我认知的影响,强调了叙事如何反映和塑造自我,并可能将其转变为一种自我中心的表达方式。
罗杰·福勒在他的词典中简洁地表达了类似的思想:“没有英雄的叙事仍然是批判性的虚构。”【21】即使是反英雄,在心理学上我们也会称之为自我(ego)的负面膨胀。无论是否被提及,自我总是存在的。如果我们以叙述的形式讲故事,那么我们最终会涉及到自我理论。贝瑞暗示,叙事这一体裁本身决定了我们如何构建和理解个案史的情节。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个案史写作风格,甚至对个别梦境和情境的解释,是自我心理学的结果吗?还是可能自我心理学——首先由弗洛伊德提出,然后由他学派的一个分支,以及现在的治疗机构所呈现的——源于我们的个案史写作风格?我们是否通过撰写个案的方式产生了自我心理学?我们的个案史不仅仅是对心灵运作方式的经验性展示,而是对我们如何通过创造(poiesis)来组织我们视野的经验性展示?
这意味着我们将开始用原型的眼光阅读个案史,关注其形式。我们会对个案幻想的体裁感兴趣,甚至是节奏、语言、句子结构和隐喻,因为我们不仅在个案史的内容中发现原型,形式也是原型的。存在一种形式的原型心理学。因此,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如果故事以另一种方式、由另一只手、从另一个视角书写,它将听起来不同,因此成为不同的故事。我建议的是治疗、传记乃至我们生活的诗意基础。
也许英雄自我的例子和流浪汉小说的例子还不足以说明我的意思。让我们回到老年的意识抽象,在这里我们完全脱离了叙事,无论是史诗还是情节。
在弗洛伊德和荣格的个案写作中,这种老年风格强调减少,要么向下减少到阉割焦虑、全能幻想、原始场景等,要么向上减少到整体性、自我、四重性。分析工作更多地描述了灵魂中起作用的基本抽象状态,而不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这些抽象和简化可以是理论上的,例如关于力比多及其量化,或者是历史性的、数字性的(四元数),或配置性的(曼荼罗)。
梦中的形象不再是主要且不可简化的,正如荣格自己的理论所述,而是某种更抽象的东西的代表。橱窗里的女士修理地毯并不是那个具体的形象及其隐喻意义,而是被简化为一个非具象和抽象的母亲形象的代表。童年的场景既不作为图像处理,也不链接到发展叙事中,而是成为理论普遍性的范例,肛门期或俄狄浦斯情结。事件不再讲述一个故事,而是揭示一个结构。这个结构随后被应用于其他事件,跨越时间和不顾上下文的图像——在学校争当最好、更换内衣的强迫症、露营时对黑暗森林的恐惧——将它们统一起来,作为单一根本原则的表现。
不再是一个接一个地追问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从一个情境过渡到下一个情境。而是实例体现原则,图像是寓言,场景是在时间中永恒真理的再现。在这个体裁中检查个案——我特意使用“检查”这个词——由作者-分析师代表的意识功能在于看到抽象物,敏锐地洞察结构和法则。
在这里,意识的连接功能被定义为系统性的,不是封闭地就意义而言,也不是战斗地就激活而言,也不是色情地或酒神式地,而是通过一种偏执的能力来看待防御和抵抗作为机制(而不是英雄进程中的障碍)。最后,在这个体裁中的结局不是以患者的目标(如改善)为终点,这属于叙事风格和自我发展,而是在分析科学上的指导,是对理论的贡献,为这座纪念碑添砖加瓦。土星,即老年。【22】
您可能已经注意到,我加入了一些我们尚未讨论的替代观点:炼金术式的写作,其中连接不是封闭而是开放和揭示;阿佛洛狄蒂式的(Aphroditic),关注感官价值、个人关系或性;酒神式的(Dionysian),其中流动最为重要。我还只是暗示了“阿尼玛”(anima)的观点,依我之见,它会停留在图像和幻想本身上,从不将它们翻译或组织成叙事或情节,而是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回应它们,在这种风格中,意识表现为暗示、反思、回声、语调和难以捉摸的动作。
文学研究中并不新鲜的是,认为在我们的叙述中有一个神,并且这个神塑造了词语,使之成为体裁的语法结构。即使这可能会让我的一些同事感到震惊,他们真的相信自己只是在撰写临床事实报告。例如,安娜贝尔·帕特森【23】再次探讨了“七颗大星”或文艺复兴时期作品中使用的七种风格理念的描述。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神是如何与不同的体裁联系起来的,比如土星与庄重、水星与速度、金星与美丽、火星与猛烈等。当然,这些一对一的平行关系不应被强加:多神心理学不能直截了当地一对一表达。相反,它们应被视为对撰写和阅读临床报告以及倾听患者语言的启发性视角。
本节中的观点已经在贝瑞的同一篇文章中提出过:“我们讲述故事的方式就是我们构建治疗的方式。”我们想象生活的方式就是我们将继续生活的方向。因为我们向自己讲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方式决定了事件如何成为体验。没有裸露的事件、单纯的实事、简单数据——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也是一个原型幻想:原始(或死寂)自然的简化论。修辞学意味着说服的艺术。而原型的修辞是每个神如何说服我们相信个案史中的神话,即情节。但神话和神并不是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在神圣时刻通过神谕或形象的显现来揭示。它们就在修辞本身之中,在我们用词说服自己的方式中,关于我们如何讲述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并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要在心理学中找到神,我们应该首先审视我们个案史写作的体裁。
我们的反思需要转向作为文学的精神分析文献。我建议文学反思是理解无知、无意识、盲点的主要方式,因为我们在工作中未区分主观因素,即工作中的神。
灵魂史与个案史 在继续之前,我们需要回到阿兰所做的区分:历史作为外部事件的故事,而虚构作为内部事件的故事。这一区分在我的《自杀与灵魂》一书中至关重要,我主张,如果要理解自杀,只能从灵魂及其内在历史的角度出发。个案记录中的外部事件是不够的。让我重复一下那里的观点:
外与内、生活与灵魂,在“个案史”和“灵魂史”中表现为平行关系。个案史是个体参与的历史事件的传记:家庭、学校、工作、疾病、战争、爱情。灵魂史常常完全忽略这些事件中的某些或许多,并自发地创造虚构和“内心景观”,而这些并不依赖于主要的外部关联。灵魂的传记关乎体验。它似乎不遵循时间单向流动的方向,而是由情感、梦境和幻想最好地表达出来……重大梦境、危机和洞见所引发的体验定义了个性。它们也有像个案史中的外部事件一样的“名字”和“日期”;它们如同界碑,划分出个人的独特领地。这些标记比生活的外部事实更难以否认,因为国籍、婚姻、宗教、职业甚至自己的名字都可以改变……个案史报告的是与世界事实相关的成就和失败。但灵魂既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取得成就,也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失败……灵魂想象并玩耍——而玩耍不会被记录下来。我们童年时期的玩耍岁月中有多少能在个案史中体现出来呢?……当个案史呈现了一系列通向诊断的事实时,灵魂史则展示了一种同心的混乱,总是指向自身之外……我们无法通过个案史获得灵魂史。【24】
随后对这种激进区别的缓和需要更多的篇幅,这里无法全部重印,但区别依然明确。个案史被贬低为“与世界事实相关的生命成就和失败”。它只是医学模式的遗物,对灵魂的关注而言是偶然的。
但这行不通。个案史不仅是书面文件,更是每个存在的实际组成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父母和学校、疾病和文凭、工作和失去的爱情。这些对灵魂来说难道是微不足道的吗?本文中对个案史的探讨延续了自杀问题上的讨论:个案史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要有它?
只要问题仍被困在旧的机械二元论中——灵魂与世界、内在与外在、心理与医学——我们就只能沿着相同的旧路前行。相反,我们必须看到历史事件本身的内在必然性,这里的“内在”不再意味着私人化且归属于自我、灵魂或自我意识,而是事件中的主观性以及将那些事件内化的态度,深入其中寻找心理深度。
心理学中的机械论核心错误在于将功能和行动视为分离的离散运动部件。我对两种“历史”的核心错误就是这种机械论的分离,即将灵魂和个案分开,后者进一步完全硬化为字面事实。上述段落对此表达得足够强烈。通过对个案史作为硬性事实的严格态度,我可以使灵魂史完全内在、重要且富有象征意义。
这种两分法模型包含了历史学家所谓的错误,即历史字面主义的错误,认为历史中写的就是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对事实的报告,是对实际事件的真实描述。阿兰也犯了这个错误,将历史放在一边,将虚构放在另一边。这种分离赋予了个案史以字面现实的崇高地位,然后必须通过过分强调——如我在上面所做的——灵魂史具有同样的现实性:“它们也有‘名字’和‘日期’……像界碑一样……”由于将外部事实具体化,我也不得不将内在具体化并硬化。
我在这里想要纠正之前遗漏的一点:个案史——无论其风格多么“外在”——也是一种想象的方式。我会重新看待个案史,作为灵魂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作为一种具有历史的案例。这样,我们可以尊重个案史,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虚构的形式:一种被字面化了的虚构,而它必然不自认为是虚构,因为在这一轮讨论中我们将看到,这种字面化对灵魂来说是必要的。灵魂需要它的字面化的个案史,并在参与生活的过程中不断增添内容。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用内在的灵魂确定性来对抗外在事实的流动。我们对自己所谓的“真实”本质和灵魂的里程碑所作的描述,同样容易受到溶解、误解和边界的改变,就像任何“外在”事件一样。我们对自己可能产生与对外部世界事实同样的误解。个案史中的外在事件与灵魂史中的内在体验之间的区别,不能以不可磨灭的永久性和字面真相为基础。没有哪一方更“真实”,仅仅因为它更坚实。我们必须以另一种方式肯定心理现实——不是通过复制用于外部现实的那些字面比喻、固定性和坚硬性的幻想。
要从其他基础上区分内在和外在,意味着看到灵魂与历史之间的运动是一个持续内化和外化、获得洞察又失去、去字面化又再字面化的过程。灵魂和历史是我们给这种更根本操作的名称,这种操作发生在印度思想所称的苏克玛(细微)和斯图拉(粗重)之间,发生在虚构的隐喻视角和字面的历史视角之间,也发生在内在性和外在性之间。并不是说有两种不同类型的事件或两个事件发生的场所,而是对事件的两种视角,一种是内在的心理视角,另一种是外在的历史视角。
现在我们来到灵魂与历史关系的一个根本点。当一个事件经历了一个心理过程,被灵魂以多种方式加工后,它就从外在转变为内在,成为灵魂的一部分。柏拉图为我们指出了主要的方式:辩证法、某些形式的狂热包括爱和仪式,以及诗歌。我们还可以加上疾病或病理化作为心灵的死亡学活动。我们可以通过将世界转化为疾病来接纳它;通过制造症状,我们可以将一个事件转化为体验。但简单的叙述,仅仅是故事,不足以形成灵魂。
爱情故事只是众多故事中的一个,仅仅是情感事件的外在历史,如同一群黄色水仙花,除非它在宁静中被回忆,并经过心理加工,如灵魂本身所迫使其进行的——情书、焦虑、诗歌、秘密、冒险的幽会、膨胀的幻想。梦境、幻象和感受——如此内在且属于我——除非被回忆、记录并进入历史,否则与灵魂无关。内在的意象和感受(所谓的“灵魂材料”)每晚在梦幻集市上自由获取,不过是来自爱之隧道和恐怖密室的赠品,除非它们经过有资格的智慧处理,通过心灵的历史化,在爱、仪式、辩证法、艺术或心理分析及其治疗情节中的纪律性反思中被筛选和衡量。
在这里,我将历史视为等同于灵魂塑造的过程,作为一种消化操作。
这两种历史方式在灵魂与个案之间的对立中再次出现。个案类型的历史是外在性的故事,原始粗糙的物质,未发酵、未消化、未加工。这种个案材料(同样也可以这样称呼)可以是LSD之旅或宗教启示中强烈的私人幻想,也可能是我文件中枯燥的公开文件——只要这些材料没有被加工和吸收成为体验。外在意味着我们从外部观察它;它封闭在其事实字面性中。这个和那个发生了,然后又发生了这个。内在意味着我们在接纳它;它向洞察力开放。接纳使事件的发生速度减慢,为了咀嚼。
我们可以从灵魂的角度看待历史。通过仔细整理发生的事情,历史消化了事件,将它们从个案材料转化为细微物质。隐藏在这个幻想中是我信仰的一个原则:灵魂减缓了历史的进程;消化驯服了欲望;体验凝固了事件。我相信,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体验,就需要更少的事件,时间的快速流逝将会停止。我还相信,我们未消化的东西会在别处显现,进入他人、政治世界、梦境、身体的症状,变得字面化和外在(并被称为历史),因为对我们来说,它太难、太不透明,无法打破并获得洞察。
我们未经历的东西只会成为个案材料或世界历史,加速了在我灵魂和世界中的事件节奏。正如一句老话所说:“所有匆忙都来自魔鬼”,从心理学角度看,这意味着一个人的魔鬼可以在其消化不良中找到,即拥有的事件超过了所经历的。通过将事件通过想象过程进行体验,我们把它们从时间的街道和我心智的无知海洋中移除。我们只需静止不动就能战胜魔鬼。
爱情故事只是一个故事,众多故事中的一个,仅仅是情感事件的外在历史,如同一群黄色水仙花,除非它在宁静中被回忆,并经过心理加工,如灵魂本身所迫使其进行的——情书、焦虑、诗歌、秘密、冒险的幽会、膨胀的幻想。梦境、幻象和感受——如此内在且属于我——除非被回忆、记录并进入历史,否则与灵魂无关。内在的意象和感受(所谓的“灵魂材料”)每晚在梦幻集市上自由获取,不过是来自爱之隧道和恐怖密室的赠品,除非它们经过有资格的智慧处理,通过心灵的历史化,在爱、仪式、辩证法、艺术或心理分析及其治疗情节中的纪律性反思中被筛选和衡量。
在这里,我将历史视为等同于灵魂塑造的过程,作为一种消化操作。
这两种历史方式在灵魂与个案之间的对立中再次出现。个案类型的历史是外在性的故事,原始粗糙的物质,未发酵、未消化、未加工。这种个案材料(同样也可以这样称呼)可以是LSD之旅或宗教启示中强烈的私人幻想,也可能是我文件中枯燥的公开文件——只要这些材料没有被加工和吸收成为体验。外在意味着我们从外部观察它;它封闭在其事实字面性中。这个和那个发生了,然后又发生了这个。内在意味着我们在接纳它;它向洞察力开放。接纳使事件的发生速度减慢,为了咀嚼。
我们可以从灵魂的角度看待历史。通过仔细整理发生的事情,历史消化了事件,将它们从个案材料转化为细微物质。隐藏在这个幻想中是我信仰的一个原则:灵魂减缓了历史的进程;消化驯服了欲望;体验凝固了事件。我相信,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体验,就需要更少的事件,时间的快速流逝将会停止。我还相信,我们未消化的东西会在别处显现,进入他人、政治世界、梦境、身体的症状,变得字面化和外在(并被称为历史),因为对我们来说,它太难、太不透明,无法打破并获得洞察。
我们未经历的东西只会成为个案材料或世界历史,加速了在我灵魂和世界中的事件节奏。正如一句老话所说:“所有匆忙都来自魔鬼”,从心理学角度看,这意味着一个人的魔鬼可以在其消化不良中找到,即拥有的事件超过了所经历的。通过将事件通过想象过程进行体验,我们把它们从时间的街道和我心智的无知海洋中移除。我们只需静止不动就能战胜魔鬼。
简化与总结 爱情故事只是众多故事中的一个,仅仅是情感事件的外在历史,如同一群黄色水仙花,除非它在宁静中被回忆并经过心理加工,如情书、焦虑、诗歌、秘密、冒险的幽会、膨胀的幻想。梦境、幻象和感受——如此内在且属于我——除非被回忆、记录并进入历史,否则与灵魂无关。内在的意象和感受(所谓的“灵魂材料”)每晚在梦幻集市上自由获取,不过是来自爱之隧道和恐怖密室的赠品,除非它们经过有资格的智慧处理,通过心灵的历史化,在爱、仪式、辩证法、艺术或心理分析及其治疗情节中的纪律性反思中被筛选和衡量。
我在此将历史视为等同于灵魂塑造的过程,作为一种消化操作。个案类型的历史是外在性的故事,原始粗糙的物质,未发酵、未消化、未加工。外在意味着我们从外部观察它;它封闭在其事实字面性中。内在意味着我们在接纳它;它向洞察力开放。接纳使事件的发生速度减慢,为了咀嚼。
通过仔细整理发生的事情,历史消化了事件,将它们从个案材料转化为细微物质。灵魂减缓了历史的进程;消化驯服了欲望;体验凝固了事件。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体验,就需要更少的事件,时间的快速流逝将会停止。我们未消化的东西会在别处显现,进入他人、政治世界、梦境、身体的症状,变得字面化和外在(并被称为历史)。我们未经历的东西只会成为个案材料或世界历史,加速了在我灵魂和世界中的事件节奏。通过将事件通过想象过程进行体验,我们把它们从时间的街道和我心智的无知海洋中移除。我们只需静止不动就能战胜魔鬼。
或者倒退——回归属于灵魂塑造的消化模式,因此许多回忆、它的痛苦、它的羞耻都是重新经历的过程,在章节关闭之前再次修订。分析师可能应该像小说家改写他们的虚构作品一样频繁地重写个案。撰写个案,然后重写和编辑,都属于治疗的一部分,治愈其中考虑不周的时刻和未消化的残留物。我们也需要清除我们写作中的时尚行话、借用的思想、传统主义和自我反思的自负。我们需要注意到使表达更加精确的形容词、介词短语,甚至是逗号,以锐化形象到本质。随着我们这些分析师变得更有文学素养,我们可能会变得不那么字面化,不再局限于个案本身而看不到其灵魂。毕竟,心理治疗意味着心灵的治疗,其实践不应仅限于那些通过诊所后匿名消失在生活中的人。写作中的跟进是我们的消化过程。实践在从业者身上继续进行,我们仍在“练习”弗洛伊德的案例。心理治疗只有通过回归才能进步,重新审视材料,重写自己的历史。
因此,我在心理上崇拜时间与缓慢之神萨图恩(Saturn)的祭坛,他是原型吞噬者,通过他那权威性的抑郁教会我们内部消化的艺术。
有趣的是,分析并不以这种有益的方式看待历史。深层心理疗法深入一个人的过去,目的是改变甚至摆脱过去的束缚。一个人之所以成为带有历史的个案,正是因为有历史的存在。治疗是一种反历史的操作(opus contra historiam),它对抗童年和社会的历史影响,以揭示一个真正的非历史性自我并解放它。因此,深层疗法会援引非历史的原则,如本能、无意识的时间性、重生、原型和其他永恒的普遍性概念,如俄狄浦斯情结或自我。深层往往意味着超越或脱离历史。这些疗法还试图赋予灵魂一个独立于其个案材料的历史,一个其历史重演种系发生或宗教个体化的灵魂。
但我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两种历史之间的对立是治疗情节的必要部分。治疗需要字面现实的虚构作为主要工作材料。它必须拥有原始材料才能加工。所以我们从经典的病史开始。但这不是为了基于事实,而是因为这些事实故事是患者心灵所陷入的原始物质。他沉浸在这些字面的依附和认同中,被物理现象的具体细节所束缚。这里看似没有灵魂的深渊,未形成、非心理学的材料充满了兄弟数据、经济数字、福利中心的经历、疼痛和需求,尚未“加工”成情节:所有这些都是发酵之前的阶段。
这一层面的虚构必须以字面化形式呈现。治疗情节需要模糊的事件以便产生洞察力。此外,作为持续过程的治疗情节需要新的材料来继续创造灵魂。因此,个案史及其材料与灵魂史并行,并使灵魂史成为可能。治疗通过保持“外在”和“内在”之间的界限,利用解释的艺术在这两者之间来回移动事物而受益。
解释需要精心维护的边界——或许正是这些解释创造了边界。也许,所有那些在心理治疗中精心定义的边界——患者与医生之间、客观与主观之间、符号与概念之间、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边界——都源于治疗最初的、基本的解释性翻译动作。防御、抵抗、对立面、自我边界:这是一门关于边界的语言。也许,移情本身也是一种解释的功能;如果我们放弃两种语言之间需要翻译的边界,就不会有两人之间的紧张移情。
假设我们不再将边界想象成对立双方之间的沟壑和战壕,需要审查员、翻译者和专业规则,而是将它们想象成镜子。分析作为一种模仿(mimesis)。那么,治疗会唤起相互对应的意象,来回反射。患者带来的图像在我的心中获得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反映,而不是被翻译成我的语言。我们对绘画和音乐的回应不需要翻译,为什么梦不能也是如此?富有想象力的艺术放弃了解释,而呼唤一种相当的想象力行为。你的梦在我心中唤起一个梦,我的梦在你心中唤起另一个梦——不是字面上如此,也不是相互分享和坦白(这会使意象陷入个人主观主义),而是作为幻想、幻想、想象力的回应,是一种不以解释为目的的灵魂塑造,不是理解的姿态。在镜像边界上,听不到意义的语言;理解彼此并不是目的,因此翻译变得无关紧要。相反,边界卫士之间有一种来回模仿的舞蹈,意象的问候,礼物的交换,仪式的进行。
你是否瞥见了我所指的方向?赫尔墨斯(Hermes)。他是边界和解释之神,是不同类型世界之间的连接之神。作为解释程序的心理治疗已经邀请了狡猾、多变的赫尔墨斯进入,带着他的商业、阳具、欺骗,然后必须通过限制来控制他,而这作为边界,反而更加激励了赫尔墨斯。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解释学的循环。无尽的分析因为不断有新的无意识材料等待有意识的解释。
我的观点并不是说赫尔墨斯不适合用于分析。我的意思是,一旦他被邀请进来,我们就应该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他自己就是一个治愈性的虚构,一位神祇。赫尔墨斯通过让我们相信解释的虚构性,并使其生效,使得解释者能够找到那句话,打开道路。但如果赫尔墨斯要作为灵魂的引导者发挥作用,我们必须有一些材料让他转化为信息。没有梦就没有治疗性的洞察。必须有某种东西跨越门槛并交流,转化为洞察。他在解释行为中显现;他的礼物就是洞察力。我们可以通过堆砌的石堆识别他的干预痕迹。这些界碑继续在心灵中竖立,成为其灵魂历史的一部分(如上所述),在对梦或故事进行巧妙的解释工作后。
当赫尔墨斯在分析中起作用时,人们会感觉自己的故事被偷走并变成了其他东西。(我的一位女同事“欺骗”了她的新患者,没有给他想要的故事:这是一次赫尔墨斯式的举动,即使它并没有奏效。)患者讲述他的故事,突然间故事情节发生了转变。他抵抗,就像试图阻止一个小偷……这根本不是我原本的意思,完全不是。但为时已晚:赫尔墨斯已经抓住了这个故事,扭转了它的方向,把黑变成白,给它插上了翅膀。故事从它最初开始的历史背景中消失,被转化成了一种地下意义。
弗洛伊德和荣格都从这些赫尔墨斯式的技巧开始。“昨天发生了一件疯狂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变成了解释学的信息。他们将口误、玩笑和词语联想的奇特之处从其表面上看似无辜的背景中抽离出来,带入心理意义的广阔洞穴。他们是赫尔墨斯式转换的大师,将个案材料转化为灵魂。
荣格:赫尔墨斯的孩子?
除了我们提到的流派——赫尔墨斯式、英雄式、流浪汉式或片段式、情色式、土星式以及阿尼玛式——我们可以在荣格的作品中找到另一种流派的种子。但我们必须在正确的地方寻找。尽管荣格对心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做出了几项贡献,这些贡献属于更传统的深度心理学方法。它们是普遍的,并且用对立的概念来描述整个问题:个人/集体无意识、美学/心理学、创造力/正常性、形式/内容等。荣格关于虚构的少量观察,除了他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与歌德的《浮士德》的亲和力之外,大多指的是二流作家如Rider Haggard。他真正的贡献,如同弗洛伊德一样,在于他自己构建的虚构,即他写作心理学的独特方式。《答约伯书》是最明显的例子,但他对不同原型(骗子、水银、儿童、阿尼玛、母亲)的现象学描述更为有趣,这些是虚构人格、传记或原型人物的性格描述的创造性发明。
与弗洛伊德一样,荣格发表的大部分个案材料(不包括他早期的精神病学和弗洛伊德学派论文,即在他三十七岁之前的工作,那时荣格成为我们现在所说的荣格式分析师)与临床实证相距甚远。当他提到个案时,贯穿他的所有书面作品,不是在临床实证意义上,而是作为轶事填充或论点的实例。他的个案通常是次要的说明,常以“我想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作为引言。
虽然荣格将其最著名的长个案“米勒小姐”(Symbols of Transformation,CW 5)副标题为“精神分裂症前奏的分析”,但它实际上是像弗洛伊德的施雷伯案例一样,是对一份印刷文件的分析。这份文件最初由美国人撰写,法语翻译版由荣格用德语处理。他的第二重要的出版个案(Psychology and Alchemy,CW 12),像弗洛伊德的汉斯案例一样,来自一位未与荣格进行过分析工作的患者的材料。荣格特意选择了一个非自己处理的个案,以便通过个案来展示他的理论更加客观实证,即较少受他本人的影响(参见CW 11: 38)。即使是那名臭名昭著的Burghölzli医院患者,其自发幻想太阳阳具创造风的现象成为了荣格关于集体无意识和原型假设的“实证”基础,实际上也不是荣格自己的个案,而是他的学生Honegger告诉他的。
当荣格介绍他收集的作品中包含关于实证分析的论文,并以《心理治疗的实践》(CW 16)这一经验性标题命名的一卷时,他说:“这本书可以给读者一个关于心理治疗实证基础的良好印象。”普通读者期待的是“个案材料”,但书中提到的十一个案例——除了第二版中编辑在荣格去世后附加的简短遗作——大多是顺带提及的轶事,或者是患者的梦境,作为荣格解释方法的材料。
后期荣格对“实证”的使用本身值得研究,因为他刷新了一个已经缩窄为科学主义陈词滥调的术语。我认为,他使用这个词指的是他自己内心的一种主观过程,更符合诗人对实证的用法。实证事件——例如患者心中的太阳阳具形象——触发了思维中的运动,启动了一个假设(或是一个意象、一行诗句)。然后人们会将实证事件指认为有效原因,因为假设确实是从具有时间和地点的具体事实开始的,就像一首诗可能从具体的感知开始。和诗人一样,荣格不断回到具体感知的世界(个案、梦境、宗教幻想、古代文本)。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实证的。其次,他在积累实例以支持其假设方面也是实证的;第三,在实用主义的意义上,通过实际治疗启发来评估假设。但他并不是实证的,即使在单个个案作为范例的临床意义上也是如此,因为个案并不是他洞见的不可或缺来源,也不是这些洞见的验证场所。
例外的是他的自传。这本自传出现在他二十卷宇宙观的最后,并不打算成为其早期理论的证据,尽管后来它被证明是他整个工作的主要实证载体。[28] 荣格的工作,如同弗洛伊德的梦、压抑和无意识理论一样,源自一个主要的个案历史,并由作者自己的经历所证明。
总之,荣格呈现个案的方式绝对不是医学实证——即医生、患者、病理和治疗之间互动的报告——而是他的个案材料展示了自发的心理虚构及其解释。(这些梦境和幻想与“个案”及医生[荣格]的关系几乎没有详细描述,通常是偶然提及的。)他的个案也不是病史,不是生活传记的呈现,这种模式是他明确拒绝的:某些方面指责新的心理治疗过多关注哲学问题,而不够重视个案历史的细节。这个指责必须坚决反驳,因为哲学问题在任何对心灵的实证研究中都占有极高的地位,既是研究的合适主题,也是哲学批评的对象。专注于个案历史细节的实证智力,不知不觉地将其自身的哲学前提不仅带入材料的安排,还带入对其的判断,甚至带入看似客观的数据呈现。如果当代心理治疗师开始谈论世界观、人生哲学,这仅仅证明他们发现了以前被最天真地忽视的某些广泛假设。如果工作受到未声明的假设影响,即使是最精确、最严谨的工作又有什么用呢?[29]
那么,我们剩下的是什么?是对自发心理想象的解释和评论。这些材料虽然被称为“无意识材料”,但实际上是虚构的。弗洛伊德在上述意义上是一个虚构的作家,而荣格则是一个关于虚构的作家。对荣格而言,虚构得越离奇越好(因此,他涉足炼金术、西藏、查拉图斯特拉、占星学的时代、精神分裂症、超心理学),因为这些“材料”迫使他在同样富有想象力的层面上与之相遇。然而——弗洛伊德和荣格都采取了实证的姿态,接受实证批评,并试图以实证辩护来回应。如果他们能从自己工作的领域——文学想象的领域——寻求帮助,他们会得到更好的服务。
荣格的心理学写作风格多样,有时像异端传教士那样充满劝诫和启示录色彩,有时带有冯特实验主义者的图表和数据,有时则充满了古怪的系统、晦涩的语言和深奥的引用,如同早期近东地区的诺斯替主义者。正如赫尔墨斯的双翼之足既能在冥界也能在奥林匹斯山着陆,并传递众神的消息,荣格的解释没有时空的限制——中国瑜伽、墨西哥仪式、当代历史事件、医院患者、现代物理学——他可以解释任何事物;任何事物都是他心理操作的原始材料。他的心理学呈现为一篇持续的文章,Versuch(尝试)。和其他伟大的散文家一样,如蒙田或爱默生,荣格始终强调他并没有写一个系统。尽管第二代追随者迅速揭示了这些非系统文章中隐藏的宇宙观——包括地图和图表——这并不使荣格本人显得不那么神秘。唯一一部试图进行系统化阐述的作品(CW 7)是在他主要的科学、宗教、神话、炼金术和心理现实作品构思之前写的。(这本书至今仍被用作理解荣格作品的基础,显示了我们对心理学解释系统的渴望,而不是对其深入见解的追求。)
因此,荣格的心理学写作似乎在多个方面受到了赫尔墨斯的影响:关注心灵的边缘状态;参与心灵的秘密;以及第三,在心理学的边界上进行解释研究,那里不同领域相互接触。此外,荣格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赫尔墨斯式的解释。它不是创造新的宇宙观,而是通过引导一切向心灵靠近,再引导心灵走向死亡,重新赋予现有宇宙观意义。所有事物都承载着来自诸神的信息。赫尔墨斯出现在荣格对意义神话的关注中,他对水银(Mercurius)的反复吸引,无论是在精神分裂症、同步性、转化、死亡还是在赫尔墨斯艺术(炼金术)中。赫尔墨斯也是那个能够扭曲词语的骗子,比如将“实证”一词扭转,以传达当下所需的讯息,从而巧妙地引入另一层含义。在他的博林根石雕中央,环绕着行星符号的是水银的标志。[30] 水银不仅是书写之神,还代表着其他许多含义。
然而,以我自己的赫尔墨斯式方式,我想指出荣格心中的神并不是赫尔墨斯,而是狄俄尼索斯,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转向荣格对梦的讨论。
梦、戏剧、狄俄尼索斯 荣格并不接受弗洛伊德对梦的虚构;它既过于刻意又过于简单。对荣格而言,梦不是寓言——“用另一种伪装描述某个主题的叙述”,其中“人物、行动和场景系统性地具有象征意义”。梦是隐喻性的,同时说着两种语言,或者说,这种赫尔墨斯式的双重性使得梦成为一个符号,将两个不和谐的事物结合成一个独特的声音。弗洛伊德和荣格之间的区别在于寓言和隐喻的区别。而寓言和隐喻的区别比弗洛伊德和荣格理论中的情节或理论差异更能决定真正心理学流派的理解,以及灵魂及其语言的本质。
寓言和隐喻都以一种事物仿佛是另一种事物的方式开始。但寓言的方法将这种双重表达分为两个组成部分——潜在的和显现的,并要求将显现的部分转化为潜在的部分;而隐喻的方法则保持两种声音在一起,聆听梦本身的声音,在每一刻既含糊又具体地传达意义。隐喻不能被解释性地翻译而不破坏其独特的统一性。例如,“这个人有一条木腿”不再是隐喻,如果有人说:“看,他的裤子里有一条腿是假的”,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仅是比喻地说他的风格像有木腿的人一样,它是假的、空洞的;它瘸了,拖沓。”由于符号和隐喻无法被翻译,因此需要另一种理解梦的方法,这种方法内在包含面具、伪装和双重性,本身就是隐喻性的。
对荣格而言,这种隐喻式的表达方式是自然本身的声音;荣格最喜欢的梦的隐喻是它就是自然本身在说话。他至少对我而言意味着natura naturans(自然的创造力量)和natura naturata(自然的原始形式,即模糊但精确的原型图像)。通过转向梦来寻找灵魂中的创造性自然,荣格也在转向这一自然的神——狄俄尼索斯。狄俄尼索斯既是生命的力量zoe,也是原始幻想的模糊流动;他永远是个孩子,两性同体,是灵魂之主,通过半隐半现的事件实现心理转化。荣格通过指出梦具有戏剧结构,也指向了狄俄尼索斯。狄俄尼索斯是戏剧之神:悲剧这个词意为“山羊歌”。
当荣格说梦具有戏剧结构,且其本质可以被视为剧场时,他做了与弗洛伊德相同的举动。他们都把用来观看梦的概念投射到梦上。弗洛伊德说梦包含被压抑的性欲,而他是在用这个概念来观察和解码梦(顺便说一句,这不仅是本能理论或生物模型,而是表达阿芙罗狄蒂、厄洛斯、普里阿普斯和狄俄尼索斯-利贝的原型情节)。荣格说梦有戏剧结构,而他是在用戏剧的视角来解读梦。我们所看到的和我们如何看之间的这种混淆是思想效应的另一个例子。eidos最初指的是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以及我们用来看到它的方法。实际上,只有当我们用戏剧结构来看时,我们才能看到它。我们看到的是由原型支配的思想允许我们看到的东西。
荣格迈向戏剧的一步是他的另一文学之举。他再次迈出了一步,使心理学接近诗学。此外(为了让你震惊,请注意以下假设并以斜体表示):如果梦本质上是无条件的、自发的、首要的心理自然,而这种心理自然能展现戏剧结构,那么心灵的本质就是诗意的。要探讨人类本体论的根本,其真理、本质和自然,必须采用虚构模式并使用诗学工具。为了理解梦的结构,我们转向戏剧;创作(poiesis)是通往王道的王道。无意识产生戏剧,产生诗意虚构;它是一个剧场。
在1945年才出版的一部作品(CW 8)中,荣格列出了戏剧结构的四个阶段:场景陈述、剧中人物、剧情展开、剧情发展至高潮或危机、解决或解脱。我在此不重复这些内容;你可以自己阅读并享受其中。它富有指导意义,实用——但也可能误导。因为戏剧结构在荣格所设定的层面上并不准确:实际遇到的梦很少能清晰地分为四个阶段,因为梦主要是突兀而片段化或歇斯底里地膨胀和漫无边际地延长。此外,戏剧结构的概念在更深层次上是误导性的:梦主要是一个形象——oneiros(希腊语中的梦)意为“形象”而非“故事”(参见Berry关于梦中叙事与形象关系的讨论)。我们可以从叙事、寓言或戏剧的角度看梦,但它本身是一个形象或一组形象。当我们从中看到戏剧时,我们总是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自己的假设。
狄俄尼索斯假设为以不同方式看待梦提供了价值;它将以更有效的方式帮助我们重新认识狄俄尼索斯。
狄俄尼索斯因其歇斯底里而被贬低或颂扬。他变得仅仅代表阿波罗的对立面,[33] 因而在大众和学术界的心目中,成了疯狂的迈纳德、集体狂喜、失去界限、革命和戏剧性的象征。逻各斯(Logos)似乎必须从其他地方引入,例如阿波罗。但当荣格说梦具有戏剧结构时,他实际上是在说梦具有戏剧逻辑,即狄俄尼索斯式的逻各斯,这种逻各斯是剧场的逻辑。梦不仅是心理自然的表现,它还呈现了心理逻辑。(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第七部分提出了这种逻辑的部分语法。然而,他的工作也可以被视为将诗意修辞转变为病理机制的一种反常转变。弗洛伊德用来描述梦的工作方式——凝缩、移置、象征化等——正是诗歌表达的方式。)
我认为荣格所暗示的是:如果心理治疗要从内部理解做梦的灵魂,最好转向“剧场逻辑”。心灵的本质在其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中有一种特定的形式:狄俄尼索斯形式。狄俄尼索斯可能是通过绿色导管驱动花朵的力量,但这股力量并非无声无息。它有内在的组织结构。在心理学中,这种语言不是遗传学的,也不是生物化学地以DNA代码信息说话,而是直接用狄俄尼索斯自己的艺术形式——剧场诗学。这意味着梦并不是一个编码的信息,而是一种展示、一种Schau(展示),其中做梦者自己扮演一个角色或作为观众,因此总是参与其中。难怪亚里士多德将心理治疗(净化)置于剧场的背景下。我们的生活是梦境的表演;我们的病史从一开始就是原型意义上的戏剧;我们是神祇发声的面具(personae)。就像梦一样,内在幻想(我们在第二章更详细探讨)也具有剧场般的逻辑。荣格写道(CW 14: 706):
“一连串的幻想思想逐渐发展出戏剧性特征:被动过程变成了行动。最初它由投射的人物组成,这些形象像剧场场景一样被观察。换句话说,你睁着眼睛做梦。通常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只是享受这种内在娱乐……舞台上的表演仍然是背景过程;它不会触动观察者,而且它越不动人,这个私人剧场的宣泄效果就越小。正在上演的作品不仅仅希望被公正地观看,它想迫使观众参与其中。如果观察者意识到自己的戏剧正在这个内在舞台上演出,他就无法对剧情及其结局保持冷漠。他会注意到,随着演员一个个登场,剧情愈发复杂,他正被无意识召唤,无意识使这些幻想形象出现在他面前。因此,他感到被迫或被分析师鼓励参与到表演中。”
这一令人惊讶的文学类比引导我们回到古希腊和狄俄尼索斯剧场在治愈中的地位。患者进入被表演者的角色,成为演员。当我们将自己从观众席移到心灵的舞台上,成为虚构中的角色(即使是神一般的真理之声,也是一种虚构),随着戏剧的强化,净化(catharsis)就会发生;我们摆脱了对字面命运的执着,在扮演角色中找到自由,尽管这些角色是片面的、支离破碎的、狄俄尼索斯式的,从未完整却参与了一个整体的戏剧,并被记住为它的表演者。戏剧和其神祇的任务是要求以技艺和敏感性来扮演一个角色。将梦与戏剧和狄俄尼索斯联系起来意味着不将其与预言和阿波罗联系在一起。荣格的这一转变否定了将梦视为预言的方法,这种方法荣格本人也常常采用,即将梦解读为关于如何行为的预言信息:梦的解释作为日常生活指导。再次强调:不是信息;而是面具。
如果狄俄尼索斯逻辑的结构是戏剧,那么狄俄尼索斯逻辑的具体体现就是演员;狄俄尼索斯逻各斯是虚构的表演,自己成为一个仿佛存在的实体,其现实完全来自想象和它强加的信念。演员既是又不是一个人,是一个人和一个面具,分裂和统一——正如狄俄尼索斯被称为两面神。自我的分裂恰恰是自我真实存在的位置——这与莱因的观点相反。真实性在于不断的解体与非存在之间,一个总是分多个部分的存在,如同一个拥有完整演员阵容的梦。我们都经历身份危机,因为单一的身份是单神论思维的幻觉,它会不惜一切代价击败狄俄尼索斯。我们所有人的意识分散在身体的各个部分,游荡的子宫;我们都是歇斯底里的。真实性存在于幻象中,玩味它,从内部看透它,就像一个演员透过他的面具看透自己,只能以这种方式看到。
未能理解这种狄俄尼索斯逻辑,即我们的戏剧充满了形式和动态一致性,因为它们是由神祇参与的神话所编织的,会驱使人们走向外部。我们试图从一个脱离的观察者的视角看透正在发生的事情。于是我们有了彭透斯在他的树上,阿波罗式的分裂运动从歇斯底里中解脱出来,剥夺了逻辑的生命,也剥夺了生活的逻辑。两者都是疯狂的。
剧场的本质在于知道它是剧场,知道自己是在表演、扮演、模仿一种完全虚构的现实。因此,当狄俄尼索斯被称为灵魂之主时,这不仅意味着死亡和冥界奥秘的形而上学意义,还意味着他是心灵洞察力之主,是从心理视角看待一切事物为面具以看透一切。因为如果伪装对某种逻辑是必不可少的,那么看透便是其隐含之意。狄俄尼索斯逻辑必然是神秘的和转化性的,因为它将事件视为面具,要求通过深奥的过程来获得下一个洞见。正是他的逻辑赋予了他运动、舞蹈和流动的属性。他的视角不能静态地看待任何事物,也不能字面化地看待任何事物,因为一切都被文学性地转化为戏剧性的虚构。“全世界是一个舞台,我们都是由梦构成的材料”,伊丽莎白一世宫廷的心理学家如是说。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相信逻各斯(Logos)只能由奥林匹斯山的结构定义,由宙斯和雅典娜的孩子们、阿波罗或赫尔墨斯或萨图恩——作为形式、法则、系统或数学的逻各斯。但赫拉克利特说它像火一样流动;耶稣说它像爱。每个神都有其逻各斯,没有单一定义,但基本上是心灵创造宇宙并赋予其意义的洞察能力。这是对我们最糟糕词汇“意识”的古老说法。
狄俄尼索斯意识通过戏剧张力而非概念对立来理解我们故事中的冲突;我们是由悲剧而非二元对立组成的。狄俄尼索斯意识是通过模仿意识来理解我们的生活和世界的模式,认识到我们整个病史都是一种表演,“无论是悲剧、喜剧、历史剧、田园剧、田园喜剧、历史田园剧、悲剧历史剧、悲喜田园剧”[34],并且“心理学”意味着在这些特定虚构的命运中看到自己。
最后,从戏剧内部看待我们自己指的是戏剧和神话表演的宗教起源,这些表演我们用“行为”的面具来命名和执行。
历史化的必要性 弗洛伊德的关键发现是,那些向他讲述的故事实际上是被装扮成历史的心理事件,并被体验为回忆的事件。这是现代心理学中首次认识到独立于其他现实的心理现实。进一步而言,这是对记忆独立于历史、历史独立于记忆的认识。有未被记住的历史——遗忘、扭曲、否认、压抑;也有非历史的记忆——屏幕记忆、虚构的记忆,以及那些早期性创伤和原始场景的叙述,这些并未发生在字面上的历史过去。
历史与记忆的可分离性——记忆不是可靠的历史指南,可能会歪曲历史——对历史学家来说早已司空见惯。因此他们坚持客观的文献证据。没有文件,就没有事件。但历史并不是记忆的本质,记忆起源于呈现其产物为复制品,这为理解心灵、回忆和时间感打开了广阔的窗口。
对于柏拉图主义者来说,弗洛伊德重新发现了他们一直以来所说的并不令人惊讶。从《美诺篇》到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再到朱利奥·卡米洛的记忆艺术,直到瑞典borg、浪漫主义哲学和鲁道夫·斯坦纳,回忆不仅仅是对你我一生中发生的事实的记忆,印刻在心灵的蜡板上,通过联想链接存储和检索。对柏拉图主义者而言,记忆是所有知识的巨大潜力,不仅由事件之手书写,更由神祇的签名书写;所有形象和召唤它们的心灵活动都与上帝的心灵有着某种直接但模糊的关系。柏拉图意义上的回忆是穿越历史进入智识的过程。
为了准确起见,这种“记住从未发生的事情”应该正确地被称为想象,这种记忆就是想象力。古老的术语“Memoria”涵盖了这两者。它指的是一种活动和一个地方,今天我们称之为记忆、想象和无意识。[35] Memoria 被描述为一个巨大的大厅,一个储藏室,一个充满图像的剧院。记忆与想象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记忆中的图像是那些被赋予了时间感的,那种奇特的信念认为它们曾经发生过。
当记忆摆脱了必须发生的束缚,摆脱了成为历史记忆的需求时,这些记忆就变成了史前的形象,即原型。从 Memoria 的储藏室中唤起的事件在柏拉图的意义上是神话的——从未发生过但始终存在。[36] 它们永恒地存在于当下,不会被遗忘,不是过去;它们现在就在我们身边,正如弗洛伊德重新发现它们在当前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中运作一样。
进入这些纪念大厅的方式是个人化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入口,这使我们认为 Memoria 本身是个人的,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精神分析的沙发是一个这样的入口;诗人的笔记本、作家的书桌也是其他的入口。然而,特定图像的记忆性——比如七月海滩上穿着黄色太阳衣的小邻居女孩挖地道去中国;派对蛋糕中丢失的带血牙齿——正是这些图像,以及如此精确地选择、检索和叙述的图像,表明它们的本质内容是原型意义上的难忘。记忆赋予图像以可记性,通过添加过去的时间感使图像对我们来说更加“真实”,赋予它们历史现实。但历史现实只是灵魂意义的外衣,只是将原型的神秘和重要性适应于专注于历史事实的意识的一种方式。如果图像不以历史的形式出现,我们可能不会认为它是真实的。
因此,回忆是一种纪念,是我们生命对灵魂背景中图像的仪式性回忆。通过回忆,我们为现生活提供了一种纪念性的传说,一种创始的形象,就像在弗洛伊德的案例中,他们的记忆为他们当前的治疗和精神分析的创立提供了传奇背景。性创伤确实“发生”了——但在想象中——并且作为仪式性的纪念,作为建立弗洛伊德主义机构及其教义、崇拜和祭司阶层的创始传说,它们一直在发生。
我需要回忆我的故事,不是因为我需要了解自己,而是因为我需要在一个我可以认为是“我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我也害怕这些故事,因为通过它们,我可能会被发现,我的想象基础暴露无遗。压抑内置于每个故事中,是对故事本身的恐惧,是对神话中神祇接近的恐惧,这些神话是我存在的基础。因此,治疗的艺术需要巧妙处理记忆和个人病史,以便真正帮助患者建立自我。因此,在治疗中引入伟大神话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它们是用虚构的基础模式解读个人历史的方法。
自弗洛伊德以来,心理治疗的内容一直是记忆。然而,如果这些内容实际上是纪念性传说,那么心理治疗实际上已经从事于神话创造(mythopoiesis),就像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治疗之父可能是弗洛伊德,但其母是 Mnemosyne,Memoria,缪斯的母亲,她的第十个、无形的女儿一定是 Psyche。
心理治疗最初旨在治愈记忆。治疗的第一步发生在弗洛伊德让记忆摆脱了其作为历史的概念——Mnemosyne 对某个特定女儿 Clio 的认同。第二步则是通过认识到记忆是图像来治愈记忆对其回忆的执着。记忆在想象中得到治愈。最后一步发生在我们认识到记忆和回忆通过她的女儿们以沉思和想象的方式继续进行,因此心理治疗鼓励这种沉思活动,它将记忆解放为图像。当我们沉思一个记忆时,它变成了一幅图像,抛弃了字面的历史事实,摆脱了因果链条,并打开了艺术创作的素材。治疗的艺术就是治愈成艺术。当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
我们来到这一点是从弗洛伊德的关键发现开始的,即 Memoria 的产物在他的病例中呈现为历史的复制品。为什么心灵需要用过去的服装来包装体验,仿佛它是历史?为什么心灵要历史化?[37] 历史化对灵魂有什么作用?
在我看来,这是从弗洛伊德对记忆“历史虚假”的洞察中产生的最重要的心理学问题。因为这种“虚假”无非是心灵自身的“历史化”活动。心灵本身创造了完全是虚构的历史。我们不仅仅是在制造历史,而是在过程中编造历史。亨利·科尔宾一直坚持认为历史在灵魂之中(而不是我们在历史中)。历史创造是一个沉思、诗意的过程,由 Clio 自主、原型地进行,向我们呈现仿佛是事实的故事。我们无法超越历史,不是因为我们不能走出时间或逃避过去,而是因为我们总是在灵魂中,受其沉思
我们无法超越历史,不是因为我们不能走出时间或逃避过去,而是因为我们总是在灵魂中,受其沉思的支配。历史的必然性并不是历史决定论——被困在历史的客观痕迹中被拖着走。相反,历史的必然性意味着我们被困在我们的故事中,灵魂的历史、悲剧、喜剧,以及它将主体性形塑为历史的需求。
心灵为何需要历史化? 心灵为何需要用过去的服装来包装体验,仿佛它是历史?为什么心灵要历史化?这对灵魂有什么作用?
在我看来,这是从弗洛伊德对记忆“历史虚假”的洞察中产生的最重要的心理学问题。因为这种“虚假”无非是心灵自身的“历史化”活动。心灵本身创造了完全是虚构的历史。我们不仅仅是在制造历史,而是在过程中编造历史。亨利·科尔宾一直坚持认为历史在灵魂之中(而不是我们在历史中)。历史创造是一个沉思、诗意的过程,由 Clio 自主、原型地进行,向我们呈现仿佛是事实的故事。我们无法超越历史,不是因为我们不能走出时间或逃避过去,而是因为我们总是在灵魂中,受其沉思的支配。
历史与灵魂的关系 历史的必要性不是被历史的客观痕迹所束缚,被迫随波逐流;而是我们被困在我们的故事中,灵魂的历史、悲剧和喜剧,以及它形成自身主体性的需求。历史的必然性意味着我们总是通过故事来理解自己,这些故事是灵魂构建其自我意识的方式。
沉思与艺术 因此,回忆是一种纪念,是我们生命对灵魂背景中图像的仪式性回忆。通过回忆,我们为现生活提供了一种纪念性的传说,一种创始的形象,就像在弗洛伊德的案例中,他们的记忆为他们当前的治疗和精神分析的创立提供了传奇背景。性创伤确实“发生”了——但在想象中——并且作为仪式性的纪念,作为建立弗洛伊德主义机构及其教义、崇拜和祭司阶层的创始传说,它们一直在发生。
我需要回忆我的故事,不是因为我需要了解自己,而是因为我需要在一个我可以认为是“我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我也害怕这些故事,因为通过它们,我可能会被发现,我的想象基础暴露无遗。压抑内置于每个故事中,是对故事本身的恐惧,是对神话中神祇接近的恐惧,这些神话是我存在的基础。因此,治疗的艺术需要巧妙处理记忆和个人病史,以便真正帮助患者建立自我。因此,在治疗中引入伟大神话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它们是用虚构的基础模式解读个人历史的方法。
自弗洛伊德以来,心理治疗的内容一直是记忆。然而,如果这些内容实际上是纪念性传说,那么心理治疗实际上已经从事于神话创造(mythopoiesis),就像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治疗之父可能是弗洛伊德,但其母是 Mnemosyne,Memoria,缪斯的母亲,她的第十个、无形的女儿一定是 Psyche。
心理治疗最初旨在治愈记忆。治疗的第一步发生在弗洛伊德让记忆摆脱了其作为历史的概念——Mnemosyne 对某个特定女儿 Clio 的认同。第二步则是通过认识到记忆是图像来治愈记忆对其回忆的执着。记忆在想象中得到治愈。最后一步发生在我们认识到记忆和回忆通过她的女儿们以沉思和想象的方式继续进行,因此心理治疗鼓励这种沉思活动,它将记忆解放为图像。当我们沉思一个记忆时,它变成了一幅图像,抛弃了字面的历史事实,摆脱了因果链条,并打开了艺术创作的素材。治疗的艺术就是治愈成艺术。当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
总结来说,这段文本探讨了记忆与想象之间的微妙关系,强调了心理治疗中的神话创造和沉思过程。它揭示了心灵如何通过虚构的历史来构建自我,并提出了治疗的新视角:通过沉思和想象来解放记忆,使它们成为更具创造性和疗愈性的材料。
有人认为,我承认自己也曾持有这种观点,即把事件放在过去是一种防御性举措。它显示了分裂的情感:一个人无法承受羞耻感,因此将它置于过去时态。当我这样说:“我以前对我的前任分析师撒谎;我以前自慰;我以前听到声音,但现在已经不再如此”,这在我和行为之间建立了一种距离。通过将丑闻置于过去,它不再如此紧密地压迫我。我否认了它。历史化是一种掩盖。
但我现在认为这些进入历史的举动是脱离现实的一种方式。
称之为防御会让我们回到指责自我(ego)不站出来、分裂、不承担责任的状态。然而,做出这些举动的不是自我,而是心灵(psyche)。它自发地进行历史化,甚至在梦中也是如此。我相信,它是这样做以获得某种特定的距离,作为将行为与现实分离的一种手段。说谎、自慰、幻听成为心理事件而非自我事件,成为反思的对象而不是控制的对象。它们现在变得不那么情绪化和个人化,更具有集体性和普遍性,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而不是报告。因为它们被否认了,它们从真实的忏悔进入了历史虚构,在那里可以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
在这种意义上,历史的掩盖是为了谨慎起见,保持事件完整但移开,如同在一个玻璃容器中,可以对其思考而不必认同。它仍然是我的罪行,但这个罪行不再是“我”。我可以围绕它移动,而如果它发生在当下,我会处于它的摆布之下,没有洞察力,只有责备和防御。分析中的过去时态转变表明心灵希望进行分析。这种转变是一种自我疗愈的尝试,将伤口包裹在客观事实的光环中,以便能够更少痛苦地处理。心灵将事件置于另一个时间,以便用另一种风格来处理,例如我们处理任何历史事件的方式,带着某种尊重、困惑的好奇心和冷静的探究——最重要的是收集其文化背景。历史化较少是心理防御的标志,而是心灵摆脱自我主宰的表现。
此外,历史化将事件置于另一种类型中。既不是此时此刻,也不是从前,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然而,这个“之间”在历史上有一个精确的位置,一个放在那里的事件可能需要按照那个历史时期的风格来处理。
并非所有以梦境形象和症状出现的心理情结都要求最新的治疗方法。我有一部分生活在过时的故事中,这些故事甚至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它们可能会对罗尔夫疗法和埃萨伦感到反感,甚至可能昏倒、发作虚脱或陷入怠惰,如果被迫“度过周末”的话。有些部分仍然生活在一个边疆的原教旨主义堡垒中,或者在革命前的凡尔赛宫,或者表现出十九世纪殖民主义的态度,或者是弗洛伊德维也纳那种隐蔽的软装色情。心灵用来告诉我们我们在哪里的历史虚构也告诉我们所需的治疗类型。根据夏科、珍妮和弗洛伊德的经典定义,完全发展的歇斯底里症最适合出现在那个历史背景下,如果它出现在当代患者身上,那个历史背景也会随之重现,包括其令人窒息的舞台布景。症状是一种进入历史的方式:其他时代,其他抱怨。历史也是进入症状的一种方式。
关于历史化还有更多要说的。为什么历史主要关于国王、决定性的战役和宣言,伟大的发明、时代和帝国?过去被呈现为一种纪念碑,那些载入史册的事情,使我们以为只有重要的事情才会被历史化,给予历史的尊严。历史增强了尊严。当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转向过去时,[38] “这是他们对尊严的关注;过去是使现在显得有尊严的手段。我们通过历史化赋予生活中事件一种尊严,这种尊严是它们在同时代中无法获得的。这里的历史化将事件向“从前”推进了一半,朝向神圣和永恒。任何琐碎的个人事件,如拿破仑的早餐、路德的放屁,一旦被历史化,立即获得了另一种意义,回响着隐喻,从描述转变为象征。历史因其将事件搬上历史舞台而赋予尊严,从而使其变得悲剧性、史诗般和富有想象力。然而,历史学家常常失去了他们工作的想象力功能。对他们来说,历史是一个由数百名工人在黑暗机库中组织数百万零件建造的巨大超音速复杂体。但一旦将其推出跑道,它便成为一个图像,从一开始就是。螺丝和螺栓消失在银色的幻象中。
这种方法使病史重获生机。我的故事是一堆灰色复杂的螺丝和螺栓,所有的金属沉闷都在于什么错了谁对,然而在这个病史中,是我的形象,我的尊严,我的纪念碑。而且它本身就是历史:我的母亲也有母亲,她的背后是一个民族的祖先之流;今天与我斗争的儿子,明天也将如此。我的个人记录的每一部分同时也是社区、社会、国家和时代的记录。没有哪一部分是我的个人历史,不同时也是更广泛背景下的历史。
历史化的深层意义 为什么历史主要围绕国王、决定性的战役和宣言,伟大的发明、时代和帝国展开?过去被呈现为一种纪念碑,那些载入史册的事情,使我们以为只有重要的事情才会被历史化,给予历史的尊严。历史增强了尊严。当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转向过去时,[38] “这是他们对尊严的关注;过去是使现在显得有尊严的手段。我们通过历史化赋予生活中事件一种尊严,这种尊严是它们在同时代中无法获得的。这里的历史化将事件向“从前”推进了一半,朝向神圣和永恒。任何琐碎的个人事件,如拿破仑的早餐、路德的放屁,一旦被历史化,立即获得了另一种意义,回响着隐喻,从描述转变为象征。历史因其将事件搬上历史舞台而赋予尊严,从而使其变得悲剧性、史诗般和富有想象力。
然而,历史学家常常失去了他们工作的想象力功能。对他们来说,历史是一个由数百名工人在黑暗机库中组织数百万零件建造的巨大超音速复杂体。但一旦将其推出跑道,它便成为一个图像,从一开始就是。螺丝和螺栓消失在银色的幻象中。
这种方法使病史重获生机。我的故事是一堆灰色复杂的螺丝和螺栓,所有的金属沉闷都在于什么错了谁对,然而在这个病史中,是我的形象,我的尊严,我的纪念碑。而且它本身就是历史:我的母亲也有母亲,她的背后是一个民族的祖先之流;今天与我斗争的儿子,明天也将如此。我的个人记录的每一部分同时也是社区、社会、国家和时代的记录。
症状与历史的交织 症状是一种进入历史的方式:其他时代,其他抱怨。历史也是进入症状的一种方式。例如,根据夏科、珍妮和弗洛伊德的经典定义,完全发展的歇斯底里症最适合出现在那个历史背景下,如果它出现在当代患者身上,那个历史背景也会随之重现,包括其令人窒息的舞台布景。因此,历史化的心理情结不仅反映了个体的心理状态,还揭示了更广泛的文化和社会背景。
介于现实与过去的中间地带 并非所有以梦境形象和症状出现的心理情结都要求最新的治疗方法。我有一部分生活在过时的故事中,这些故事甚至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它们可能会对罗尔夫疗法和埃萨伦感到反感,甚至可能昏倒、发作虚脱或陷入怠惰,如果被迫“度过周末”的话。有些部分仍然生活在一个边疆的原教旨主义堡垒中,或者在革命前的凡尔赛宫,或者表现出十九世纪殖民主义的态度,或者是弗洛伊德维也纳那种隐蔽的软装色情。心灵用来告诉我们我们在哪里的历史虚构也告诉我们所需的治疗类型。
历史化的目的 历史化将事件置于另一个时间框架中,既不是此时此刻,也不是从前,而是介于两者之间。这个“之间”在历史上有一个精确的位置,一个放在那里的事件可能需要按照那个历史时期的风格来处理。历史化不仅是为了掩盖或否认,而是为了创造一种距离,使我们可以更冷静地反思和理解这些事件。它提供了一个空间,在其中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和重构自己的故事,赋予它们新的意义和价值。
恢复病史的活力 这种方法使病史重获生机。我的故事是一堆灰色复杂的螺丝和螺栓,充满了金属般的沉闷和琐碎的细节,然而在这堆细节中,是我个人的形象、尊严和纪念碑。我的母亲也有母亲,她的背后是一个民族的祖先之流;今天与我斗争的儿子,明天也将如此。我的个人记录的每一部分不仅是我的故事,也是社区、社会、国家和时代的记录。
总结 总之,这段文本探讨了历史化在心理治疗中的重要作用。它揭示了心灵如何通过将事件置于过去来获得一种特定的距离,从而能够更客观和冷静地反思和理解这些事件。历史化不仅仅是防御机制,更是心灵寻求自我疗愈和重构自我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个人故事不仅得到了重新诠释,还与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建立了联系,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尊严。
病史的意义 其含义是:如果历史赋予尊严,那么作为历史书写形式的病史也应如此。在我们的情况下,即使这历史是由左拉、热内、斯皮兰或狄更斯所写,病史也是我们人类尊严的一部分。即使它是一个堕落的故事,充满感伤,甚至被呈现为一系列完全字面的事实以用于临床诊断,病史因为它是历史,因此也是虚构,是一种进入想象的举动。
因为正是想象力给予了距离和尊严,使我们能够将事件视为图像来看待。想象力介于当下的世界与精神那难以察觉的永恒之间。历史背后是记忆女神 Mnemosyne(Memoria),即想象的母亲,是历史化的原型、独特的沉思过程,是心灵按照历史术语进行思考的方式。
历史是一种对自己进行沉思的方式,而病史作为一种表达克莉欧(Clio)的方式,是治疗专业人员和患者可以共同进行的一种疗愈性沉思。尽管它有时不成功,反而创造了堕落和诊断而不是超然和尊严,但这再次指出了故事在决定我们是谁方面的力量。然而,重新审视和提升我们自身形象的可能性存在于每个病史的事件中,如果我们学会将其作为虚构来阅读,并将其事件视为 Memoria 的形象,她需要被记住以便创造。
病史的礼物 我发现,那些从小就有故事感的人比那些没有故事经历的人更为健全,后者没有听过、读过、演过或编过故事。这里我指的是口头故事,主要依赖于语言——即使是独自默默阅读也具有口语的一面——而不是通过屏幕或图画书观看的故事。(我稍后会解释对文字而非视觉的偏好。)
早期接触故事能让人熟悉故事的有效性。人们知道故事能做什么,如何构建世界并将存在转化为这些世界。人们保持一种对想象世界的感知,相信它的现实存在,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可以进入和离开的,它总是伴随着田野、宫殿、地牢和等待的长船而存在。人们了解到世界是由语言而不是仅仅由锤子和电线创造的。
通过屏幕观看的故事不同,因为它们通过感知进入想象,强化了“感知图像和想象图像”之间的混淆。我们用感官感知图片;我们用想象来形成图像。或者正如爱德华·凯西 [39] 所说:图像是我们看东西的方式,而不是我们看到的内容。我们可以将图片视为图像,电影中的图片也可能被想象成图像;但这些图像通常仍与其首次出现的视觉环境相连。然而,词句形成的图像是想象的直接产物,随后可能以模拟感知的方式将其视觉化(如将音乐场景或小说中的角色面孔、地点视觉化)。但词句图像的本质在于它们脱离了可感知的世界,并使人从这个世界中解脱出来。它们将心灵带回家,回到其诗意的基础,回到想象的世界。
弗洛伊德再次发现了感知图像和想象图像之间的区别。实际的图片——周六下午在床上的父母——并不具备故事和《原始场景》中图像那样的回忆力量和症状制造力。引用凯西的话:创伤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我们看待发生的方式。创伤不是病理事件,而是病态化的图像,一个变得“无法忍受”的图像,正如洛佩兹-佩德拉扎所说。
如果我们的疾病是因为这些无法忍受的图像,那么我们康复的原因也在于想象力。诗性即治疗。
总结 总之,这段文本探讨了病史在心理治疗中的重要性和意义。它强调了病史作为一种历史写作形式,不仅是对个体经历的记录,更是通过想象力赋予个体尊严和距离的方式。通过理解病史中的故事和图像,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和提升自我形象,实现心灵的治愈。此外,文本还讨论了早期接触故事对个人成长的重要性,以及口头故事相对于视觉故事的优势,指出文字图像更能激发想象力,帮助人们摆脱现实世界的束缚,进入想象的领域。最后,作者提到弗洛伊德对感知图像和想象图像区别的发现,进一步强调了想象力在治疗中的关键作用。
早期故事对想象力的塑造 那些从小就有故事经历的人,他们的想象力得到了锻炼,成为一种活动。他们不仅能够思考、感受、感知或学习生活,还能想象生活。并且,他们认识到想象力是一个可以存在的地方,一种存在的方式。此外,他们遇到了病态化的图像,这些幻想人物有的残缺不全、愚蠢可笑、性方面令人厌恶、暴力残忍,或是无所不能地美丽诱人。治疗是重新激发和锻炼想象力的一种方式。整个治疗过程就是这种想象力的锻炼。它重新拾起了讲故事的口头传统;治疗重新叙述了生活。当然,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童年,因为那是我们社会和个人放置想象力的地方。[40] 治疗必须关注我们内心的幼稚部分,以重新创造和锻炼想象力。
理性主义与想象力的对立 坚持理性主义和联想主义心理理论以及实证主义人类理论的人会争辩说,幻想太多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行为,而治疗的任务恰恰与我所描述的相反。他们认为,治疗应该是逐渐削减想象力,并使其服务于现实目标。他们说,使一个人发疯的正是被幻想淹没。过多的故事,故事与历史混淆,现实消失了。
但像玛丽·沃特金斯在其开创性的著作《觉醒之梦》中敏感讨论的那样,富有想象力的治疗学派直接进入幻想。他们非常字面地理解治疗师是“故事工作者”。不幸的是,这可能导致他们忽视个案史,仅仅将其视为外在的东西,忘记了这段历史本身也是一种想象力的体现;其中的所有人物,包括那些始终存在的创伤性人物——父母,不是记忆中的图片,而是记忆女神 Memoria 的形象,带有原型回响,是我家谱神话中的始祖,继续通过他们引发的幻想和情感来孕育我的灵魂。个案史不仅是需要摆脱的障碍,它也是一个清醒的梦境,能带来与任何进入龙洞或漫步天堂花园一样多的奇迹。只需将生命的每一句话句都比喻化,将过去的每一个画面都视为一个图像。
心理学中的个案史 最终,我们认识到心理学中的个案史是一个真正的心理事件,是对灵魂的真实表达,是由心灵的历史化活动创造的虚构,而不是由医生创造的。这种叙事形式对应于通过深度分析,灵魂在我们这个时代重新浮现。正如深度心理学发明了一种新的从业者和患者类型,一种新的语言、仪式风格和爱的形式,它也塑造了一种新的故事类型,既不是传记,也不是医学记录,也不是忏悔见证,而是一段关于灵魂内在运作的时间叙事,一段关于记忆、梦想和反思的历史,有时伪装成经验现实,但不一定如此。无论谁写它们,它们仍然是灵魂的文件。
孤独的分析师在他的灯光昏暗的书房里,社工不停地吸烟,在压力下打字——即使这些故事从未出版也无人阅读,写作的冲动本身就是一种心理学姿态,本身就是一种讲述。因为这种新的虚构形式带着强烈的冲动进入了我们的时代。我们想把它记录下来;有太多的事情要讲述。这些琐碎的事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历史现在正在灵魂中发生,而灵魂再次进入了历史。治疗师是新的历史学家。[41]
在这个意义上,个案史对于深度心理学至关重要。它们获得我们的关注不是作为经验基础或医学模式的残留,也不是作为展示某个理论家观点的范例。它们是主观现象,是灵魂的故事。它们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其主角,即你和我。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叙事,一种文学虚构,通过将其置于故事中,使我们的生活从对外部世界的投射性痴迷中解脱出来。它们使我们从现实的虚构转向虚构的现实。
认识自己与灵魂塑造 它们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在世界的混乱中认识到自己一直参与并将继续参与灵魂塑造,其中“制造”回归到其原始含义 poiesis(诗性创造)。灵魂塑造作为一种心理 poiesis,是通过语言的想象力创造灵魂。[43] 或许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去接受分析并不是为了被爱、治愈,甚至也不是为了“认识你自己”。或许我们去是为了得到一个个案史,被编入一个灵魂故事,并获得一个可以依此生活的剧情。这就是个案史的礼物,是在神话中找到自己的礼物。在神话中,神与人相遇。
总结 总之,这段文本探讨了早期故事对个人想象力的深远影响,以及个案史在深度心理学中的核心地位。它强调了想象力的重要性,如何通过治疗重新激发和锻炼想象力,使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重构自己的生活。同时,文本还揭示了个案史不仅是记录事实的工具,更是灵魂的真实表达,是个人与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建立联系的重要途径。通过这种方式,个案史帮助人们超越现实的束缚,进入想象的世界,实现自我认知
G. Papini 的文章《拜访弗洛伊德》(“A Visit to Freud”)重新发表在《存在心理学与精神医学评论》(Review of Existential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第9卷第2期(1969年),第130-134页。 J. Hillman,《重塑心理学》(Re-Visioning Psychology),纽约:Harper & Row,1975年。 CP 3,“个案史”。关于弗洛伊德的个案作为文学的一些最新讨论,请参见 S. Marcus 的文章《弗洛伊德与多拉:小说、历史、病史》(“Freud und Dora. Roman, Geschichte, Krankengeschichte”),Psyche,1974年第28期,第32-79页;以及 L. Freeman 在其著作《安娜·O的故事》(The Story of Anna O.)中的“参考书目”,纽约:Walker,1972年。自 D. H. Lawrence 的《白色旅馆》(The White Hotel)以来,类似的讨论越来越多。 R. Fowler 编,《现代批评术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Modern Critical Terms),伦敦和波士顿: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年,“技巧”条目。 E. M. Forster,《小说的几个方面》(Aspects of the Novel),哈蒙兹沃思:企鹅出版社,1962年,第37-38页。 据说弗洛伊德临终前读的最后一本书是巴尔扎克的《驴皮记》(Peau de chagrin)。 引自 Forster,《小说的几个方面》,第54页。 引自弗洛伊德,CP 3: 24。弗洛伊德对患者防御机制的辩护(如胆怯和羞耻感)也使他有机会作为叙述者介入故事和读者之间。这种手法对讲故事至关重要:“在想象文学中,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联系性质是关键,而叙述者在这里变得重要。叙事有两个重叠的方面。一方面是内容问题,即材料的组合;另一方面是修辞问题,即如何向受众呈现叙事。”(Fowler,《批评术语》,‘叙事’条目) 参见我的《松散的结尾:原型心理学的主要论文》(Loose Ends: Primary Papers in Archetypal Psychology),纽约/苏黎世:Spring Publications,1975年,第196-198页,“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同样见于 CP 3。关于 Schreber 案例的最佳讨论和参考书目是 Roberto Calasso 为 Schreber 的《回忆录》意大利译本所作的附录(米兰:Adelphi,1974年)。 引自 Forster,《小说的几个方面》,第54页,出自 Alain(Émile Chartier)的《美的艺术体系》(Système des beaux-arts),巴黎:Gallimard 出版社,1920年,第314-315页。 Forster,《小说的几个方面》,第93-95页。 Fowler,《批评术语》。参见“情节”条目。 J. M. Baldwin,《哲学与心理学词典》(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纽约:Macmillan,1925年,“历史”条目。 A. J. Ayer,《经验知识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Empirical Knowledge),伦敦:Macmillan,1969年,第79页。 H. Vaihinger,《“仿佛”哲学:人类理论、实践和宗教虚构的系统》,C. K. Ogden 译,伦敦:Routledge & Kegan Paul,1935年;参见我《重塑心理学》一书中对“仿佛”虚构在原型心理学中的相关性讨论,第153页及以后。 探索分析师对个案的虚构视角模式的是 R. Schafer,《心理分析的现实愿景》(“The Psychoanalytic Vision of Reality”),国际精神分析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1970年第51期,第279-297页。Schafer 发现了四种基本的心理分析写作视野:喜剧、浪漫、悲剧和讽刺(他承认自己借鉴了 Northrop Frye 的观点,而 Frye 又借用了荣格的观点)。
W. Giegerich,《本体发生 = 系统发生?》(“Ontogeny = Phylogeny?”),《春天:原型心理学与荣格思想年刊》(Spring: An Annual of Archetypal Psychology and Jungian Thought),1975年,第118页。 参考文献补充说明 这些引用和参考文献展示了从不同角度对心理学、文学和哲学的交叉探讨。例如:
G. Papini 的文章 提供了关于弗洛伊德及其工作的重要历史背景。 J. Hillman 的《重塑心理学》 强调了通过想象力和象征手法重新理解心理现象的重要性。 弗洛伊德个案史的研究 展示了个案史作为文学作品的价值,以及它们如何揭示更深层次的心理过程。 R. Fowler 的《现代批评术语词典》 为理解叙事技巧和文学批评提供了理论框架。 E. M. Forster 的《小说的几个方面》 探讨了叙事结构和人物塑造在文学中的作用。 Alain(Émile Chartier)的《美的艺术体系》 涉及美学和艺术理论,为理解文学与心理学的关系提供了哲学基础。 H. Vaihinger 的《“仿佛”哲学》 探讨了虚构在人类认知和行为中的作用,对原型心理学有重要影响。 R. Schafer 的《心理分析的现实愿景》 分析了心理分析师如何通过不同的视角来理解和解释患者的个案。 W. Giegerich 的文章 探讨了个体发展与集体无意识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了对心理现象的理解。 这些文献共同构成了一个跨学科的视角,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心理学、文学和哲学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深度心理学和原型心理学领域。
总结 总之,这段内容引用了多篇重要的学术文献,涉及心理学、文学批评和哲学等领域。它展示了如何通过文学和哲学的视角来理解心理现象,特别是弗洛伊德的个案史及其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这些文献不仅提供了理论支持,还为我们理解人类心灵的复杂性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资料。 我的《论老者意识》(“On Senex Consciousness”),发表于《春天:原型心理学与荣格思想年刊》(Spring: An Annual of Archetypal Psychology and Jungian Thought,1970年),第146-165页;重印于《老者与青年》(Senex & Puer),统一版第3卷(UE 3)。关于从心理学视角看土星,参见 A. Vitale 的文章《土星:父亲的转变》(“Satur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ather”),收录于 P. Berry 编辑的《父亲与母亲:五人手稿文集》(Fathers and Mothers: Essays by Five Hands),纽约/苏黎世:Spring Publications,1990年,第5-39页。 P. Berry,《梦的方法》(“An Approach to the Dream”),收录于她的《回声的微妙身体:对原型心理学的贡献》(Echo’s Subtle Body: Contributions to an Archetypal Psychology),康涅狄格州普特南:Spring Publications,2008年。 R. Fowler,《现代批评术语词典》(Critical Terms),英雄条目。 关于土星和简化论,参见 P. Berry 的《论简化论》(“On Reduction”),出处同上,以及我的《“否定”的老者意识及其文艺复兴解决方案》(“The ‘Negative’ Senex and a Renaissance Solution”),发表于《春天:原型心理学与荣格思想年刊》(1975年),第88页及以后。 A. M. Patterson,《赫尔莫根尼斯与文艺复兴:七种风格理念》(Hermogenes and the Renaissance: Seven Ideas of Style),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0年。 J. Hillman,《自杀与灵魂》(Suicide and the Soul),康涅狄格州普特南:Spring Publications,1997年,第77-79页。 CW 15 CW 8: 477, 809, 451, 843, 457, 303;CW 7: 44, 75, 206;CW 16: 91, 307, 335, 464;CW 10: 29, 627。27 H. H. Walser,《早期精神分析悲剧》(“An Early Psychoanalytical Tragedy”),发表于《春天:原型心理学与荣格思想年刊》(1974年),注释248。 关于荣格的思想与其个案史的关系,参见 A. Jaffé,《荣格生活中的创造性阶段》(“The Creative Phases in Jung’s Life”),发表于《春天:原型心理学与荣格思想年刊》(1972年),第162-190页。 CW 10: 1042。另见 CW 9: 319f,进一步解释荣格为何不按常规方式讨论个案史。 关于荣格与赫尔墨斯,参见 D. C. Noel,《面纱下的卡比尔:C. G. 荣格的男性自画像》(“Veiled Kabir: C. G. Jung’s Phallic Self-Image”),发表于《春天:原型心理学与荣格思想年刊》(1974年),特别是第235-240页。 G. Clifford,《寓言的转变》(Transformations of Allegory),伦敦:Routledge,1974年。 R. Fowler,《现代批评术语词典》(Critical Terms),寓言条目。 关于狄俄尼索斯/阿波罗对比的历史,参见 J. Ritter 编辑的《哲学历史词典》(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巴塞尔/斯图加特:Schwabe,1971年,第一卷,“阿波罗式的/狄俄尼索斯式的”。关于荣格对狄俄尼索斯的看法,参见我的《荣格著作中的狄俄尼索斯》(“Dionysus in Jung’s Writings”),发表于《春天:原型心理学与荣格思想年刊》(1972年),重印于《神话人物》(Mythic
关于狄俄尼索斯/阿波罗对比的历史,参见 J. Ritter 编辑的《哲学历史词典》(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巴塞尔/斯图加特:Schwabe,1971年,第一卷,“阿波罗式的/狄俄尼索斯式的”。关于荣格对狄俄尼索斯的看法,参见我的《荣格著作中的狄俄尼索斯》(“Dionysus in Jung’s Writings”),发表于《春天:原型心理学与荣格思想年刊》(1972年),重印于《神话人物》(Mythic Figures),统一版第9卷(UE 9.1)。关于阿波罗-狄俄尼索斯,参见我的《分析的神话》(The Myth of Analysis),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西北大学出版社,1972年,以及 G. Holton,《在狄俄尼索斯和阿波罗之间》(“On Being Caught between Dionysians and Apollonians”),《达芬奇》(Daedalus),1974年夏季号,第65-81页。关于希腊神狄俄尼索斯本身,不可或缺的作品是 W. F. Otto 的《狄俄尼索斯》,R. B. Palmer 译,纽约/苏黎世:Spring Publications,1981年,以及 K. Kerényi 的《狄俄尼索斯》,R. Manheim 译,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6年。 现代作品中关于这一主题的内容往往具有误导性,因为它们未能充分描绘狄俄尼索斯或阿波罗的形象,这正是因为这些作品本身被这些神祇的对立面所吸引,从而表达了原型化的刻板观点。例如,P. E. Slater 的《赫拉的荣耀:希腊神话与希腊家庭》(The Glory of Hera: Greek Mythology and the Greek Family),波士顿:Beacon Press,1968年;M. K. Spears 的《狄俄尼索斯与城市:二十世纪诗歌中的现代主义》(Dionysus and the City: Modernism in Twentieth-Century Poetry),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正如我在关于荣格的狄俄尼索斯的文章中指出的,我们对这位神祇的一般印象是尼采式的、沃坦式的、日耳曼式的。关于这种日耳曼化的狄俄尼索斯的材料汇编,参见 J. H. W. Rosteutscher,《狄俄尼索斯的回归》(Die Wiederkunft des Dionysos),伯尔尼:Franke Verlag,1947年。
参考文献补充说明 这些引用展示了从不同角度探讨原型心理学、神话学和哲学交叉领域的学术文献。例如:
G. Clifford 的《寓言的转变》 提供了关于寓言及其演变的深入研究。 R. Fowler 的《现代批评术语词典》 为理解文学批评中的英雄和寓言概念提供了理论框架。 W. F. Otto 和 K. Kerényi 的《狄俄尼索斯》 是研究这位古希腊神祇的经典之作,揭示了其在文化和心理层面的深远影响。 P. E. Slater 和 M. K. Spears 的作品 虽然存在局限性,但也为我们理解狄俄尼索斯和阿波罗的现代诠释提供了背景。 这些文献共同构成了一个跨学科的视角,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原型心理学和神话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深度心理学领域。
总结 总之,这段内容引用了多篇重要的学术文献,涉及心理学、神话学和哲学等领域。它展示了如何通过神话和哲学的视角来理解心理现象,特别是荣格对狄俄尼索斯的理解及其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这些文献不仅提供了理论支持,还为我们理解人类心灵的复杂性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资料。
W.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 记忆与想象之间的经典区别仅在于“被记住”的图像具有时间的特质。这一区分源自亚里士多德,参见 F. Yates,《记忆的艺术》(The Art of Memory),伦敦:Routledge & Kegan Paul,1966年,第32页及以后。 当萨鲁斯特解释神话的本质时,他写道:“这一切并不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发生的,而是始终如此。”出自 Sallustius,《论神与宇宙》(Concerning the Gods and the Universe),由 A. Darby Nock 编辑,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26年。 参见 K. R. Popper,《历史主义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伦敦:Routledge & Kegan Paul,1969年。Popper 首次探讨了历史作为一种心理需求的问题。但他讨论的是特定的历史观和使用方式:历史主义。我们进一步提出问题:为什么会有历史模式? P. Burke,《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感》(The Renaissance Sense of the Past),伦敦:Edward Arnold,1969年,第105页。 E. S. Casey,《朝向想象的现象学》(“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Imagination”),《英国现象学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Phenomenology),1974年1月号,第10页。 我在我的文章《放弃儿童》(“Abandoning the Child”),收录于《埃拉诺斯年鉴》(Eranos Yearbook)第40卷(1971年),详细讨论了想象力与童年之间的关系。 病例史写作中的差异遵循古老的传统。社会现实主义对卑微和平凡细节的兴趣要求低风格的写作,描述日常生活的事物。荣格风格则是“高”的,它具有英雄、部落和神话事件的原型共鸣;它遵循古典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观念,这些观念“排除了‘低’的人、事物或词语”(参见 Burke 的上述引用)。 “灵魂塑造”这一术语及其发生在“世界的山谷”中的概念来自约翰·济慈,详见我在《分析的神话》(The Myth of Analysis)和《重新构想心理学》(Re-visioning Psychology)中的讨论。 关于通过语言进行灵魂塑造和心理治疗的精彩阐述,参见 P. L. Entralgo,《古典时代的语言疗法》(The Therapy of the Word in Classical Antiquity),由 L. J. Rather 和 J. M. Sharp 翻译,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0年。 图像的潘多拉魔盒: 荣格对“认识你自己”的贡献
没有神祇的参与,是不可能正确谈论神祇的。
这些段落涵盖了文学、哲学、心理学和神话学等领域的多个重要主题,引用了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帮助我们理解记忆与想象的区别、神话的本质、历史模式的心理需求以及“灵魂塑造”概念的起源和意义。特别是最后一句话强调了在讨论神祇时,神祇本身的不可或缺性,这反映了古代哲学中关于人类认知与神圣存在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
扬布里科斯
荣格的灵魅
当我们探究荣格对我们文化的具体贡献时,有一个美德在我看来尤为突出。荣格对我们的文化中最持久的心理需求——从俄狄浦斯到苏格拉底,再到哈姆雷特和浮士德——给出了明确回应:“认识你自己”。荣格不仅将这一格言作为自己生活的主旋律,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应对这个关于自我认知的根本问题。正是这种如何与自己相处的艺术或方法,作为所有心理学的基础动力,我们可以特别从荣格那里学到很多。因此,我希望在这里探讨的角度是,荣格的心理学方法是他给予我们最宝贵的礼物。
你可能还记得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这在荣格的自传中由安妮拉·雅菲(Aniela Jaffé)讲述。荣格被“源源不断的幻想”所淹没,这些幻想是一系列“心理内容和图像的洪流”。为了应对情感的风暴,他写下自己的幻想,并让这些风暴转化为图像。
你也记得这是何时发生的:这件事发生在与弗洛伊德决裂之后不久——以至于斯坦利·莱维(Stanley Leavy)[1] 建议说,在我即将提到的那个幻象中的莎乐美实际上就是伪装成的路·安德烈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Salomé),而以利亚则是弗洛伊德。在这个时候,荣格在精神上感到孤独。然而,在这种孤立中,他既没有转向新的团体,也没有转向有组织的宗教,更没有逃入精神病态或寻求传统活动、工作或家庭的安全感:而是转向了他的图像。当没有什么可以依靠时,荣格转向了内心视觉中的人格化图像。他进入了内心的戏剧,将自己投入到想象的虚构中,然后,或许是从那时起开始了他的疗愈——即使这被称为他的崩溃期。在那里,他找到了一个不再属于维也纳的地方,遇到了不再是精神分析同事的人物,并找到了一个不再是弗洛伊德的顾问。与这些个人化人物的相遇成为了他成熟命运的第一批人格化形象——荣格也正是这样描述我们在内省以“认识你自己”时遇到的人格化形象[2]。就在这个时候,在鸽子少女在一个关键梦中与他对话期间,荣格找到了自己的天职、心理信仰以及一种个性感[3]。从这一点开始,荣格成为心灵现实的伟大先驱倡导者。
这些段落详细描述了荣格在心理学领域的贡献,特别是他如何通过面对内心的形象来处理自己心理危机的过程。荣格不仅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重要性,还开发了一套具体的方法论,帮助人们进行自我探索和疗愈。这一过程不仅塑造了他的个人命运,也奠定了他在心理学领域的重要地位。
我们已经探讨了“如何”和“何时”,现在来讨论“什么”和“谁”。第一次幻象的内容是什么?荣格遇到了谁?自传中写道:
为了抓住这些幻想,我经常想象自己在进行一次陡峭的下降。我甚至尝试了几次到达最底部……这就像一次登月之旅,或者是一次进入虚空的下降……我有一种自己身处死者之地……另一个世界的感觉……我看到了两个身影,一位白胡子老人和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孩。我鼓起勇气,像对待真人一样接近他们,并认真倾听他们对我说的话。[4]
我详细引用这段文字,因为它揭示了方法的关键;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本指导手册。
荣格遇到的人物是:以利亚、莎乐美和一条黑蛇。不久之后,以利亚变成了菲莱蒙(Philemon),荣格这样描述他:
菲莱蒙是一个异教徒,他带来了埃及-希腊的氛围,带有诺斯替主义的色彩……菲莱蒙和其他我幻想中的人物让我深刻认识到,在心灵中有我不创造的东西,但它们自己产生并拥有自己的生命。[5]
以利亚、莎乐美、黑蛇和菲莱蒙带来的宇宙——这种“带有诺斯替色彩的埃及-希腊氛围”——正是能够支撑荣格所进行行为的背景。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荣格首先遇到的人物,通过与心灵力量建立个人关系,使他相信它们的心灵存在是真实的。这些人物流淌自希腊化世界及其对灵魅(daimons)的信仰。(Daimon 是这些人物在古希腊文中的原始拼写,后来由于基督教的观点,它们变成了恶魔(demons),而在积极意义上则被称为守护神(daemons)。)
荣格下到“死者之地”的旅程向他展示了其精神祖先,通过荣格,这些人开启了新的灵魅学和天使学。
这段文字详细描述了荣格在心理探索过程中遇到的具体人物及其象征意义,强调了这些人物对荣格思想形成的重要性。特别是这些人物所代表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以及它们如何帮助荣格理解心灵中的自主力量。
以荣格的方式“认识你自己”意味着要熟悉、敞开心扉并倾听这些灵魅(daimons),即去了解和辨别它们。进入内心的故事需要一种类似于开始写一部小说的勇气。我们必须与那些能够彻底改变甚至主宰我们思想和情感的人互动,既不指挥他们也不完全屈服于他们。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他们和我们都被编织成一个神话、一个情节,直到死亡将我们分离。这是一种罕见的勇气,它屈从于心灵现实的中间地带,在这里,事实的所谓确定性和虚构的幻象交换了衣裳。
为了提醒我们荣格人格化的这一举动是多么激进、震撼——神学上、认识论上、本体论上的变革——让我简单地重申一下西方宗教心理学对灵魅的通常评判。无论是东正教还是罗马天主教,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灵魅都不是好东西。它们是撒旦的世界、混乱和诱惑的一部分。几个世纪以来,重要的基督教神学家一直反对它们,将其与基督教欧洲中的蛇崇拜联系起来,并且根据《马太福音》的权威说法[6],它们是附身、疾病和魔法的源头。
这些形象究竟为何如此令人畏惧?如果我们回顾基督教兴起之前和同时期的世界——从荷马到柏拉图和戏剧家,再到普鲁塔克、普罗提诺、扬布里科斯,再到文艺复兴时期——灵魅是中间领域的形象,既不是完全超越的神祇也不是完全物质的人类,而且种类繁多,有益的、可怕的、传递信息的、调停的、指导和警示的声音(如苏格拉底的灵魅和狄奥提玛)。甚至连爱神厄洛斯(Eros)也是一个灵魅。
但我们的宗教文化通过教条的固化将灵魅妖魔化了。作为多神教异教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们必须被基督教神学否定和否认,这种神学将自身的压抑投射到灵魅上,称它们为否定和拒绝的力量。因此,荣格直接转向中间领域图像和形象的举动被视为异端、恶魔般的举动。他因幻想和情感而被迫进入的想象世界,在我们的宗教语言中早已被预判为恶魔,在临床语言中则被认为是多重人格或精神分裂症。然而,这种激进的想象力激活正是荣格“认识你自己”的方法。
这段文字深入探讨了荣格关于“认识你自己”的理念,强调了与内心深处的形象互动的重要性及其在个人成长和心理治疗中的作用。它还揭示了西方宗教文化对灵魅的看法如何影响了对荣格理论的理解,并解释了荣格方法的独特性和挑战性。
他在神学宗教和临床科学主义这两种正统之间的转变,在经验中重新确立了一个他称之为“心灵现实”的中间领域。荣格发现的这种心灵现实由虚构的形象组成,具有诗意、戏剧性和文学性。柏拉图的“中介”(metaxy)通过神话式的虚构来表达。弗洛伊德的虚构在他的个案史和宇宙起源理论中被掩盖;而荣格的虚构则在他的个人经历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弗洛伊德通过写关于别人的故事进入了文学想象;荣格则是通过将自己设想为“其他人”来进入文学想象。我们从弗洛伊德那里学到的是,这种文学想象是在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而我们从荣格那里学到的是,这种文学想象是在我们自身内部进行的。实际上,我们的心理生活是由诗意、戏剧性的虚构所构成的。我们的灵魂生活是一种想象的生活。
根据指导手册中的线索,我们已经得知如何重新建立传统上称为“灵魂”的第三领域——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荣格说,他对待遇到的人物“就像他们是真实的人一样。”关键在于“仿佛”(as though);这种比喻性的、仿佛真实的现实既不是字面上的真实(幻觉或街头上的行人),也不是虚幻的/不真实的(“仅仅是”虚构、投射,我作为“我”的一部分所创造的自我暗示的幻象)。在“仿佛”的意识中,它们是有声音、有形体、有动作和思想的力量,完全被感知但完全是虚构的。这就是心灵现实,它以灵魅(daimons)的形式出现。通过这些灵魅现实,荣格确认了灵魂的自主性。他自己的经验再次将灵魅领域与灵魂领域联系起来。自那时以来,灵魂和灵魅彼此暗示,甚至相互要求。
这段文字深入探讨了荣格对心灵现实的理解,强调了虚构形象在心理治疗和个人成长中的作用。它还揭示了荣格如何通过“仿佛”这一概念,超越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重新定义了灵魂和灵魅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人类心理中的重要地位。
内省 简要地,让我们来看一下内省的问题,以理解为什么荣格对“认识你自己”的方法不仅在哲学和神学上是激进的,而且也是心理学中的一个新且重要的步骤。
当你或我试图了解自己时,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方式呢?我们可以询问他人。我们可以进行测试:例如,投射性测试(如罗夏墨迹测验),用以探索我们内心的幻想;心理内容清单测试;以及像智力测试这样的比较性测试,这些测试根据他人的标准来评估我们的能力和技能。我们可以回忆;我们可以追溯并深入那些被遗忘和压抑的记忆。我们可以审视自己的行为,以及我们如何塑造了自己经历的一切——即自传。[8] 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意识状态,从柏拉图在其四种狂喜中所建议的方式,到现代的释放疗法,来解放我们“真实的自我”,使之摆脱日常的自我。我们可以去爱:因为正如一些人所认为的,只有在爱中,我们的自我才能变得可见和可知。(这最后一点意味着你无法完全或永远“认识你自己”,而只能揭示自己;我们可以被他人了解,但不能完全了解自己。)
这种多样化的答案揭示了原型心理学的一个前提,即对于所有主要的、原型类的问题,存在着多种答案,这取决于我们回答时所依据的神祇和神话主题,无论是冷漠的阿波罗式的、抽象的土星式的、爱之神还是狄俄尼索斯式的释放、英雄事迹还是赫菲斯托斯式的工艺品。似乎没有一种单一的方法可以“认识你自己”,即使心理学倾向于采用内省的方法。
这段文字探讨了内省的不同方法及其局限性,强调了荣格“认识你自己”理念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它还指出了原型心理学中对不同答案的开放态度,反映了人类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内省 内省与心理学的历史紧密相连。现代心理学或许源于内省的倾向,并且是对意识进行客观化和系统化的尝试,旨在实现对意识的冷静观察。我们可以在柏拉图的作品中找到内省的根源,例如《美诺篇》,当然还有苏格拉底的行为中。我们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也看到了内省作为方法的应用。从笛卡尔的“inspectio”到洛克和休谟,再到胡塞尔,内省构成了现代哲学心理学的基础。在这里,我暂且不讨论宗教中的灵性学科、虔敬主义、良心审查等领域的内省。
作为方法的现代内省始于卡尔·菲利普·莫里茨(1756-93),他将虔敬主义的自我观察方法转化为启蒙科学。这一方法在奥斯瓦尔德·库尔佩和维尔茨堡学派的工作中达到了顶峰。为了认识自己,了解灵魂,人们观察它的联想、意志和记忆的方式,感知、感觉、品味、情感,尤其是它的思考模式,即纯粹的、无形象的思维形式。
然而,这种方法的最大破产之处在于——否则它不会如此轻易地被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所取代——内省仍然局限于理性灵魂之中。它最终是唯我论的。我们永远无法走出自己的私人感受、思想、意志和回忆。它主要是一种对自我意识色调的探究。即使在今天,无论是在梅洛-庞蒂、尤金·根德林,还是罗杰·波尔那里,内省仍然是对笛卡尔自我的“inspectio”。或者用原型心理学的神话术语来说,这种方法是一种阿波罗-赫利俄斯(Apollo-Hellos)式的自我表演。
那么,对于深层的东西呢?我们能否从上方和阳光下审视它们?因此,即使在试图聚焦于直觉感受时,这也必然是一种阳光下的冷静观察。因此,浮现的情感以概念语言出现,如焦虑、内疚、绝望、敌意——这些抽象词汇缺乏形象。实际的病态身体被平滑并公式化为代表该身体的规范性词汇。这种将真实情感替换为概念化情感的做法,导致了在阿波罗阳光下干枯的结果,这是笛卡尔式内省过程的结果。或者,我们是否必须像荣格那样深入其中?
当你或我在面对关键的困惑时,是否可以通过内省找到问题的根源?能否通过内省到达绝望的底部或焦虑的源头?向内转时,我们常常一无所获。
这段文字探讨了内省的历史和发展,指出了其局限性,并强调了深入内心深处的重要性。它揭示了传统内省方法的局限,以及荣格提出的更深层次探索的必要性。
作家与角色的自主性 作家们知道他们无法内省他们的角色。场景自然而然地呈现,人物自行说话、进出。作家与他的角色之间的亲密关系很少有人能及,然而这些角色却以其自主性不断给他带来惊喜。此外,角色们并不关心“我”,而是关注他们所生活的世界,这个世界只是间接地与我——这个内省者相关。转向想象的行为并不是一种内省:它是一种负面能力,是有意地对他们保持怀疑的态度,并对自己作为作者的身份产生信念。作者的相对化——谁在创造谁,谁在书写谁——伴随着虚构模式,在积极想象的过程中,人们在失去控制和替他们说话之间摇摆不定。但内省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进一步的虚构行为才能做到。内省只会将人带回主体性的字面主义。我们对主体性的概念理解得如此字面化,以至于现在相信每个句子开头都有一个虚构的主体在工作,一个作为每个动词前缀的主体。但实际的工作是由动词本身完成的;它们在进行虚构,主动想象,而不是我在做。行动在于情节中,而情节是内省无法触及的,只有角色知道发生了什么。正如菲莱蒙教给荣格的,你不是心理戏剧的作者。
更重要的是,谁在进行内省?难道不是那个老“我”吗?我们如何内省这个内省者?我们如何相对化观察者并深入到试图了解的主体之下,以发现一种不被“我”所决定的心理客观性?
为了达到心理客观性,或荣格所说的客观心灵,我们首先需要心理对象,即那些无情阻碍自我道路的力量、强迫观念和突入意识的事物。这正是荣格如何描述情结如同神祇或灵魅,横亘于我们的主观意志之前[11]。情结不会回应忧虑、搜索队、带着标签的自然主义者。当注意力转向它们时,“小人物”(荣格对情结的称呼)会迅速躲进灌木丛中。同样,它们也不会通过简单的放松找到,仿佛只要我们躺下它们就会出现。放松的身体参照内省仍然停留在意志的语言中。(此外,如果一个形象或身体感觉只是我们已经意识到的内容的图解,那它仅仅是另一种媒介中的同一已知内容,是寓言而已。)深处的情结有其自身的身体和意志,这并不受制于自我的补偿法则。因此,人本主义疗法从未超越人类的本质,也无法脱离其主体性。整个存在主义程序,即人在探索自己或沉入自己后,通过下定决心来选择,都是基于一种忽略了“小人物”的内省。它们的观点往往在未被询问时才会显现,作为超出自我意识的访问或干扰。我们可以召唤天使吗?它们是否遵循补偿原则?
这段文字探讨了作家与其角色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了内省的局限性,并强调了荣格关于心理客观性和情结的观点。它指出了传统内省方法的不足,以及深入理解和处理潜意识力量的重要性。
内省的局限性 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尼采、狄尔泰和荣格都对常规内省的价值持严重怀疑态度。狄尔泰[12]坚持认为,内省永远不足以理解人性,而历史却能做到这一点。尼采写道:“直接的自我观察远远不够让我们学会如何认识自己。我们需要历史,因为过去通过无数渠道继续在我们身上流淌。”[13] 如果我们将尼采和狄尔泰所说的“历史”翻译为“集体无意识”,那么我们就接近了荣格对“认识你自己”的立场。
在这里,“认识你自己”意味着了解历史的无意识,特别是它如何在“我”——即“客观”的内省者本身中起作用。只要这个“我”是历史性的自我,无意识地反映并延续塑造它的历史,我们在内省中所发现的一切都将被塑造成我们自己的历史形象。我将被迫相信,我遇到的那些形象是“我”的一部分,是“我”的投射。我会正确地将它们评估为虚幻的影子,是我投下的阴影,并轻视它们。
但这样一来,我会错过进入“认识你自己”的第一步,而这一步正是这些自我映像所提供的——因为首先,它们是我的影子,描绘了我的历史处境。它们提供了认识历史的无数渠道(如荣格的齐格弗里德和他的圣经形象)的机会,这些渠道实际上决定了我的意识。
这里最重要的是认识到,这些“小人物”确实来自亡者之地。就像荣格的菲莱蒙和萨洛梅一样,它们是历史上传奇的人物,展示了文化在灵魂渠道中的运作。亡者之地是祖先的国度,走进我们心中的形象就是我们的祖先。即使不是字面上的血缘和基因传承,它们也是我们精神的历史先驱或原型,用祖先的文化赋予我们独特的灵性。
这段文字探讨了内省的局限性,并强调了历史和集体无意识在理解自我中的重要性。它指出了荣格关于“认识你自己”的观点,即要超越个人的主观经验,认识到历史和集体无意识对我们意识的深刻影响。
形象作为祖先的认知 在认识到形象作为祖先这一历史背景之后,我体验到了这些形象对我提出的主张。这是想象中的道德时刻。想象的道德性本质上并不在于我对所见灵魅的好坏判断,也不在于想象的应用(即如何将从形象中发现的内容转化为生活中的行动)。相反,这种道德性在于以宗教的态度认识这些形象,视它们为具有主张的力量。
荣格在他的一章中提出了这个伦理问题,我们已经引用过这一章节。他说:
我非常小心地尝试理解每一个形象……最重要的是,在实际生活中实现它们。这正是我们通常忽略的事情。我们让形象浮现,也许会感到好奇,但仅此而已。我们没有费心去……得出伦理结论……认为对形象的理解足够了,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对形象的洞察必须转化为一种伦理义务……这些形象……给人带来了巨大的责任。[14]
在这里,荣格将道德时刻归因于回应的自我,而我会进一步心理学化这个问题,问一问为什么在与形象相遇后,道德问题会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可能道德关注是由于这次相遇本身产生的,因此进入了荣格的叙述。[15] 正如这些想象中的人物带来了一种内在的命运感,它们也带来了对内在必然性和其局限性的意识。我们对他们感到负责,也为他们感到负责。一种相互关怀包裹着这种关系,或者正如古代所说,灵魅也是守护精灵。我们的形象是我们的守护者,我们也是他们的守护者。
从外部看,灵魅的出现似乎提供了伦理相对性:一个充满诱惑和冒险的乐园。
这段文字探讨了荣格关于形象和灵魅对个人内心的深刻影响,强调了理解这些形象的重要性以及它们所带来的道德责任。它揭示了人与内心形象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引发深刻的伦理思考。
伦理相对性的幻想 但这种伦理相对性的幻想暴露了一种尚未进入想象世界的意识,它无法从其形象内部“认识自己”。换句话说,每当有人提到“形象的混乱”和多神论时,伦理相对性的问题就会浮现,而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于形象所要求的献身精神。是它们——而不是我们——要求被精心雕琢成珠宝般的偶像;是它们要求仪式化的奉献,并坚持在我们行动之前咨询它们。形象不仅是道德和宗教的强烈源泉,也是艺术良知的体现。正如我们不是凭空捏造这些形象一样,我们也无法编造对它们的回应,而是由这些形象作为道德实例“教导”我们如何回应。当我们失去这些形象时,我们就变得道学气十足,仿佛形象中的道德变成了分离的、游离的内疚感,一种没有面孔的良心。
当一个形象被实现——被充分想象为一个不同于我自己的活生生的存在——它就成为了一个心理引导者(psychopompos),一个具有自身固有限制和必然性的灵魂向导。正是这个特定的形象,使得关于道德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概念性问题在实际与形象接触时显得微不足道。所谓的充满创造力的想象混乱被限制在其现象出现在特定形象中,那个具体且充满意义和意图的形象,在此时此地作为一个必要的天使出现,并教导手如何去描绘它,耳朵如何去聆听,心灵如何去回应。通过这种接触,揭示了一种形象的道德性。
源于想象的心理道德不再是通过同一个老康德式的自我及其英雄般对抗抽象二元论来实现的“新伦理学”。自我不再是道德所在之处,这种哲学立场曾将道德从想象中剥离,从而将其妖魔化。相反,灵魅(daimon)才是我们的导师,是我们的心灵引导者(spiritus rector)。
在这里,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和以利亚-菲莱蒙再次登场。正如自传中所述:
在我的幻想中,我与他[菲莱蒙]进行了对话,他说了一些我未曾有意识思考过的事情……他说我对待思想好像它们是我自己产生的,但在他看来,思想就像森林中的动物,或房间里的人,或天空中的鸟……是他教会了我心理客观性,心灵的现实性。[16]
这段文字探讨了形象在个人内心世界中的深刻影响,强调了理解这些形象的重要性以及它们所带来的道德责任。它揭示了人与内心形象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引发深刻的伦理思考。荣格通过与菲莱蒙的对话,进一步阐述了心理客观性和心灵现实性的概念。
荣格的积极想象方法 荣格在现代心理学中开创的积极想象方法是对经典内省问题的深刻回应,它改变了对人类、心灵以及“认识你自己”本质的理解。在弗洛伊德之前,“认识你自己”在心理学中意味着了解自我意识及其功能。然后,随着弗洛伊德的发展,“认识你自己”扩展为了解个人的过去生活,回忆起完整的一生。但到了荣格这里,“认识你自己”意味着一种原型的认知,一种灵魅的认知。这意味着要熟悉来自地理、历史和文化背景中的众多心理形象,超越个人身份的无数渠道。荣格之后,我无法假装了解自己,除非我了解原型——正如荣格所说:“将它们视为灵魅完全符合它们的本质。”[17] 我既在想象中遇到这些奇特的存在,也在意识中体验到作为原型模式的它们。
杰斯帕对灵魅论的批判 现在我们转向卡尔·杰斯帕(Karl Jaspers),以聆听他对灵魅论的批判性攻击。让我们听听这位反对者的声音,因为在杰斯帕和荣格之间的差异体现了精神与灵魂、哲学与心理学、一元论与多中心论、抽象与拟人化、字面意义与文学性、存在主义人文主义与原型心理学、自我与阿尼玛之间的巨大差异。在听杰斯帕的论述时,请记住荣格与其内心人物对话的方法,以及我们各自的积极想象经验、内心之旅和梦境。杰斯帕写道:
我们称灵魅论为一种观念,即认为存在居住于力量之中,存在于有效的形式构成力量中,具有建设性和破坏性的力量,即灵魅,有善的和恶的,众神;这些力量被视为直接明显的,并且这些知觉被转化为一种学说。善与恶都被神圣化,整体通过展现为形象的黑暗深度而得到升华……它被视为内在的超越……并且不可避免地分裂成多种力量。[19]
杰斯帕认为灵魅论适合神话和古典世界。但当超验的上帝作为一种替代出现时,“灵魅论消失了或被控制住了”。因此,在当今世界复兴这种神话思维方式是一种幻觉,因为“没有灵魅”。他讨论了歌德和克尔凯郭尔,总结了他的批评六点(第125-128页):
现代灵魅论:
“忽略了超越性”,因为“诸神已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个体人没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无法建立与唯一的联系……碎片化……;人分裂为其潜在性……;一切都可以被合理化”; “灵魅论淹没在自然中……;人失去了与自然的区别”; “现代灵魅论纯粹是一种审美态度。人不再需要承诺,因为对于每种情况,他都有一套具有虚幻宏伟感的审美形象”; 最重要的是,“灵魅论设立了一种既非经验现实也非超验实在的中间存在形式……所有既不是世界(作为可证明的现实)也不是上帝的东西都是欺骗和幻象……有上帝和世界,二者之间没有其他东西。” 我让杰斯帕领导了对灵魅的攻击,但我也可以引用卡尔·巴特(Karl Barth),他认为灵魅是混沌的力量和否定的力量,自基督战胜灵魅后,它们已无话可说。或者,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指出:“‘一’与这不存在的多样性对立,这种多样性通过反抗的方式与‘一’相对立。创造就是浓缩、集中、组织、统一。”[21]
这段文字探讨了荣格的积极想象方法如何深刻影响了对“认识你自己”的理解,并引入了杰斯帕对灵魅论的批判,揭示了不同思想家在这一议题上的分歧。
杰斯帕、巴特和德日进眼中的灵魅 对于杰斯帕、巴特和德日进而言,灵魅(daimons)是一种矛盾的存在:本质上它们是多样的(就像我们情结中的意识火花一样)。[22] 尽管它们被认为是“不存在的”且“无话可说”,但它们却带来了矛盾,并要求进行斗争。这场斗争是对抗多样性力量的斗争。人类内在的多样性使我们的内在冲突和自我分化成为可能,即荣格所说的“认识你自己”的复杂性——或个体化过程,在他们看来是灵魅的表现。
通过将灵魅想象为矛盾的存在,关于它们是否能够说话的问题便产生了。这个问题早在古典和基督教思想中就已经存在;如果它们能说话,那会是什么语言呢?普罗提诺(Plotinus,《九章集》IV 3, 18)认为灵魅和灵魂可能会使用语言。但基督教作家削弱多神教的一种方式就是否认内心声音拥有言说的力量(Logos)。唯一的真正Logos是基督。打开通往内心声音的大门会让黑暗势力、古代宗教的灵魅、多神教和异端进入。[24]
因此,可以看到,一种通过倾听和与内心形象对话来追随想象路径的内省意味着与灵魅相遇。深度心理学因此最终不得不面对巨大的神学恐惧——灵魅论,正如杰斯帕敏锐地认识到的那样。灵魅的否定和驱逐一直是基督教心理学的一部分,使得西方心灵几乎没有任何手段去认识灵魅现实,除了疯狂的幻觉。通过拒绝多种声音的可能性——除了魔鬼的声音——所有灵魅在信息及其多样性上都变得具有反基督教性质。当然,古典内省止步不前,无法超越自我。内省的进程和界限由坚持统一性的意识所设定。聆听深处不仅冒犯了基督教传统;它还邀请了被宣布为魔鬼、地狱和疯狂的事物。(再次证明,荣格的个案就是一个见证。)
这段文字探讨了不同思想家对灵魅的看法,特别是杰斯帕、巴特和德日进的观点。它揭示了灵魅在基督教传统中的地位及其对心理内省的影响,强调了荣格的深度心理学如何被迫面对灵魅论这一巨大神学挑战。
当代心理控制与灵魅的否定 如今,我们把心灵内部的监督称为“思想控制”。在这里,我们开始看到否认灵魅(daimons)所带来的惊人后果:它使心灵失去了所有内在的人物,只剩下自我(ego),这个控制者变成了超我(super-ego)。没有自发的幻想、形象或情感能够独立于这个统一的自我。每一个心理现象都成了“我的”。认识自己(Know Thyself)变成了认识我自己(Know Myself)。然而,菲莱蒙教给荣格的是,心灵中有些东西并不比“森林中的动物……或空中的鸟”更属于“我”。此外,没有了形象,想象力本身也会枯萎,只会强化自我的字面理解。因此,基督教传统继续指责这个它所培养的自我,责备其骄傲的罪,并以谦卑来惩戒它。那些能教导自我其界限的形象,如同菲莱蒙教导荣格的那样,被压抑后只会在主观意识中以原型错觉的形式重新出现。自我变得恶魔化,完全相信自己的力量。
回顾杰斯帕的六个批判,我们不妨不反驳它们,而是尝试透过这些批判来看透其背后的含义。我们试着确定他攻击的是哪个原型因素,因为这个原型可能是他观点主导视角无法容忍的。通过揭示这一背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他的观点,甚至重新评估这些观点以支持荣格。
积极想象的灵魅论“忽略了超越性”:因为认识自己——所有心理学流派的目标——是了解内在和表象行为之下的世界,即内在性。诸神在世界之中,而不是超越世界。超越性是精神的语言;内在性是心理学或灵魂的语言。[25] “个体人没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为荣格的心理学关注的不是作为个人主义的人格,而是作为非个人心理过程的个体化,这是赋予价值的终极来源。价值不是来自作为人文主义中的人,而是来自人背后和内心的灵魂(anima)。心理学是以灵魂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核心的生存主义人文主义。 “无法建立与唯一的联系”:当然,荣格花费了很多精力在“与唯一的关系”上。但荣格并没有强迫这种关系,也没有为了抽象的统一而放弃多样性和多重性。[26] 完整性和完美不仅是统一,它们也是特定对立面的组合。根据荣格的观点,个体化是一个分化、差异化的进程,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是许多情结、声音和人物的集合。 这段文字探讨了当代对心灵内部监督的理解及其对灵魅的否定,以及杰斯帕对荣格心理学的批判。它强调了荣格心理学中关于内在性、个体化和多样性的深刻见解,揭示了杰斯帕批评背后可能的原型冲突。
第四点:“灵魅论淹没在自然中” 第四点:“灵魅论淹没在自然中。”是的,荣格说,这正是积极想象的意图:再次将现代人“沉浸于自然中,因为这是他所失去的——原始的、本能的反应。而这种自然的反应以原型形象的形式出现,因为原型也是本能。当杰斯帕区分超越性和自然时,荣格则认为本能的自然是超越性原型的场所。荣格曾说:“古老智者实际上是一只猿。”
第五点:“现代灵魅论是一种纯粹的审美态度” 第五点:“现代灵魅论是一种纯粹的审美态度。”荣格再次同意谴责这种审美态度,特别是在面对形象时。[27] 但荣格进一步提出一个心理学问题,发现这种“态度”隐藏了阿尼玛(anima)迷人的微笑和狡猾。这意味着审美属于灵魂。如果我们跟随杰斯帕,这种审美态度会变得恶魔化;如果我们跟随荣格,我们可以认识到审美主义中的内在人物,并通过赋予它价值和任务(如绘画、写作、塑造)来实现想象力,将其保留在心理作品中。显然,第二、第四和第五个批评都指向了阿尼玛。
第六点:灵魅论设立了一种既非经验也非超验的存在形式 第六点:灵魅论设立了一种既非经验也非超验的存在形式;这与杰斯帕的二元对立观点(“有上帝和世界,二者之间没有其他东西”)一样,需要更仔细地审视。杰斯帕坚持两界系统:精神与物质、哲学与科学、上帝与自然、神圣与世俗、心灵与身体——无论你怎么表达。他无法允许的中间选择是柏拉图传统中的第三领域,这也是荣格所坚持并基于其整个思想和生活的领域。“Esse in anima”,荣格称之为“存在于灵魂中”,即灵魂的存在论。这个第三领域不仅介于杰斯帕的两个世界之间,还保持了它们之间的区别。[29]
在这里,杰斯帕认识到对灵魅的承诺肯定了心理现实,一种仿佛存在的模式,这种模式既类似于又不同于经验性和形而上的视角,并提供了一种从灵魂的角度关联两者的方式。
换句话说,杰斯帕无意中为我们阐述了我们的观点,尽管是从反面。通过采取新教一神论的超越立场——上帝与世界之间没有任何中介——他被迫否认灵魅的心理现实。他始终停留在哲学的原型视角中,坚持连贯的统一性。他对人类的崇高观念肯定并夸大了反映这种超越统一性的自我,一个只能将多样性视为碎片化的自我。杰斯帕很好地认识到了灵魅论的危险,但没有认识到它释放灵魂脱离自我主导历史的可能性。
这段文字探讨了杰斯帕对灵魅论的批判以及荣格对其观点的回应,揭示了二者在超越性、自然和审美态度上的分歧。同时,它强调了荣格对心理现实和灵魂存在的重视,以及对个体化和多样性的理解。
杰斯帕的形而上学视角与心理现实 因为杰斯帕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处理这个问题,使用“是”动词的语言(“是否有恶魔存在?”),对他来说,问题在于实体和存在。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处理,灵魅(daimons)首先会被视为经验,即对事件的人格化视角,而灵魅论则被视为一种想象的方式。然而,以这种心理学的方式来接近问题,需要对形象和阿尼玛(anima)有所欣赏。
阿尼玛是他批判的真正目标。他对灵魅论的批评更基本的是对心理现实的攻击,即esse in anima,这个阿尼玛因素具有美学特质,它人格化了我们,使我们“沉浸于自然中”,并不想提升到超越性,坚持认为灵魂和人类一样不可替代,并拒绝那种会抹杀其模糊存在位置的二元对立。
这个被杰斯帕的存在主义思想所禁止的阿尼玛因素,在他自己的存在中以易怒和任性的方式回归,当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第25页):“这种灵魅论如同普罗透斯一样难以捉摸,它是不断变换新伪装的虚无,在其多面性中利用了所有恶魔的老把戏。”
在这里,我们的对手被水银般的阿尼玛(anima mercurii)抓住了,荣格也将其比作普罗透斯,[30] 这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回归灵魂及其形象时最受青睐的“神祇”。
我对杰斯帕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很难离开这个话题,因为他的立场浓缩了哲学、神学和人文存在主义对荣格成就的反对。
这种成就是出于命运的必然,而不是有意复活神话和灵魅,也不是异端行为、神秘政治或魔法神术,正如杰斯帕的批评所暗示的那样。相反,荣格关注灵魅源于他在精神病理学危机中突破自我命运的必要性。讽刺的是,精神病理学是杰斯帕在其著作中留下深远印记的一个领域。然而,他早期就离开了这个领域。我相信我们可以看到他离开的原因,以及他对精神分析的厌恶,他曾说:“魔鬼已经深深控制了它……我相信任何遵循这条道路的医生都处于危险之中。”[32]
要伴随患者的病理学深入到底层,医生必须走到杰斯帕不愿涉足的地方。他的形而上学不允许有第三个模糊的空间。他不能像荣格那样成为一个“灵魅之人”。因为精神病理学是以功能语言描述的现象,而灵魅论则是以人格化内容的语言来处理同一现象。
这段文字探讨了杰斯帕对灵魅论的形而上学批判与荣格的心理现实之间的差异,揭示了二者在哲学、神学和精神病理学上的分歧。同时,它强调了荣格对灵魅的关注源自个人的精神病理学危机,而非有意为之的神话复活或异端行为。
荣格对精神病理学的观点 荣格这样描述精神病理学的问题: “每一部分被分裂的力比多(libido),每一个情结都有或是一个(片段的)人格……当我们深入探讨时,我们发现它们实际上是原型构造。对于这些原型人物从一开始就具有人格而非仅仅是次级人格化的假设,并没有确凿的论据反对。只要原型不仅仅是功能关系的表现,它们就会以灵魅(daimones)的形式显现,作为个人代理。”[33]
正是这些想象中的人格化代理——记忆艺术称之为imagines agentes[34]——构成了每个案例的历史。这些灵魅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心理动力和精神病理学。(正如这个术语本身的二重性所暗示的,恶魔也是灵魅。)这些形象是超越性如何成为内在性的途径。作为心理现实的形象,它们引导我们在心理现实中前行,使我们不会转向经验自然主义或精神超验主义的指导。既不是行为主义者,也不是古鲁们。作为引导者,它们使我们坚持正在上演的神话,为我们提供了不断的机会来观察撒旦真正工作的场所——正如凯瑟琳·雷恩通过研究布莱克所展示的那样。撒旦通过其仆人工作,即选择的自我(它试图分割恶魔/灵魅的二重性),无论这个自我是披着道德主义的黑衣、马克思主义的蓝布,还是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严肃粗花呢。
在自传的“晚期思考”中,荣格再次回到灵魅的话题。他解释说,尽管他知道他同样可以用“上帝”或“灵魅”来表达,但他更喜欢使用“无意识”这个词。他意识到“mana”、“灵魅”和“上帝”都是无意识的同义词——也就是说,我们对它们的了解与对无意识的了解一样多或一样少。他说“无意识”这个词是“科学的”和“理性的”,“中立的”和“平实的”,而使用“神话语言”则能“激发想象力”。荣格认为理性命名和神话命名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平庸”和“神圣感”。但这种界限真的需要划得如此分明吗?这是否设立了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翻译的不同领域?神话想象必须如此神圣,而概念科学必须如此平庸吗?
这段文字探讨了荣格对精神病理学的理解,特别是他对灵魅(daimones)的看法,以及他在晚年对“无意识”和“灵魅”等概念的反思。荣格强调了原型构造和个人代理的重要性,并讨论了理性与神话命名之间的区别及其对心理现实的影响。
灵魅与无意识:想象的两种模式 对我来说,灵魅(daimon)和无意识都是想象的方式,是书写虚构的方式,二者在特定情况下都具有治愈效力。想象存在于平凡之中,存在于日常“不具想象力”的语言中,只要我们用心聆听其中的形象或用想象的眼睛去看。一种浪漫的想象观会夸大它,因此我们需要清醒的科学将我们从神圣感带回到平凡。然而,如果我们让想象突破其异国情调的边界,扩展其定义,使其成为一切事物中普遍存在的无意识方面,那么像“无意识”这样的科学术语所提供的“冷静观察”就不是唯一一种想象的对象化方式。神话想象提供了另一种方式,正如荣格在同一段落中所描述的。
“灵魅”和“上帝”这两个词的最大优势在于它们能够更好地对象化对立方,即对其进行人格化。它们的情感特质赋予了它们生命力和效果。恨与爱、恐惧与敬畏进入对立场景,并将其提升为戏剧。原本只是“展示”的东西变成了“行动”。通过投射出人物、形象和声音,灵魅模式不仅对象化了这些元素,还要求情感参与。此时,我们不再只是剧院中的观众(如我们在前面讨论的“梦、戏剧、狄俄尼索斯”),也不是树上的彭透斯,或是作为中立的普通观察者进入虚构世界。这些拟人化的形象客观地揭示了事实,正如事实希望以自己的声音呈现自己的一样。
想象主义与破偶像运动 现在让我们追溯到荣格和杰斯帕之前,远远超越他们,回到公元787年秋天的尼西亚,在那里东正教和天主教的约三百名主教及其代表聚集在拜占庭的比提尼亚。在那里,关于图像的本质及其正确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区分。
你可能记得,杰斯帕对灵魅论的批判包含以下陈述: “我们称灵魅论为一种概念,即将存在归因于力量、多位神祇,并通过凝视黑暗深处直接感知这些力量,这些力量在图像中显现。”
你也记得,这正是荣格所做的:他凝视黑暗深处,下降,找到了新的自我——后弗洛伊德时代的荣格,esse in anima 的荣格,而这一切都源于他直接转向了图像。
因此,为了深刻理解作为两种世界观代表的杰斯帕和荣格之间的差异,我们需要回到尼西亚和787年的伟大破偶像争议。[35] 这一争议在历史上反复出现:圣经、穆罕默德、克伦威尔;它在特伦托会议中再次出现。也许它在现代绘画中也有所体现。破偶像运动与想象主义(或如破偶像者所称的偶像崇拜)之间的对立反复出现。
这段文字探讨了灵魅和无意识作为想象的不同模式,强调了它们的治愈功能以及在心理现实中的作用。同时,它通过回顾历史上的破偶像争议,进一步对比了杰斯帕和荣格在对待图像和灵魅论上的不同态度,揭示了他们在世界观上的根本差异。
破偶像运动对形象的攻击 破偶像运动对形象的攻击——这象征着精神对灵魂的攻击——不仅体现在具体的行为中,如打碎雕像、焚烧祭坛和毁坏图像。我们延续了这种破偶像的习惯,在宗教和文学中通过寓言破坏形象,在心理学中通过概念解释摧毁形象。(例如,“你梦中的这只小猫代表你的感觉功能;这条狗代表你的性欲;角落里盘踞的大蛇代表你的无意识,或母亲,或焦虑。”)形象被概念化后变得空洞,或者消失成抽象的概念。
作为对那次会议及其背后关于破偶像与想象主义之争(即精神与灵魂之争)的注脚,我们发现当时双方的部分划分是基于男性与女性的对立。主要是军队,即拜占庭士兵,在村庄中摧毁了那些流行的偶像,而村里的女性则对抗士兵。(顺便提一句,据信“最早记录的基督雕像”是由《马太福音》9:20-22中提到的那个有血漏病的女人竖立的。)[36] 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尤为争议的中心,伊琳娜女皇代表想象主义派召集了这次会议。
当我们阅读该会议的教规时,[37] 我们可以看到男女、精神与灵魂的争论贯穿于最细微的细节中,比如严格分离修士和修女(不允许在餐桌唱“撒旦”的歌,也不允许一起用餐,见教规17-22)。同时,还有针对我们所谓的审美阿尼玛(anima)的措施:不允许穿“华丽服饰”,不允许在祭司服装边缘使用“鲜艳丝绸”或“彩色装饰”——见教规16。这种严肃的抽象神学改革精神早在西方宗教改革之前就存在了,但其名称相同:反对形象、想象力和阿尼玛的战争。
尽管历史书上说想象主义者在那次会议上获胜了,但我认为更深入的心理学解读显示胜利者实际上是破偶像主义者。在尼西亚,对崇拜形象(偶像崇拜)和尊敬形象进行了微妙的区别。[38] 会议的八次陈述强调了形象本身具有完整的神圣力量与形象作为象征或指向这种力量之间的区别。结论是神圣并不内在于形象;形象并不是力量的储存库。相反,它们主要用于教育目的。它们不是实体或“呈现”,而是表征、图解和寓言,以提醒信徒抽象的神学构想超越于形象之上。[39]
此外,还明确规定了哪些形象是可以表现的——这些是我们习惯在基督教传统图标中看到的形象。荣格所称的“个体符号形成”[40] 被禁止了。
这段文字探讨了破偶像运动对形象的攻击及其深远影响,特别指出了精神与灵魂、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并详细描述了尼西亚会议上的争论和决议,揭示了破偶像运动和想象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在宗教和心理学中的体现。
想象主义者对形象的辩护 想象主义者的一条辩护思路如下:基督本身就是一位圣像画家,其本质决定了他必须化为人形并具有可见的形象。这意味着真正的基督教服务也必须服务于形象。形象是其相关原因的效果,并且因为这些原因而产生效果。相关性意味着同时性;原因和结果在同一个时刻共同存在:原型存在于形象之中。因此,“谁摧毁了效果,也就摧毁了原因”[41]。一个人无法在不同时毁灭原型的情况下毁坏一个形象——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基督本人!
除了围绕形象争论的许多次要论点外,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主要的争斗是在字面意义的精神神学与想象心理学之间展开的。或者至少这是一种表述这场争斗的方式。破偶像者认为形象在其各个方面与其原型是同质的。描绘的基督形象与基督的本质完全一致。他们辩称这不仅是不可能的,因为基督不能被限定(除非在其肉身的人性中),而且这是不可容忍的,因为它意味着上帝实际上并且完全地存在于圣像之中。正如谢尔登-威廉斯所指出的,破偶像者通过实质的范畴来等同形象与原型。而想象主义者则从类比的角度思考,以质量的范畴来理解。基督的形象在所有方面都类似于可见的历史上的基督,虽然在质量上相似,但当然不是与那个基督本质上相同。
尽管破偶像者指责他们的对手因崇拜雕像而陷入原始异教徒的偶像崇拜,将他们视为字面主义者,真正的字面主义并不在于崇拜的对象,而在于崇拜者的思维中。形而上学和物理学的思维方式如同豆荚中的两颗豌豆:一个抽象,另一个具体,它们都无法理解灵魂的类比和隐喻模式。
因此,破偶像争议逐渐从形象本身的性质问题转向我们如何与形象建立联系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回到约翰·达马斯坎努斯(约675–749年),他是第一个认真捍卫想象主义的人。形象不应以“拉特里亚”(latria)的态度对待,即对作为宗教对象的最高无形力量的崇拜。[42] 或者用我们的语言来说:不要以精神的态度接近形象;而是以“杜利亚”(dulia)的态度,即服务的态度去面对它。这是一种对圣人或天使、圣地、物体或书籍的圣像应有的心理专注和细致观察。与雕像的关系中的拉特里亚是偶像崇拜——正如这个词本身所表明的。但这并不是形象本身成为偶像;而是拉特里亚使其成为偶像。
这段文字探讨了想象主义者对形象的辩护及其与破偶像者的争论,强调了形象与原型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态度对理解形象的影响。它还讨论了约翰·达马斯坎努斯的观点,即正确的态度应是服务而非崇拜,从而避免偶像崇拜。
心理学中的形象治愈力量 在心理学中,形象的治愈力量并不在于一种字面意义上的、神奇的效果:如果你的耳朵疼,去画它或在神龛上挂一个锡制的耳朵形状复制品。这将是“拉特里亚”(latria),即对病态部分的偶像崇拜,耳朵本身成为偶像。拉特里亚假设耳朵和形象之间存在一对一的关系,而忽视了耳朵所蕴含的隐喻意义。(在这方面,医学就像魔法一样:它是完全字面化的,并将患病的部分偶像化。)绘画形象或以诗歌形式与之对话的行为是“杜利亚”(dulia),即对形象的服务(而不是对耳朵),即使我们因疼痛而被迫这样做。
形象工作旨在通过想象力来引导想象力,因此如果治愈发生,它会通过心理的中间领域实现,即想象身体和想象力的“中耳”的治愈。这种通过形象工作的治愈过程依赖于一种虚构的感觉:我们在想象的现实中保持专注的服务态度(杜利亚)。形象工作的首要目标是把形象描绘准确(而不是耳朵)。因此,如果治愈发生,首先是对我们虚构感的治愈,甚至赋予我们的疾病以虚构的意义。想象力本身需要被关注,因为想象力可能是我们患病的根源。
今天,心理学中仍然以其他方式继续存在拉特里亚,即偶像崇拜。例如,当我们把我们的形象视为来自无意识的神奇信息,或者作为自我的神圣启示时。补偿心理学(梦中形象作为对自我意识的补偿性回应)已经取代了祈祷神学(梦中形象作为对人类祈求的神圣回应)。我们忘记了杜利亚——即人类有责任去服务和照顾这些形象。正如圣巴西勒所说,“给予形象的荣誉会传递给原型。”[43]
这种形象作为实体和形象作为表征之间的心理学差异,以及象征与寓言之间的区别,在今天的心理学中依然存在。当我们以康德的方式谈论原型形象为“大母神、自我或阿尼玛的表征”,并将原型视为超越具体形象的不可知的超验现实时,我们就采取了尼西亚会议的立场。我们分离了原型与形象,本体与现象。这一转变不仅带我们回到康德和新教的破偶像运动,也回到了对抽象概念——真理、美、上帝——的精神偏好,认为它们比具体的、心理的想象力更重要、更普遍、更永恒。这是一种回到尼西亚和787年的回归。
这段文字探讨了心理学中形象的治愈力量,强调了形象工作通过想象力进行的重要性,并指出了拉特里亚(偶像崇拜)与杜利亚(服务)的区别。同时,它还讨论了现代心理学中关于形象作为实体与表征之间的持续争论,揭示了其背后的历史和哲学背景。
贾斯帕斯与荣格对形象的不同态度 贾斯帕斯将恶魔学与形象联系起来是一种破偶像主义的再现。荣格转向经验性形象是想象主义姿态的再现。因为无论这些形象是在外部作为崇拜雕像存在,这些雕像会动、眨眼或点头——(“numinous”一词源自于形象的动画化,这与鲁道夫·奥托对超越的、无形象的“全然他者”的抽象感受完全不同)[44]——还是像荣格的情况那样,在内心想象中作为自我运动的形象出现。(菲勒蒙-以利亚由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陪同。)对于爱图者来说,重要的是贾斯帕斯所谴责的:存在、力量和现实都赋予了形象。它们之所以具有灵性,是因为它们是被灵魂充满的,无论是外在的圣像还是内在的灵魂中的想象。
我们将荣格的例子视为一种方法的展示,一本讲述“如何做”的手册。进一步地,按照亨利·科尔宾的意义,我们将荣格的例子视为一种叙述,即对想象力冒险的叙述。这样的冒险为灵魂开辟了新的领域,给予灵魂新的根基——或恢复其旧有的根基。因此,通过荣格的示例和方法,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能摆脱古代教会对我们想象心灵的束缚。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恢复形象在我们个人生活中的首要地位,从而重新实现形象与心灵之间的直接关系。
事实上,当荣格表述他的体验时,他写道:“形象即是心灵。”[45] 因此,当我问:“我的灵魂在哪里;我如何遇见它;它现在想要什么?”答案是:“转向你的形象。”荣格写道:“每个心理过程都是一个形象和‘想象’……这些形象与你自己一样真实。”[47] 或如美国的想象力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所说:“我们在形象中醒来……它是,我们是。”[48]
这里引用一位诗人是有意为之,因为当荣格使用“形象”这个词时,他说他从“诗歌用法”中借用,“一个幻想或幻想形象的象征”。[49] 形象不是感知的残余,不是衰减的感觉或后像——就像天真的实在论中的复制品。形象是自发的、原始的,与心灵本身一同存在,是“事物核心的本质诗篇”。[50] 原始数据是形象——贾斯帕斯的恶魔——这是心灵的直接呈现。而且,荣格说,力比多并不是以原貌出现,而是总是形成形象,因此当我们观察一个幻想时,我们就是在观看并参与自己的心理能量。他还说,这些构成我们灵魂本质的形象是我们唯一直接呈现的事物。其他一切——世界、他人、我们的身体——都是通过这个诗意的祖先因素,即形象,传递给意识的。我们关于世界、他人、我们身体的任何说法都会受到这些原型幻想形象的影响。在我们的感知、情感、思想和行为中,有神祇、精灵和英雄,这些幻想人物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感受、思考和行动,所有存在都由想象力构建。
这段文字探讨了贾斯帕斯与荣格对形象的不同理解,强调了荣格认为形象是心灵的直接呈现,并且指出形象在心理学和个人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通过引用荣格和其他诗人的观点,文章揭示了形象在理解和治疗心灵中的关键作用。
想象与原型心理学 这引导我们进入一种原型心理学:不断反思那些主观的幻想因素,认识形象及其在我们所有现实中的持续作用。正如荣格所说:“心灵每天都在创造现实。我唯一能用来描述这种活动的词是幻想……因此,我认为幻想是心灵特定活动最清晰的表现。”[51]
灵魂与精灵 但此刻你一定会问,像贾斯帕斯那样感到:这些形象带来的危险是什么呢!传统似乎都一致认为,恶魔是危险的——任何现实都是危险的。那么我们如何分辨这些形象是邪恶的诱惑者还是守护者呢?我们怎么知道它们是对我们怀有善意还是会占有我们呢?[52] 如果我们观察我们内心形象的来去,并在私下的积极想象中致力于它们的培养,那我们的传统虔诚和仪式会发生什么变化?
这些问题也曾困扰古代的心理学家。例如,波菲利提出了关于区分神祇和精灵的问题,并像之前的普罗提诺一样批评了通过祈祷、占卜、祭祀等方法(即神术)试图影响精灵行为以造福灵魂的做法。[53]
扬布里克回答了这样的问题:“通过什么迹象可以识别神祇、天使、大天使或精灵的存在?”[54] “是什么将精灵与可见和不可见的神祇区分开来?”[55] 他试图用描述捕捉并以有序的层级呈现这些想象中的人物及其效应,在今天可以类比于内省主义者、现象学家和精神病医生对心理事件的精确描述。
对于理性而言,精灵们似乎构成了一个混乱的世界,而理性的反应是尝试进行智力上的辨识(diakrisis,即辨别、区分)。荣格与形象的对话是一种心理上的辨识,给它们机会呈现自己的逻各斯(logos)。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并不是以混乱的形式出现在他面前,而是作为具有明确特征和名字的个体形象。
新柏拉图主义作家特别关注的是神祇与精灵之间的关系。荣格并不是第一个互换使用这些术语的人。这种用法早在荷马时期就已存在,[57] 并几乎成为一种惯例。然而,这种区分很重要,因为据说神祇是超越的,而精灵是内在的,或者至少处于中间领域。因此,这种区分涉及更抽象的区别,即将精神的力量与灵魂的力量区分开来。[58] 在情感涌入或突然直觉袭来时,我们如何判断这是召唤还是情结,是神祇还是精灵?最终,这种简化把所有好的归于神祇,所有的模棱两可归于精灵,演变成了流行的观点:患者是否需要神职人员的驱魔还是心理治疗的宣泄?
这段文字探讨了原型心理学中关于形象和幻想的作用,以及区分神祇和精灵的重要性。它还讨论了古希腊哲学家如波菲利和扬布里克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以及荣格在现代心理学中的贡献。文章强调了理解这些概念对于处理心理和情感体验的关键意义。
神祇与精灵的关系:荣格的原型与情结 因此,更深刻的探究是试图发现神祇与精灵——或用荣格的语言来说,原型与情结——之间的关系。归因于精灵的突然事件,以及我们内心生活的形象,如何融入更广泛的行星宇宙原则、神祇或原型的怀抱?
普罗克洛斯通过声明解决了这个问题:“每个神祇周围都有无数的精灵,它们与其领袖有相同的名称……因为它们在自身中表达了其领导神祇的独特特征。”[59] 这意味着我们的情结、症状和幻想中的小精灵处于主要神祇的前驱行列,并表达出阿波罗式的、火星式的或金星式的特质。我们在围绕神祇的精灵中找到了神祇。或者正如荣格所说:“神祇已变成疾病。”如果我们用批判性的想象力去观察,我们会在顽固的“恶魔”心理问题中发现神祇。[60]
虽然我们无法在此详细探讨扬布里克为深度心理学提供的推论,但我至少可以提及他对想象中人物区别的模式,包括他们的美丽、运动、光辉和能量。例如,他说英雄幻影会经历运动和变化,并表现出宏伟;天使不会说话;而精灵会引起恐惧,但它们的行为不像看起来那么迅速。
我们回到这些早期作家的作品中,以理解他们对灵魂的看法及其心理学。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他们的教义和道德论据,以及他们的灵性。事实上,荣格的转向迫使我们回归到一般称为新柏拉图主义的传统,因为在那个传统中,心灵的中间领域得到了热烈的关注。(自869年以来,官方思想的主要脉络通过将人简化为身体和精神的二元人类学,排除了灵魂。)[61] 荣格的转向还使我们能够通过将其洞见与我们当代意识中的精灵及多样化的世界联系起来,重新激活新柏拉图主义。
这段文字探讨了神祇与精灵(或原型与情结)之间的关系,引用了古代哲学家如普罗克洛斯和扬布里克的观点,并结合荣格的思想,强调了新柏拉图主义在理解心灵方面的重要性。文章指出,荣格的工作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这一传统,并将其应用于现代心理学的理解中。
多元世界的心理视角 从心理学角度看,多元世界指的是决定我们主观性的多元视角,即通过我们的眼睛看到的众多视角。并不是说有许多截然不同的世界,每个世界由一位神祇统治;而是正如凯伦尼经常强调的那样,存在一个我们共同参与的世界,但总是且仅通过某一特定星座或神话中的主导想象人物的宇宙来体验。这些是自尼采以来存在主义人道主义所称的“视角”的神圣背景。这些形象以英雄、天使、阿尼玛(anima)、精灵或神祇的形象塑造了我们所谓的现实世界。
广义上的恶魔学因此成为描述那些存在于我们所有思想和行为中的想象人物的逻各斯(logos)。广义上的恶魔学也是人类学,因为正如史蒂文斯所写:“……对他的形象的研究 / 就是对人的研究……”[62] 更进一步,广义上的恶魔学包括所有人,甚至想象中的天使,它不仅成为我们精神病理学的基础,也成为我们认识论的基础,即一切知识的基础。认知模式从未完全摆脱“主观因素”,而这一因素正是某个想象人物将我们的意识投射到特定的认识论前提中。
因此,知识的第一任务是了解这些前提,即“认识你自己”。想象力的多样性甚至先于我们对其的感知,更不用说理解了。(W. H. 奥登曾说过:“我们被我们假装理解的力量所支配。”)同样,这些以精灵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人物使我们的感知方式和参与事物现实的风格成为可能。作为首要任务——同时也是最初的享受——“认识你自己”是一种自我反思的时刻,一种在所有时刻中都存在的心理学先验,在所有事物中瞥见自我认同的笑容。
积极想象:治愈的艺术 在此,我们暂停一下,以关于积极想象的目的的观察来结束这一章节,荣格在其最后一部重要著作《神秘结合》的结尾处将其与“认识你自己”联系起来。[64] 我认为,也正是通过积极想象,荣格重新连接了希腊化时期、新柏拉图主义的图像工作传统以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自我认知分析模式。这种联系比通常将柏拉图主义和弗洛伊德分开的做法更为重要,因为在荣格的方法中,其巨大潜力之一就在于使重新解读弗洛伊德成为可能。
当我们仔细研究荣格为何提倡进行积极想象时,会发现这些基本提醒。它们可以被表述为一种否定路径的警告,类似于赋予弗洛伊德分析模式以宗教虔诚的严肃克制。
这段文字探讨了心理学中多元世界的概念,解释了不同想象人物如何影响我们的认知和行为,并强调了“认识你自己”的重要性。此外,文章还讨论了荣格的积极想象作为一种连接古代哲学与现代心理学的桥梁,及其对重新解读弗洛伊德的潜在意义。
积极想象的性质与界限 积极想象不是一种灵修实践,不是像罗耀拉的依纳爵或东方瑜伽那样的修炼方式,因为没有规定或禁止的幻想。人们处理的是自发出现的形象,而不是由大师或某种规范选定的特定形象。[65] 积极想象不是一种艺术创作,不是绘画和诗歌的创造性生产。虽然可以尽量以美学形式赋予这些形象——实际上应该尽力做到这一点——但这只是为了献给这些形象,实现它们的美,而不是为了艺术本身。因此,积极想象的美学工作不应与为展览或出版的艺术混淆。 积极想象的目标不是沉默而是表达,不是静止而是讲述、戏剧或对话。它强调语言的重要性,而不是取消语言,从而使语言成为“关联”的方式,成为情感的工具。[66] 因此,积极想象不是一种神秘活动,不是为了达到特定意识状态(如三昧、悟境、与万物合一)而进行的。那会是在心理活动中强加一种灵性意图;那会是精神对灵魂的主宰,甚至是压抑。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积极想象仅限于个人意义上的心理学活动——为了治愈症状、安抚或宣泄恐惧和贪婪、改善家庭关系、提升和发展个性。如果这样,就会把精灵贬低为个人仆人,使他们只关心解决我们称之为现实的幻觉,因为我们还没有看透这些幻觉背后的引导形象。 此外,积极想象也不是超个人意义上神术(仪式魔法)的心理学活动,即通过人类意志来操控形象。从原型心理学的传统两方面——普罗提诺和弗洛伊德——我们都得到了警告,不要打开通往“神秘主义黑潮”的闸门。[67] 当我们人为激活形象(如使用药物)、将其作为例行公事的仪式、追求特殊效果(如同步性)、增强占卜能力(转向内心声音解释梦境)、用它来增强决策中的自信时,积极想象就变成了大众迷信的神术。[68] 所有这些用途不再是自我认知的方式,而是自我膨胀的方式,现在被冠以“心灵成长”的无辜标签。浮士德式的追求依然存在并扭曲了我们的“认识你自己”,将其变成了一种超越其原意限度的驱动力:“认识到你只是凡人,而非神。”作为神术占卜的积极想象会试图操控神祇,而不是认识到神祇在我们身上的作用。我们追求得太过遥远,错过了日常和每晚都存在的精灵。正如普罗提诺所说:“应该是他们来找我,而不是我去找他们。”[69] 这段文字详细界定了积极想象的本质及其与灵修、艺术、沉默、神秘主义和个人及超个人心理学活动的区别。它强调了积极想象作为一种心理学工具的独特性和正确使用的重要性,避免误入歧途或滥用。
荣格内心想象的方法 因此,荣格的内心想象方法并非出于这些原因——灵修实践、艺术创造力、超越世俗、神秘愿景或合一、个人提升或魔法效果。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其目的是什么?
主要目的是通过重新建立心理在“中介”(metaxy)中的位置来治愈心灵,从字面主义的疾病中恢复过来。找到回归中介的道路需要一种神话式的想象方式,就像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作为灵魂疗愈者所使用的那样。这种回归虚构和神话的中间领域,使人们与自己所在的宇宙产生对话式的熟悉感。因此,治愈意味着“回归”,而心理意识意味着“对话”,一个“被治愈的意识”以虚构的方式生活,正如像荣格和弗洛伊德这样的疗愈人物在我们眼前成为虚构的人物,他们的事实传记溶解并凝结成神话,成为虚构的一部分,从而继续发挥疗愈作用。
因此,尽管积极想象在程序上与艺术非常接近,但在目的上却有所不同。这不仅因为积极想象放弃了物理产品的最终结果,更重要的是,它的意图是“认识你自己”,即自我理解,这也是它的界限——与赫拉克利特的心灵无尽性相对应的悖论性无尽界限。自我理解必然是循环往复的,在其场景、幻象和声音中不断旋转。[70]
从叙事的角度来看,幻象和声音是一个无尽展开的故事。积极想象是无尽的,因为故事进入了死亡,而死亡是无尽的——谁知道它会在哪里停止?从叙事的角度看,自我理解是那种将生命个体化为死亡的疗愈虚构。然而,从形象的角度看,自我理解之所以无尽,是因为它本身就不在时间之中。“认识你自己”具有启示性、非线性和不连续性;它像一幅画、一首抒情诗;传记完全融入了想象行为。我们可以虚构启示时刻之间的联系,但这些联系隐藏起来,如同火花之间的空间或发光鱼眼睛周围的黑暗海洋,这是荣格用来解释形象的形象。每个形象都是其自身的开始和结束,在自身内得到治愈。所以,“认识你自己”在离开线性时间并成为想象行为时终止。部分洞见就是全部——这首歌现在,这个形象;部分地看就是全部。由积极想象治愈的自我理解。
“认识你自己”既是其终点又没有终点。它是水银般的存在。[71] 它是一种矛盾的炼金术艺术,既有目标又无尽头,正如老年的弗洛伊德在流亡维也纳前的最后一篇论文中所说,分析既有作为目标的终点,也有时间中的终点:“不仅是患者的分析,分析师自己的分析也已不再是可终结的任务,而是成为一个无尽的任务。”除了灵魂塑造的行为本身外,没有其他终点,而灵魂是无尽的。
这段文字探讨了荣格内心想象方法的目的及其与艺术、灵修和个人提升的区别。文章强调了积极想象的核心目标是通过“认识你自己”实现自我理解,并将其描述为一种既目标导向又无尽的艺术形式,旨在揭示心灵的深层结构和无尽性。
回响(Nachklang) 在结尾处,有一种诱惑浮现——这就是后记的精灵(daimon)。自我认知这一无尽之作,在荣格的语言中,是一个个体化的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推进,热度不断增加。后期的精神操作变得更为重要,这些操作被称为蒸馏、挥发、升华,特别是炼金术士所称的“增殖”[72]。虽然这些操作增强了精神的力量,但也倾向于打破心理容器,溢出到物质、行动、社会和政治领域,带着预言和使命的急迫性。随着精神热度的每一次增加,灵魂容纳它的能力也需要相应增强,以在其内在神圣空间内放大这种力量。这个空间,这幅色彩斑斓、错综复杂的灵魂地毯,其边缘和丝绸,是阿尼玛(anima)的容器——滋养者、编织者、反射者。
在这里,结合(conjunctio)是指这种被包含的精神,这种充满活力的、灵感迸发的包容。
因此,增殖(multiplicatio)并不是世界使命,也不是直接、天真地将精神注入政治和社会事务中的染色剂。相反,我认为,增殖是通过活力触及灵魂的所有点,其百条形象之渠,并通过负载灵魂的形象,使精神的光辉冲动找到见证并认识自己。“认识你自己”在此完全脱离了认知者,成为灵魂镜中精神的自我认知,灵魂对其精灵的认可。增殖以其炽热的红色[73],以自己的方式渗透进世界的物质事件的躯体,通过中间领域即灵魂或阿尼玛传递。然后,这些物质的、政治的、社会的事件本身被视作多重性——不再是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对立,不再呼唤辩证的战斗。不再是两极对立,而是多元性。或者说,再次表述:首先是心灵(Psyche),然后是世界;通过心灵这一中介(mediatrix)到达世界,而世界也因此成为多样的心灵世界。
S. 利维,《荣格〈回忆录〉的一则注释》,《精神分析季刊》第33卷(1964年),第567-574页。 《荣格全集》第七卷:183页。关于作为命运分配者的精灵,参见 B. C. 迪特里希,《死亡、命运与神祇:希腊民间信仰及荷马作品中宗教观念的发展》(伦敦:Athlon出版社,1967年),第18页、57页。 这段文字探讨了荣格心理学中个体化进程中的“增殖”概念及其对精神与灵魂关系的影响。文章强调了在个体化过程中,精神力量的增强需要灵魂相应的能力来容纳和反映,并指出真正的增殖不是外在的世界使命,而是内在灵魂各部分的全面激活,最终实现从二元对立到多元性的转变。
参考文献 参见 R. 格林内尔(R. Grinnell),“关于意识原型的反思——人格与心理信仰”,《春:原型心理学与荣格思想年鉴》(Spring: An Annual of Archetypal Psychology and Jungian Thought,1970年),第30-39页。 《回忆、梦、反思》(MDR),第181页。 《回忆、梦、反思》(MDR),第182-183页。 参见马太福音24:4和24(尽管没有直接提到精灵),8:31,9:32,11:18,15:22;类似的还有马可福音1:33,5:12。其他新约中关于精灵的陈述见以下脚注。 关于精灵(daimons)和恶魔学的文献介绍,参见《宗教的历史与现状》(Die Religio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由H. 冈克尔(H. Gunkel)、O. 谢尔(O. Scheel)等编(图宾根:J. C. B. Mohr出版社,1909-1913年)中的“Dämonen”条目;G. 范德卢(G. van der Leeuw),《宗教的本质与表现:现象学研究》,J. E. 特纳(J. E. Turner)译(伦敦:George Allen & Unwin出版社,1938年),第一卷(关于精灵、天使、复数灵魂、外部灵魂);E. 罗德(E. Rohde),《心灵:希腊人的灵魂崇拜与不朽信仰》,W. B. 希利斯(W. B. Hillis)译(伦敦:Routledge and Kegan Paul出版社,1925年)。对于更现代的作品,参见F. A. 威尔福德(F. A. Wilford),“荷马中的精灵”,《努门》(Numen)第12卷(1965年),第217-232页;R. H. 巴罗(R. H. Barrow),《普鲁塔克及其时代》(Plutarch and His Times,Bloomington和伦敦:Indiana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1969年),第86-91页;G. 苏里(G. Soury),《普鲁塔克的恶魔学:论一位折衷主义柏拉图主义者的思想与神话》,(La Démonologie de Plutarque. Essai sur les idées religieuses et les mythes d'un Platonicien éclectique,巴黎:Les Belles Lettres出版社,1942年);关于古代整体上的这一主题,参见M. 德蒂恩(M. Detienne),《古代毕达哥拉斯主义中的δαμων概念》(La notion de δαμων dans le pythagorisme ancien,巴黎:Les Belles Lettres出版社,1963年);E. R. 多兹(E. R. Dodds),《异教徒与基督徒在一个焦虑的时代》,(Pagan and Christian in an Age of Anxiety,剑桥: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1965年)中的“人与精灵世界”一章;A. 库克(A. Cook),《表演:希腊悲剧》(Enactment: Greek Tragedy,芝加哥:Swallow Press出版社,1971年)中的“精灵”条目。特别有见地的段落可以在以下文献中找到:R. B. 奥尼安斯(R. B. Onians),《欧洲思想的起源:关于身体、心灵、灵魂、世界、时间和命运》(The Origins of European Thought: About the Body, the Mind, the Soul, the World, Time, and Fate,剑桥: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1951年);D. O'Brien,《埃姆佩多克勒的宇宙循环:基于残篇和二手资料的重建》(Empedocles' Cosmic Cycle: A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Fragments and Secondary Sources,剑桥: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1969年),第85-97页,325-36页;A. D. 诺克(A. D. Nock),《皇帝的神灵》(The Emperor's Divine Comes),收录于其《关于宗教与古代世界的论文集》,两卷本(牛津:Clarendon Press出版社,
参考文献 E. 本兹(E. Benz),《体验形式与图像世界》(Erfahrungsformen und Bilderwelt,斯图加特:Ernst Klett Verlag出版社,1969年);O. 迪特尔姆(O. Diethelm),“17和18世纪的医学恶魔学教学”,《行为科学历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第6卷(1970年),第3-15页;R. 梅(R. May),“心理治疗与精灵”,收录于J. 谭普尔(J. Campbell)编,《神话、梦与宗教:十一重连接之愿景》(Myths, Dreams, and Religion: Eleven Visions of Connection,纽约:Dutton出版社,1970年),第196-210页;P. 弗里德兰德(P. Friedlander),《柏拉图》,第一卷“精灵与爱欲”,H. 梅耶霍夫(H. Meyerhoff)译(纽约:Pantheon出版社,1958年)。《柏拉图神话中的精灵教义史》(“Excursus on the History of the Doctrine of Daemons”),J. A. 斯图亚特(J. A. Stewart)译,《柏拉图的神话》(The Myths of Plato,伦敦:Centaur Press出版社,1960年),第434页及以后。
对于荷马时期的希腊人来说,“一个人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其生命中故事或多个故事来表达的。一个人参与的事件……构成了他的身份。如果事件的版本不同,那么身份也不同。”B. 西蒙(B. Simon)和H. 韦纳(H. Weiner),“古希腊心灵和精神疾病的模型之一:荷马的心灵模型”,《行为科学历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第2卷(1966年),第308页。由于神祇参与了这些故事,它们成为了神话,而一个人的传记变成了其神话。自我认知或“内省”在后来的希腊思想中是对这些“故事”的“审查、分类和审视”。
E. 根丁(E. Gendlin),“聚焦”,《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第6/1期(1969年),第4-5页。这篇优秀的论文展示了现象学和身体导向疗法中内省的局限性。自我检查从未离开其自身意识的“内部”。 R. 波尔(R. Poole),《走向深层主体性》(Towards Deep Subjectivity,伦敦:Allen Lane出版社,1972年)。在这里,深度维度从未真正下降到历史自我及其情感之下。对“多重视角的总体性”的呼吁仍然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没有那些通过神话将各种视角联系起来的神圣宇宙,也没有为其提供根本隐喻和意义共同体的根源。在缺乏原型人物的情况下,这些人物提供了真正深层次的(超越个人的)主体性,存在主义和现象学人文主义对其自身的基础结构视而不见。它变成了一种世俗的激进相对主义,或者是相互竞争的个人情感的唯我论(波尔承认这一点),仅仅是一种意见的方式,不会因增加意见的数量而改变。虽然提倡多种主观视角,但这种立场背叛了对其源头的不敬。因为,通过将所有眼睛放在全知人类的头部(一个视角的总体性),或者在一个委员会成员的内射中,实际上使用我们眼睛的神祇被忽视了。只有神祇使激进的相对主义合法化并变得可容忍。但一旦他们被承认,我们就离开了波尔(他代表普罗泰戈拉、胡塞尔、萨特、莱恩、克尔凯郭尔等人及其人文主义),进入了原型心理学的形象精确性。然后,深层主体性指的是我深处的主体。 这段文字探讨了关于自我认知、内省以及深层主体性的哲学和心理学观点,并引用了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强调了神话和原型在理解人类心理和身份中的重要性。
《荣格全集》第八卷:204页、627页、712页;第六卷:174页以下(基于席勒),383页;另见我的文章“对尼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一段文字的评论”,《春:原型心理学与荣格思想年鉴》(1972年),第152-154页。这些段落说明了荣格对情结的宗教理解。 参见 J. 卡默比克(J. Kamerbeek),“狄尔泰与尼采”,《哲学研究:瑞士哲学学会年鉴》第10卷(1950年),第52-84页,文中收集了两位作者批评内省的段落。 F. 尼采(F. Nietzsche),《人性,太人性的》第二部分,格言223,O. 勒维(O. Levy)译(爱丁堡:T. N. Foulis出版社,1910年)。 《回忆、梦、反思》(MDR),第192-193页。 关于道德方面的类似反应,请参见下面雅斯贝尔斯(Jaspers)的讨论,特别是当他开始讨论精灵时。对于与原型图像相关的道德问题的深入探讨,参见 R. 格林内尔(R. Grinnell),“赞美‘不圣洁的本能’——关于道德原型的启示”,《春:原型心理学与荣格思想年鉴》(1971年),第168-185页。 《回忆、梦、反思》(MDR),第183页。 《回忆、梦、反思》(MDR),第319页。 关于灵魂与精神的区别和关系,参见我的《心理学的重新审视》(Re-Visioning Psychology,纽约:Harper & Row出版社,1975年),第67-70页;另见我的文章“阿尼玛II”,《春:原型心理学与荣格思想年鉴》(1974年),第144-145页。 K. 雅斯贝尔斯(K. Jaspers),《哲学的永恒范围》,R. 曼海姆(R. Manheim)译(伦敦:Routledge & Kegan Paul出版社,1950年),第177页。雅斯贝尔斯早先在《世界观的心理学》(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柏林:Julius Springer出版社,1919年),第166-172页中,特别以歌德为例,考察并谴责了“神话-精灵的世界观”。 K. 巴特(K. Barth),《教会教义学》第三卷第三部分:论创造(Die Kirchliche Dogmatik III/3: Die Lehre von der Schöpfung,苏黎世:Evangelischer Verlag出版社,1950年),第608页及以后。 引自 D. P. 格雷(D. P. Gray),《一与多:德尚神父的统一愿景》(The One and the Many: Teilhard de Chardin’s Vision of Unity,伦敦:Burns & Oates出版社,1969年),第21页。关于各种原型创造力的概念,参见我的《分析的神话》,第一部分(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德尚在此的观点显然是老者原型的视角。 参见《荣格全集》第八卷:388页及以后和582页。 这个问题已在马可福音1:34中提出,其中提到耶稣“不允许魔鬼说话”。 “古代的精神语言”,收录于 W. 泰勒(W. Theiler),《新柏拉图主义研究》(Forschungen zum Neuplatonismus,柏林:de Gruyter出版社,1966年),第302-312页。 这段文字引用了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涉及了荣格心理学、哲学、神学等多个领域的文献,探讨了情结的宗教理解、内省的批评、灵魂与精神的关系以及原型心理学中的道德问题等主题。
关于精神语言与灵魂语言之间的差异,可参见我的文章“高峰与低谷:灵魂/精神的区分作为心理治疗与灵性修行之间差异的基础”,收录于《老者与少年》,第三卷第二章(Senex and Puer, UE 3, Chapter 2)。 “现实由多种事物构成。但‘一’不是数字;第一个数字是‘二’,从它开始才有多种性和现实。”《荣格全集》第14卷:659页;另见他在《死者的七次布道》(Septem Sermones ad Mortuos)第四部分中关于多样性的段落:“神祇的多样性等于人类的多样性。”“意识或所谓人格的统一并不是现实,而是一种愿望”(《荣格全集》第9卷第一部分:190页)。 参见《回忆、梦、反思》(MDR),第185-188页;《荣格全集》第8卷:172-179页。 对比雅斯贝尔斯的激进二元论(“两者之间无任何中介”)与柏拉图在《会饮篇》中狄奥提玛(Diotima)所说的这段话:“所有精灵都是神与凡人之间的中介。它们解释并传达人们向神的愿望和神向人的旨意,介于两者之间并填补了这一空隙……神不与人直接接触;只有通过精灵,无论是在清醒时还是在睡眠中,人与神之间才有交流和对话。精通此类交流的人是精灵之人……”(多兹,《异教徒与基督徒》,第37页)。普鲁塔克进一步指出,否认精灵的存在就打断了将世界与神连接起来的链条(《神谕的衰落》,13节)。显然,正如C. 比格(C. Bigg)在《亚历山大的基督教柏拉图主义者》(The Christian Platonists of Alexandria,牛津:Clarendon Press出版社,1913年,1968年,第307-308页)中所指出的:“正确理解的精灵学说……会使对基督的信仰变得没有必要。”因此,问题在于中介的本质——要么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即基督与十字架(世界轴心),要么是多个想象中的角色。因此,十字架的符号被用作抵御精灵的保护符。同样的,“心理学十字架”也可以这样使用——即荣格在同一时期遇到精灵时在他脑海中浮现的曼荼罗,在他关于曼荼罗的著作中,它被描述为一个抵御心理力量入侵的避难所(《荣格全集》第9卷第一部分:16页,710页)。关于十字架与多重力量的关系,见《荣格全集》第11卷:429页。正如荣格进一步指出的那样,当这个世界轴心(作为中介的基督教)崩溃时,精灵们会复活,并回到他们以前的高位,“像天空中看到的事物一样”(UFOs,《荣格全集》第10卷:635页),并使用了与扬布里科斯(Iamblichus)描述精灵时相同的术语(见下文)。
这段文字探讨了精神与灵魂的区别、荣格关于多样性的观点、雅斯贝尔斯的二元论与柏拉图的精灵概念之间的对比,以及精灵学说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文中还讨论了曼荼罗和十字架作为心理保护符号的意义。
精灵(daimons)具有诸如迅捷性、光辉性等特质。当今的官方宗教(科学、军事、政府)通过其监察机构已经宣布这些精灵“不存在”,而民间信仰却继续“看到”它们并带来见证。29 伊姆比利克斯(Iamblichus)在其《中项法则》(Law of Mean Terms)中详细阐述了第三领域的逻辑:“两个不同的概念必须由一个与两者都有共同之处的中介连接。”因此,灵魂作为中介,因为它既与世俗世界又与神圣领域有共同点,同时“将它们牢固地分开”。引文和讨论来自 R. T. Wallis,《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伦敦:Duckworth出版社,1972年),第131页。
30 参见我在荣格和文艺复兴时期对普罗透斯形象的注释,《心理学的重新审视》(Re-Visioning Psychology),第256页脚注73。
31 精灵教会我们神话中的仿佛思考(as-if thinking),这一点早在普罗克洛斯(Proclus)时就已注意到(《荷马寓言的辩护》,托马斯·泰勒的柏拉图主义:精选作品,K. 莱恩和G. M. 哈珀编(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461页:“……我们尤其能感知到这些寓言与精灵部落之间的联系,其能量以象征的方式表现了许多事物,正如那些在清醒时遇到过精灵或在梦中享受其灵感的人所知道的……”)
32 H. 斯蒂尔林(H. Stierlin),“卡尔·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学在他的基本哲学立场下的光芒”,《行为科学历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第10/2期(1974年),第221页。斯蒂尔林指责雅斯贝尔斯未能处理好精神分裂症,这也可以理解为他未能处理好精灵问题。
33 《荣格全集》第五卷:388页。
34 F.A. 耶茨(F.A. Yates),《记忆的艺术》(The Art of Memory,伦敦:Routledge and Kegan Paul出版社,1966年),第10页。
35 图像破坏争议由 C. J. 海费莱(C. J. Hefele)在其《教会会议史》(A History of the Councils of the Church,W. R. 克拉克译(爱丁堡:T. & T. Clark出版社,1896年),第5卷:260-301页)中进行了详尽的回顾。另见 C. 曼戈(C. Mango)编,《拜占庭帝国的艺术》(The Art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312–1453,恩格尔伍德悬崖:Prentice Hall出版社,1972年),第149-177页中的一些相关文献。
36 欧塞比乌斯(Eusebius),《教会史》第七卷18章;参见 I. P. 谢尔顿-威廉姆斯(I. P. Sheldon-Williams),“图像的哲学”,收录于 A. H. 阿姆斯特朗(A. H. Armstrong)编,《后期希腊和早期中世纪哲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r Greek and Early Medieval Philosophy,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515页。
37 海费莱,《教会会议史》,第5卷:378-385页。
这段文字探讨了精灵的本质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引用了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涉及新柏拉图主义、神话思维、精神病学以及宗教历史等多个领域的文献。文中特别强调了灵魂作为中介的角色,并讨论了精灵与人类经验和文化表达之间的关系。
同上,第5卷:371-372页(第五次会议报告)。参见莱昂尼德·乌斯彭斯基(Leonide Ouspensky),《圣像神学》(Theology of the Ikon,纽约州克雷斯特伍德:圣弗拉基米尔神学院出版社,1978年),第145-178页。“……会议特别强调我们对图像的态度应该是尊敬和敬仰,但不是真正的崇拜,真正的崇拜只属于上帝……”(第170页)。会议使用的希腊词是proskunesis,这个词有问候、欢迎,甚至亲吻的含义,暗示与图像是通过灵魂(anima)建立关系的。 一方面,圣像崇拜者援引约翰·达马森(John of Damascus)的话认为,“图像是某人的肖像和表现,本身包含着被描绘的人”,圣约翰·达马森,《论神圣的图像》,M. H. 艾利斯译(伦敦:托马斯·贝克出版社,1898年,第三部分)(斜体字为我所加)。另一方面,官方立场在869-70年的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海费莱,同上,第4卷:402页,第3条):“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圣形象应予以敬仰,如同对福音书一样;因为正如文字引导我们走向救赎,图像也通过色彩起作用,所有有学问或无学问的人都发现它们有用。”(译文和斜体字为我所加)。教义决定进一步指出:“每当我们在图像中看到它们的表现时,每次凝视它们时,都会让我们想起原型……”(乌斯彭斯基,《圣像神学》,第160页)。图像是通向原型的媒介——这一观点始终意味着图像是第二位的、较低等级的存在。 荣格(《荣格全集》第八卷:92页)将“多神教的消灭”与基督教对“个人符号形成”的压制联系起来。“但随着基督教理念的强度开始减弱,个人符号形成的复兴是可以预期的。”这并不排除这种符号形成仍然是基督教的,正如荣格自己的情况一样。 谢尔顿-威廉姆斯(Sheldon-Williams),“图像的哲学”,第512页。 圣约翰·达马森,《论神圣的图像》,第三部分。 圣巴西勒(St. Basil),《论圣灵》第十八章,在谢尔顿-威廉姆斯,“图像的哲学”,第509页。 通常被忽视的是,奥托将一个罗马术语从多神教的图像语境中转移到犹太-基督教神学感受中。《神圣的概念》(Das Heilige)据说源自他在丹吉尔犹太会堂的一次“神秘体验”。(R. 施恩泽(R. Schinzer),“鲁道夫·奥托——传记草稿”,收录于《鲁道夫·奥托对宗教科学和神学的意义:庆祝其诞辰一百周年,1969年9月25日》,E. 本兹编(《宗教史与思想史杂志增刊》,14)(莱顿:Brill出版社,1971年),第17页;同一作者(更详细),本兹文章中的第37页。奥托的经历和路德宗语言继续影响荣格心理学(例如,当自我和其他原型被认为尤其通过“神秘事件”被认出时),而未意识到numen是一个图像。“神秘的”因此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同的神圣力量,而是指图像的宗教性质。 这段文字探讨了圣像崇拜的历史背景及其神学意义,引用了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涉及图像崇拜、荣格心理学以及宗教哲学等多个领域的文献。文中特别讨论了圣像作为通向原型的媒介的角色,以及图像崇拜与基督教神学的关系。
《荣格全集》第13卷:75页;关于情结作为“图像”见《荣格全集》第8卷:201页,作为“人”见202页。 《荣格全集》第11卷:889页。 《荣格全集》第14卷:753页。 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集》(The Collected Poems of Wallace Stevens,伦敦:Faber出版社,1955年),第463页:“图像的研究 I”。 《荣格全集》第6卷:743页。 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集》,第440页:“一个原始的像球体的事物”。 《荣格全集》第6卷:78页。 关于精灵(daimons)的道德二元论问题(雅斯贝尔斯将其分为“善良和邪恶”)据说是——正如许多西方二元论所声称的那样——一种波斯影响,它彻底区分了与上帝同在的好势力(天使)和阿赫里曼的恶势力(邪恶精灵)。然而,正如A. D. 诺克(A. D. Nock)所说,“这些术语[神祇和精灵]通常并不涉及善恶对立。”(“希腊人与玛吉”,收录于《论文集》,第2卷:520页)。多兹(Dodds,《异教徒与基督徒》,第118页注释)发现这种二元论在普鲁塔克对恩培多克勒的引用中是本土的。(参见普鲁塔克的《伊西斯与奥西里斯》,J. W. 格里菲斯译(卡迪夫:威尔士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24-28页,383页及后)。但难道不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19-21中将关于精灵的二元论推向了极端吗?在谴责偶像之后,他说:“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非此即彼。新柏拉图主义试图通过将它们排列在中间区域的差异化垂直链条上来用多元主义解决二元论。荣格通过拟人化形象(阴影、孩子、母亲、老者、阿尼玛/阿尼姆斯等)对心理进行区分的做法与新柏拉图主义的努力相类似。两者都以不同类型的想象人物来构建灵魂。同样,朱利奥·卡米洛(Guilio Camillo)在《记忆的艺术》中的剧院也是如此。这些都是恶魔学说,它们通过多种拟人化的神话神灵(原型)来组织灵魂,并将组织因素置于灵魂本身,即想象力之中。 沃利斯,《新柏拉图主义》,第109页。 伊姆比利克斯关于埃及人、迦勒底人和亚述人的神秘著作,托马斯·泰勒译(1821年)(伦敦:Stuart and Watkins出版社,1968年),第2卷:3页。 这段文字探讨了荣格心理学中关于情结和原型的概念,引用了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歌以及新柏拉图主义和古代哲学家的观点。文中特别讨论了关于精灵的道德二元论问题及其在宗教和哲学中的表现,并比较了新柏拉图主义和荣格心理学在灵魂结构上的相似性。
同上,第1卷:20页。(波菲利在给阿涅博的书信中提出的问题在同一卷中有翻译,第1-16页。) 参见沃利斯,《新柏拉图主义》,第152页,有关等级结构的图表。 参见迪特里希(Dietrich),《死亡、命运与神祇》(Death, Fate and the Gods),第二章:“精灵与英雄”,进行了一次全面讨论。 精神/灵魂的区别是荣格作品中的基本问题,从1919年关于这一问题的论文(《荣格全集》第8卷:570页及后)到关于两者结合的巨著(《荣格全集》第14卷)。 伊姆比利克斯,第260页(托马斯·泰勒的一条注释引用了普罗克洛斯对《阿尔西比亚德斯第一》的评论)。 精灵模式不仅通过图像呈现,也出现在反思中。正如诺克所说:“必须记住的是,正如威拉莫维茨和尼尔森教导我们的,‘daimon’这个词在宗教仪式中极为罕见。它是一个反思和分析的词汇。”(“英雄崇拜”,收录于《论文集》,第2卷:580页注释)。精灵模式出现在我们对事件后的神话化思考中。这在上述第31条注释中已有所暗示,其中普罗克洛斯将“精灵部落”与神话叙述方式联系起来。 在869年的教会会议第十次会议的第十一项法令中,人被正式二元化为物质和非物质的双重性。非物质部分将灵魂与精神合为一体。一个本质区别因此丧失。灵魂的消除早在789年的会议上就已经准备好了(见上文),当时是对图像的驯服。教训是明确的;历史在心理学中重演。一旦图像失去了自主性和力量,就不再有“灵魂”的体验证据,灵魂在没有图像的情况下沦为一个无必要的(神学)概念。 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集》(The Collected Poems of Wallace Stevens),第463页:“图像的研究 I”。 参见R. F. C. 赫尔(R. F. C. Hull),“荣格著作中关于积极想象的书目注释”,收录于《原型心理学与荣格思想年度刊》(Spring: An Annual of Archetypal Psychology and Jungian Thought,1971年),第115-120页,以获取完整的段落列表。 《荣格全集》第14卷:707页及后(第六部分,第6章:“自知”)。 《荣格全集》第14卷:708页,749页。 荣格强调“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不可见的人)之间的内部对话,就像召唤神祇或与自己交流,或与自己的好天使交流”(引自鲁兰德的炼金术词典,《荣格全集》第14卷:707页)。 这段文字探讨了荣格心理学中关于灵魂与精神的区别及其重要性,并引用了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涉及新柏拉图主义、古代哲学家的观点以及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歌。文中特别讨论了灵魂与精神的关系及其在宗教和哲学中的表现,并强调了内在对话的重要性。
荣格引用了弗洛伊德对他的警告,《荣格自传》(MDR),第150页。 流行的迷信神术(对神祇的作用)通常归因于新柏拉图主义,对此有激烈的争论,例如A. A. 巴伯(AA Barb)在《四世纪异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The Conflict Between Paganis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Fourth Century),由A. 莫米利亚诺(A. Momigliano)编(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63年)中的“魔法艺术的存续”。实际上,扬布里克(Iamblichus)推荐了一种“更高”的神术(或白魔法)。新柏拉图主义中(或荣格积极想象中)流行主义的一个根源是其心理学思维风格,即思考“不可见的事物”。因此,一些新柏拉图主义者(如扬布里克,《神秘事物》,5: 15-17)建议使用神术将身体引入哲学;或者(对于波菲利而言),神术是为简单和粗俗的心灵(即只进行字面和具体思维的心灵)提供与神力交流的简易入门。但从根本上说,正如普罗提诺所坚持的(《九章集》II, 9, 14),神术不能帮助灵魂返回理智秩序。最多,这种神术(引导式意象)是一种用于立即实际效果的反魔法(《九章集》IV, 4, 43),或现代心理治疗所谓的“对抗恐惧仪式”。详见沃利斯,《新柏拉图主义》,第3、14、71、108及后、153页;多兹(1947),“神术”,附录(在其《神祇与非理性》[波士顿:信标出版社,1957年];沃克,《灵性和恶魔魔法》)。 波菲利的《普罗提诺传》,10.33-38,引自沃利斯,《新柏拉图主义》,第71页。 自我认知的无尽性不仅体现在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中(灵魂是无尽的)和苏格拉底的思想中(自我认知最终是对死亡的研究,也是对神圣的研究——《阿尔西比亚德斯第一》127d,也解释了自我为灵魂),也体现在犹太-伊斯兰传统中,其中“认识你自己”从根本上意味着对上帝的认识(人是上帝的形象):“认识自己的人认识他的主。”参见A. 阿尔特曼(A. Altmann),“德尔斐格言在中世纪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中的意义”,收录于其《宗教哲学与神秘主义研究》(Studies in Religious Philosophy and Mysticism,伦敦:卢特ledge和Kegan Paul出版社,1969年),第1-40页,附有丰富的注释。根据这一传统,在本文中我始终将德尔斐的“自我”理解为“灵魂”,nefesh、nafs、nafashu、psyché、anima。 这段文字探讨了荣格心理学中关于自我认知的无尽性及其在不同文化和哲学传统中的表现,引用了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涉及新柏拉图主义、古代哲学家的观点以及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传统。文中特别讨论了神术在新柏拉图主义中的地位及其心理学意义,并强调了“认识你自己”这一古老格言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深远意义。
在《神秘结合》的最后一部分中,荣格关于自我认知和积极想象的讨论不断回到墨丘利(Mercurius),他似乎既是秘密的(炼金术式的)“认知者”,也是被认知的对象,《荣格全集》第14卷:705页至结尾。 “增殖……在于重新开始已经进行过的操作,但这次是用升华和完善的事物,而不是粗糙的物质……整个秘密……在于汞中的物理溶解……” M. 鲁兰德(M. Ruland),《炼金术词典》(A Lexicon of Alchemy,1612年),由A. E. 沃特(A. E. Waite)译(伦敦:John M. Watkins出版社,1893/1964年)。其含义很明显:该操作要求将冲动的物理性(炼金术士称之为“投影”)再次溶解在心理层面(汞);而不是基于当今粗糙的实质性概念,即行为社会学的唯物主义,而是重新开始心理学工作,但现在具有更高的微妙性。 再次出现的是多花墨丘利(Mercurius multi flores)的形象,“他引诱我们进入感官的世界”,其居所是在充血的静脉中(《荣格全集》第13卷:209页)。一个基本的炼金术格言说,如果“变红过早”,工作就会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工作在尚未染污灵魂之前就进入了世界。 灵魂想要什么? 阿德勒的自卑想象
首先,他【爱欲(Eros)】总是贫穷的,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细腻和美丽,而是粗犷而肮脏,赤脚且无家可归,睡在露天的土地上、街道和门廊下,像他的母亲【贫困(Penia)】一样总是处于匮乏之中。 ——柏拉图,《会饮篇》,203c
写给灵魂 “审慎的问题是科学的一半。” 每次心理治疗分析都包含一个问题,要么由患者发起,要么是我对患者感到困惑而提出。我好奇患者真正想要什么,他在这里做什么,除了我们试图总结的内容外,正如患者努力搞清楚他们真正来寻求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不仅在第一天出现,还会反复出现,有时是有意重新引入,以使分析更加有意识。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像书中所说的那么简单,例如患者想要被爱、治愈症状、改善关系、发展潜能或接受分析师培训。治疗师的愿望——帮助他人、与人亲密、坐在扶手椅里赚钱、探究心灵、解决自己的情结——也并非问题涉及的全部。
这段文字探讨了荣格心理学中关于自我认知和积极想象的概念,引用了炼金术的术语和哲学,特别是墨丘利(Mercurius)的角色及其象征意义。文中还引用了阿德勒关于自卑感的思想以及柏拉图对爱欲(Eros)的描述,强调了心理治疗中提问的重要性及其复杂性。
我所希望的和患者所希望的似乎总是被另一个因素纠缠着,就像一根拉回的线,一种反思性的犹豫,使得我们对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的断言永远无法直接表达出来,以至于当我们刚刚触及自己的意图时,这些意图就自我否定:“那完全不是它。那根本不是我的意思。”
我逐渐认为,关于患者和我真正为何在此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就是我们真正为之而来的原因:这个第三因素似乎故意使我们的目标不断变化且复杂化,并在拒绝我们答案的同时迫使我们面对这个问题。
我认为,在治疗经验中这一反思性介入的时刻,即这个第三因素,可以归因于灵魂。我相信患者和我之所以留在心理治疗分析中,是因为它以各种方式让我们保持在那里,从移情的执念到症状的顽固性和梦境的谜团——而这些都是我们不理解的现象。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被那种对某种深深重要的东西的渴望所羁绊,这种渴望从未能与我们认为自己想要的东西相一致。此外,这种无法言喻的欲望使我们感到一种无可救药的自卑感。我们感到自卑,因为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参与心理治疗,它究竟是什么,是否进展顺利或甚至是否正在进行,或者何时结束。由于我们知道得如此之少,我们不得不依赖于实证主义、实证科学、精神教义的确定性以及意识形态的道德立场。我们紧紧抓住这些光明而僵硬的稻草,因为支撑我们的基础,即灵魂,是无尽且深不可测的。
因此,我们心理治疗中的自卑主题表现为这种渴望——超越失败、抑郁、重复和痛苦等实际的自卑,这些构成了治疗的内容——这种不可补救的不足感,是我们工作的根源,并由“灵魂”这个词呈现。
解决这种不确定性的方法之一是直接转向灵魂本身,以了解它想要什么,而不依赖于患者的报告或医生的诊断。这种直接的方法早在特土良(Tertullian)的《灵魂的见证》(De testimonio animae)中就已经出现,他写道:
我召唤新的证词,这比所有文学更为人所知……比所有出版物更公开,比整个人类更大……站出来吧,哦,灵魂……,站出来并作证。
与灵魂直接对话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更远的时代:比如埃及那位厌世的人与他的Ba(灵魂的一部分)对话,苏格拉底与狄奥提玛(Diotima)交谈,后来还有狱中的波伊提乌斯(Boethius),被哲学的声音安慰;文艺复兴时期的波利菲洛(Poliphilo)与其他人物交谈,直到最终在我们这个时代,荣格的积极想象疗法方法成为我们前一章所见的例子。
这段文字探讨了心理治疗过程中患者和治疗师之间的深层互动,特别是涉及灵魂的不确定性和难以言喻的渴望。文中引用了历史上的例子,如特土良、苏格拉底、波伊提乌斯和波利菲洛,强调了与灵魂直接对话的传统,同时反映了荣格心理学中积极想象的重要性。
让我通过一些实际案例来展示,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想象的对话中。
有一位大约四十岁的女性,她在苏黎世一家大银行担任重要职位。她原本来自乡村,现在独自居住在一栋现代化的大型公寓楼里,远离家人,没有恋人。她深刻地感受到自己高标准且有能力的生活中的那种凝固、刻板、秘书式的孤独感——内心深处害怕自己会发疯,做出疯狂的事情。她梦到一个穿着白衬衫和绿帽子的陌生年轻男子,他被关在监狱里。这个年轻人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动作僵硬,像个小丑或杂技演员,或者“像个疯子”,她这样描述。在梦中,她想把他从监狱里救出来。
我对她说:“用想象去那里并与他交谈。”
她很容易就进入了这种状态。虽然不寻常,但她确实做到了。她问他一些问题:他的名字,他来自哪里,为什么被关在监狱,他做了什么,以及她能做些什么来让他获释。他却不说话,只是跳舞、摇头,装疯卖傻。她下次来见我时,因与他的这次会面感到绝望。
我对她说:“继续回去那里。但我们也要在这里探讨一下,你身上是否有任何东西使他表现出这种行为。” 然后我们发现她对他是“愤怒的”:他认为不合作,不回应,似乎没有意识到她在试图帮助他。
于是我们开始看到,她是法官,在她去帮助他时,甚至现在还在审判他,她的提问实际上是在进一步控诉他。我们很快明白是谁将他送进监狱的。
她再次回到他身边。这次她什么也没说,他也一言不发。他们隔着铁栏杆互相注视着。然后在她的想象中,她发现自己已经在他身边,或者至少没有了栏杆。他把头放在她的腿上。她触摸他的绿帽子,问:“今天感觉怎么样?”他没有回答。她意识到,“啊哈,我又问了一个问题。我仍然在试图获取信息,还是像一个女警察。”
所以她让他的头留在她的腿上,手放在他的绿帽子上。她开始要说“这对你有帮助吗?”但制止了自己。在内心经过几次类似的较量后,她突然清楚地听到他说:“谢谢你。我已经孤单太久了。我现在不会发疯了。”
这段文字展示了如何通过想象对话帮助患者探索内心世界,揭示潜在的情感和认知模式,并逐步实现自我理解和情感释放。案例中的女性通过与梦中人物的互动,逐渐认识到自己内心的评判和控制倾向,并最终达到了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接纳。
我相信您已经能够窥见一些关于如何发现灵魂想要什么的答案。首先,我们只需走近它并让它告诉我们。这可能并不容易,因为它可能不会在我们学会倾听之前说话。只有当她停止追问(审问、询问)和谴责(评判);只有当她也置身于栏杆之后,他们之间的栏杆才消失;只有当她把他的头放在她的腿上时,他的声音才清晰地响起。他想要什么?似乎不过是不想被独自留下而发疯。因为疯狂(以及她对疯狂的恐惧)是他唯一能让自己存在的方式。这是他对她忽视、评判和令人畏惧的理性的一种防御。
接下来的例子来自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他在妻子去世后从国外来到这里。他没有孩子。他来到苏黎世,租了一间小房间,开始钻研一切他能找到的心理学资料。他保持着日记。以下是日记中的一段:
8月27日。仍然如此冷,我做了顿热午饭;然后回到纽曼的书上。过了一会儿,我的注意力分散了,听到一个清晰的年轻声音说:“父亲,你住在哪里?”这声音可能是男孩或女孩的。如果我根据B的信得出结论,认为梦中的父亲已经死了,那么我现在可以承担父亲的角色。我正在成为一个父亲。如果是男孩在说话,那他是我内心的神圣孩童吗?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存在?如果是女孩,那她大概会是阿尼玛形象吧?但为什么我要成为她的父亲?我迷失了……后来:自从上述情况后,我试图用我能想到的所有最温馨的话语去接触那个声音,但都无济于事。老傻瓜,只是坐下来,去爱这个声音吧。放松。
我相信您感受到了这位男士简单而悲怆的错误。之所以说是简单的,因为他本可以做的是听到孩子的提问——“他去哪儿了?”——并尝试回应。之所以说是悲怆的,是因为他用心理学概念和解释来回应这个声音,即他用心理学对抗了灵魂。
这段文字探讨了如何通过倾听和理解来发现灵魂的需求,并强调了直接回应内心声音的重要性,而不是用复杂的心理学理论来解读。案例中的女性通过放下自己的控制欲和评判,最终与内心的声音建立了联系,而老年男子则因过度分析而错过了这一机会。
可以推测,他的回答——所有那些心理学问题:因为B的信,我是否正在成为一个父亲,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是女孩,那么……——正是他所停留的地方。因为他一直停留在这个令人困惑的思考迷宫中,所以他没有真正听到。孩子的简单清晰的声音打破了他对纽曼阅读的系统性概念,提供了一条走出迷宫的路径。但他试图内省地接近孩子,而灵魂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触及,正如我们在第二章讨论的那样。此外,它也不能仅仅通过爱来显现,因为他在这种情境下自我规定“爱这个声音”又是一种心理学解释。孩子并没有说“爱我”。它清楚地问他:“父亲,你住在哪里?”他错过了那个时刻。所有的恳求和哄劝都无法让它回来。
对于像这两个人这样聪明、有经验且成熟的人来说,面对自己内心的影像和声音时,感到如此愚蠢的自卑是多么令人困惑。正确对待灵魂是多么困难。仿佛它的想象让我们感到自卑,伴随着那种在治疗中出现的罪恶感、无言、错误的感觉——一种没有疼痛但也没有焦点或聚焦错误的痛苦,人们只是为自己的无能哭泣,焦虑不安,无法掌握要领,悲惨地感到自卑。也许这一切不仅是因为治疗使我们回到未发展的部分,或者因为治疗是一种权力和依赖的情境。也许治疗邀请了灵魂,而灵魂则聚集了一种不同的力量,既是其自身的自卑,也使得我们过去和现在的所有一切都显得卑微。
让我们看看当询问灵魂想要什么时,它的进一步表现。这次我们的资料是作家与他名为Agatha的灵魂形象之间的信件往来。患者曾是一位成功的记者,他的智慧和才能远超过他的工作所展示的。他即将步入四十岁,因老化而陷入抑郁,认为青春(puer)的结束意味着天赋和好运的终结。他痴迷于莫扎特、帕斯卡、爱伦·坡、狄兰·托马斯、纳撒尼尔·韦斯特、托马斯·沃尔夫等天才偶像在接近四十岁时的早逝。他的写作变得极度拘谨,情绪波动、狂欢和疑病症主宰着他。在这种状态下,他开始给自己的灵魂写信。这是第一封信:
亲爱的Agatha,
我最近在荣格的书中读到了关于阿尼玛的内容,这促使我现在给你写信。我在荣格的著作中读到,有一个我们称之为无意识的客观心理世界,可以通过阿尼玛来接近,在我的情况下则是通过你。我惊讶地发现,阿尼玛有时会引发男人无法理解的情绪,甚至身体症状。昨晚,希尔曼似乎暗示你在被压抑了二十年或更久后正试图浮现。这是真的吗?请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这段文字探讨了个体在面对内心声音时的复杂情感反应,以及如何通过直接对话的方式尝试理解灵魂的需求。案例中的男性通过书信与自己的灵魂形象交流,试图理解和应对内心的困惑与矛盾。
你的朋友,威廉
我们有这样一个问题:“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以下是阿加莎的回复:
亲爱的威廉,
你问我想要什么。我需要你的陪伴,正如你需要我的陪伴一样。我渴望你的爱和忠诚。你必须将你的生命奉献给我,作为回报,我会全身心地给予你。但你必须自己找到如何更接近我的方法。我无法告诉你具体怎么做。你必须自己做出决定。这也是你可以发现自己最近一直困扰的职业选择的方法。既然我看到了你今天所做的事,你能允许我对它发表评论吗?你有一个很好的写作想法,但要从内心出发去做。把灵魂注入你的写作中。为什么不再次让想象力自由驰骋呢?你之前写的东西是垃圾,因为你不关心它。它对你没有价值。我会帮助你。
爱你的,阿加莎
他立刻回信道:
亲爱的阿加莎,
感谢你的回答和对我的写作提出的建议。我喜欢你的想法。现在我还想问你另一件事。你在做什么?我感到焦虑。我想告诉你,我仍然对这个过程感到害怕……现在告诉我,亲爱的阿尼玛,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在做什么?
威廉
她的回复如下:
亲爱的威廉,
我很惊讶于你。我费心给你提供了那么多关于写作的建议,而你却背弃了我,指责我让你感到焦虑……还有一件事:我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愚蠢。我体现了你所珍视的理想,如美丽、智慧和真理。你最近一直在绞尽脑汁思考你相信什么,你的立场是什么,你真正重视的是什么。如果你更接近我,你会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更容易找到,并且更容易信任你自己的真理。
爱你的,阿加莎
这段对话展示了威廉与他的内在灵魂形象阿加莎之间的交流。阿加莎强调了真诚沟通和个人内在探索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了威廉在面对内心世界时的矛盾和不安。通过这封信,阿加莎鼓励威廉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从而找到真正的自我和创作灵感。
永远属于你的,阿加莎
她在信中总是充满爱与忠诚地署名,并直呼他的名字。而他则较为含蓄,在信中常常称她为“灵魂”(anima),这是一种心理学概念。他们之间相当正式的书信往来持续了几个月。但我们的主要观点在于指出,即使当灵魂被询问并诚实地回答时,它的声音也未被重视。询问者有一种奇特的犹豫,不愿屈服于灵魂的关注,仿佛尽管有最好的意图,询问者仍必须保持主导地位。灵魂所说的话没有他自己说的话那样受到重视;它的需求排在其次。就像那位寡妇更关注自己对那个声音的心理学解释而非声音本身一样,这位作家也更关心自己的焦虑及其心理原因——用灵魂来澄清自己的症状——而不是这个形象告诉他的关于她对陪伴和奉献的需求,而这当然触及了他在想象性写作中放手的需求。
你是否也注意到阿加莎希望得到对她价值的认可?她不想被视为低人一等或被愚蠢地对待。在一个女人与一条黑蛇的对话中,这位女士通过称它为“幻想动物”侮辱了它。随后,这条蛇开始厌倦她的谈话水平,它回答说:“我已经受够了你想什么、你需要什么以及你感觉如何。我将回到我的丛林和自然中,直到你提出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给我。”
我们目前最后一个例子来自一位年轻的外科医生实习生乌尔里希,他第一次尝试进行内心对话。他与一位女性展开了以下对话:
她:你想要我做什么? 乌尔里希:我想和你谈谈我梦中的怪物。 她:它总是准备好跳到你的背上。 此时,一个内在的声音打断道,“这都是胡说八道”,这是怀疑理性的声音。对此,这位女士立即回应乌尔里希:“它看起来像什么?”她在敦促:抓住形象而不是内容。面对它;看清是谁在说话,否则你会被所说的内容所捕获。
乌尔里希:他看起来非常严厉,有一张灰蒙蒙的脸。 女士:给他起个名字。 乌尔里希:我不知道该叫他什么名字。 女士:给他起个名字。随便什么名字。 灰衣人说:给我起名是没有意义的。 乌尔里希:我会叫他“那个人”。 灰衣人说:这全是空想。
这段简短的对话已经揭示了灵魂的一些需求。首先,她问他乌尔里希想要什么,仿佛在这种情况下,她的期望是他能够明确自己的需求(就像那位作家“必须发现如何更接近”因为阿加莎无法直接告诉他)。接着,她希望我们的外科医生能够精确地描述出他内心怀疑者的形象,并给它一个具体的名字。(请注意,怀疑者只被允许间接表达。)如同我们其他例子中所见,乌尔里希并未完全理解到这一点。他简单地称这个形象为“灰蒙蒙的”,使它保持模糊不清,又称之为“那个人”,使其显得非个人化、疏远且匿名。当然,“那个人”是以象征方式谈论男性特质,青年中的男人;但在这一刻,由于没有充分聆听灵魂的指示,乌尔里希表现出与内心的怀疑者——他的反心理怀疑者——秘密结盟。因此,他与灵魂的对话几乎在开始时就结束了。
我通过这些对话的目的并不是要对灵魂得出一个普遍结论。我不是用它们来做一个经验性的论点,例如说这是灵魂说话的方式,灵魂知道它想要什么并且是绝对“正确”的,甚至不是说我认为这些代表灵魂的声音确实是灵魂的声音。我的理由只是这些是我们图像的声音——正如荣格所说“图像是心灵”,那么我们还能在哪里听到灵魂的需求,除了那些亲密地反映我们心理状态的图像呢?此外,这些声音来自地下世界,来自低处的声音,inferiores以低调的方式(sotto voce)说话,而这个地下世界正是灵魂的主要场所,如我在《梦与地下世界》中所详述的那样。
inferiores是居住在下层区域的精灵——心理学上的术语是“阴影”;当我们这些形象表达它们的需求时,我们会感到自卑、羞辱和羞耻。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怂恿我们做不好的事情,而是因为我们把它们隐藏起来,对待它们的方式让人羞愧,不倾听它们,很少关心我们心理社会的底层。
因此,这些对话展示的与其说是假设或事实,不如说是一种治疗方法或方法,这种方法借鉴了荣格的思想,积极投入到想象之中,尤其是低级想象:关于低级形象的想象以及使我们表现得低下的形象——这与专注于更高理想和目标的精神修炼方法截然不同。我们的方法不是解释图像,而是与图像对话。它不问图像意味着什么,而是问它想要什么。所以,我们第一次尝试回答“灵魂想要什么?”并没有给出一个实质性的答案,即它到底想要什么,而是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上的答案,即如何发现它想要什么。
探究的方法类似于写作虚构。有时它甚至被称为“创造性幻想”。这种体裁最接近于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通过多次相遇来教育作者的灵魂,提供一种富有启示性的叙述。尽管如此,虚构写作和积极想象之间存在差异,其中一些我们已经提到过。这里我想强调的区别在于对话者本人在虚构中的主动干预。这些对话要求一个人必须亲自参与自己的故事,在整个过程中尝试扮演主要角色,“我”,尽可能贴近社会现实的角色,就像卡洛斯·卡斯塔尼达在他的想象对话中以人类学家的身份与“唐璜”交谈时保持了社会现实主义的外表。即使想象力将故事带到了最高法院、贝德兰姆医院或阿拉伯酋长的后宫,“我”也应该保持其“真实自我”,热情投入但始终是一个提问者,一个通常现实中必要的虚构人物,如同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中细致入微的记录者作者所描述的阿德里安·莱弗库恩的非凡冒险一样。“平常自我”的任务是通过追求其命运——灵魂的命运——来接受教育(或治愈),坚持问“灵魂想要什么?”这个问题,无论想象力创造了多少波折和迂回。
从这些文档中,我希望我们能获得的最大收获是对不可避免的误解的理解。我们对心灵的理解是多么少。即使怀着最好的意图,我们也似乎会搞砸——我引用了一些敏感人士认真参与的微妙对话。还有很多其他例子,人们一开始就直接问道:“好吧,你是谁,你想要什么?”仿佛手里拿着枪,发现衣柜里有个闯入者,只是简单粗暴且缺乏好奇心。
如果我们应该擅长并谨慎对待任何事物,那应该是灵魂。毕竟,我们自出生以来就与它同在,每晚都与它共眠。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吗?然而,如果你在上驾驶课或烹饪课,你会比这些人更关注他们最亲密的声音。
心理治疗推动人类的沟通和关系——但我们甚至无法正确地与自己对话,也无法正确地倾听自己。我们的内在形象,如同蛇一般,带着被冒犯的感觉悄然滑走。为什么当我们终于听到时,几乎必然会以错误的方式开始,犯下各种错误,比如老鳏夫自言自语地说要爱,而那并不是孩子所要求的;又如年轻的外科医生说:“我不知道任何名字。”
我们所见的少许情况证实了荣格说过的一句话:虽然我们都拥有心灵(psyche),但我们并非都是心理学家。我们天性上并不具备心理学素养。心理学必须通过学习获得,因为它不是天生赋予的;没有心理学教育,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并使我们的守护灵(daimons)受苦。这表明,无论哪个学派的心理治疗,无论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其目的之一是获得心理学——一种同时作为灵魂治疗的灵魂话语(logos)。我们需要获得那种能让人理解灵魂的智慧回应,一种理解和关照灵魂需求的技艺与秩序,一种在言语中关心灵魂需求的知识技巧。如果这种话语(logos)就是它的治疗,因为它阐明了心灵的需求,那么对“灵魂想要什么”的一个回答就是心理学。
官方的深层心理学已经宣布了灵魂的需求。它有所欲求这一事实,在存在主义学派中,揭示了它的本质。它的需求是对恐惧的反映,是在心理存在(Dasein)所依赖的空虚深渊上的映射。基于灵魂的需求,存在主义建立了它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
如果从弗洛伊德的角度理解这个问题,那么灵魂的需求指的是本我(id)的愿望,即对力比多满足的渴望。由此构建了一种现实观和自我观,既能满足灵魂的需求,又能应对否定这些需求的现实。
从荣格的角度来看,灵魂的需求是心理目的性的基础。灵魂寻求的是初始的神秘体验(teleté),这也意味着实现。灵魂的需求是目的论的,因为它尚未分化、不完整且未结合;以整体为目标(telos)的个体化过程回应了灵魂的需求。
这三个例子表明,我们提出的问题揭示了深层心理学的基本假设。我们也看到,这些基本假设——恐惧、愿望满足、完整性——是对灵魂问题的元心理学回应。对话中的声音以更具体的方式回答,但在每种情况下都提到了自卑感,要么作为询问者的感觉,要么作为声音形象的一部分。这些声音并没有提供一个全面的元心理学答案,但它们确实让我们面对了与灵魂直接相关的自卑感。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自卑感,这个对我们的问题如此核心的概念,让我们转向心理治疗的历史和更理论的视角。正如您可能预期的那样,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思想上。
阿德勒疗法的诗学 “任何对‘精神分析’感兴趣,并希望全面了解现代精神病学整个领域的人,都不应该忽视研究阿德勒(Alfred Adler)的著作。他将发现这些著作极具启发性……” —— C. G. 荣格,CW 4: 756(1930年)
当今的深层心理学学生承认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是开创该领域的三巨头之一,但往往仅止于此。没有专门的阿德勒档案,没有他的信件集,很少有照片,在流行心理学中也鲜有提及。阿德勒是来自布根兰(Liszt和Haydn的故乡)的奥匈帝国人,是一名全科医生,特别擅长眼科,是一位后来改信新教的犹太人。他身材矮胖、面色苍白、体态圆润,额头宽阔有力。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东线服役,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维也纳。他比弗洛伊德年轻十四岁,比荣格年长五岁,在1902年受邀加入弗洛伊德的小圈子——最初的五人精神分析团体时,阿德勒32岁。几年后,即1907年,荣格发表了经典作品《早发性痴呆的心理学》(CW 3),阿德勒则出版了他的经典著作《器官自卑论》,十年后该书英文版名为《器官自卑及其心理补偿》。
对阿德勒成就的忽视部分归因于他本人的性格特点:他风趣友善且聪明机智,但这智慧要么花费在讲笑话上,要么在咖啡馆的闲谈中,或隐藏在他那种既简化又混淆思想的写作风格中。他对音乐和歌唱有着心灵上的敏感,同时也关注裁缝、教师和社会工作者——这与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客户群体大相径庭。晚年的阿德勒与弗洛伊德面对痛苦时的斯多葛派贵族风度或荣格的知识巨人形象不同,他在大萧条时期流亡纽约,晚上看电影而不是在书房写作,最终在远在苏格兰小镇的街头去世,享年67岁。像他的伟大同事一样,阿德勒的一生和死亡也体现了他的主导思想:人类的自卑感和同情感。
自弗洛伊德与荣格的通信发表以来,这三位中的两位仍然备受关注。阿德勒和荣格思想之间的关系尤其被追随者们忽视。例如,埃伦伯格对早期深层心理学的详尽研究中,阿德勒章节里只有两次简短提到荣格。荣格本人对阿德勒的早期主要作品相当熟悉,在自己的著作中总结了它们的内容,并在许多地方向阿德勒致敬。在阿德勒与弗洛伊德的争执中,荣格最初站在弗洛伊德一边,但在一封关键信件中(FJL, 335 F),荣格的笔迹暴露了他与阿德勒的认同以及独立性。
但荣格和阿德勒之间的共同点远不止与弗洛伊德的争论。阿德勒和荣格都受到康德和尼采的影响,并且都依赖于一些共同的基本概念——尽管各自的工作方式不同——如意义、个体性、集体意识和亲属感、对立与补偿,以及心理双性化。如果弗洛伊德的思想与荣格有相似之处,那么与阿德勒的相似之处则更为明显。阿德勒的工作将人类命运这一主题带入实践,这也是本章及本书的主要主题之一:我们如何应对不完美的感觉?如何生活在这种不完美中?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基本的自卑感,而人类的基本冲动却是追求完美,我们如何在认识到自己的低微的同时提升到更高的境界?这难道不是我们所寻求的治愈吗:摆脱西方神话中的双重诅咒——精神对完美的愿景和物质的根本局限,这两种原型虚构决定了“需求”的两种含义,即驱动的需求和空洞的缺乏。
进一步而言,我们寻求的治愈中的虚构与心灵在精神的完美和物质的局限之间的位置有何联系?阿德勒是那位将这些主题——人类的双重性、自卑、完美、虚构——作为人性隐喻的基本构建的深层心理学家。
或许这些构建更应该被想象为虚构——如果我们忠于阿德勒的话。尽管他的写作风格通常显得枯燥乏味,但他并非如此字面化或缺乏想象力。他所有的基本构建都可以被解读为生活的诗学,正如弗洛伊德的梦理论和荣格的原型图像理论一样,都是富有想象力的事业。
器官自卑与有机体的自卑 早在古埃及的医学仪式中,特定的身体器官就与特定的神像有关联。在木乃伊的准备过程中,肺部被放入猿形罐中,肠道被放入鹰盖罐中,胃部被放入豺狼头罐中,肝脏被放入人头罐中。器官被物理地置于与之想象中对应的或所属的神像或原型结构之下。[4] 整个中世纪医学,部分由于盖伦和伊斯兰医学的影响,不同的灵魂类型——动物、植物、生殖、精神、血液——被归因于不同的身体部位和系统。到了近代,普拉特纳(1744-1818)设想每个主要器官都有其自身的生命力,而多姆里奇在上个世纪中期强调了特定情绪与特定器官之间的关系。接近上个世纪末时,韦尼克认为主要器官具有特定的象征性表现。荣格(CW 15: 112;CW 12: 440)引用了韦尼克的观点,并在他的塔维斯托克讲座(CW 18: 135, 299f.)中通过结合心理图像和身体器官做出了几个惊人的诊断推断。[5] 弗洛伊德关于基于不同生理性感区的性格特征理论也沿袭了类似的思路。
阿德勒的贡献既更为详细也更为普遍。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最薄弱的地方,一个有机的“阿喀琉斯之踵”,这决定了我们心理生活的主线。在众多例子中,阿德勒提到了“莫扎特耳朵的退化倾向、贝多芬的耳硬化症、布鲁克纳耳朵的问题”,以及舒曼精神病中的幻觉现象和克拉拉·舒曼疑似童年失聪(OI, 60)。在另一个例子中,他引用了一项研究表明,超过70%的艺术学校学生存在视力异常(OI, 61)。
阿德勒建立了一种器官异常与心理活动之间的一对一关系:耳朵-音乐。然而,这种观点被认为过于简单且“不科学”,学术委员会一致拒绝了他在维也纳大学申请讲师职位的请求(ELL, 586)。根据当时的科学标准,他的器官自卑理论不够科学,首先是因为它将器官视为与体质相关的完整功能系统(这不同于遗传),其次是因为它忽视了器官的微观层面及其相互关系。
因此,真正吸引我们注意的不是生理上字面意义上的器官自卑,而是其富有想象力的心理方面——即一个人的整体心理生活从一种有机弱点的感觉中展开,与其说是某个具体的器官自卑,不如说是一种整体的有机自卑感。作为有形体的生物,我们在本质上是脆弱的,正是这种自卑感驱使我们的心理生活行动起来(LA-S, 161)。用阿德勒的话来说:“个体对身体自卑感的认知成为其心理发展的一种持久推动力”(NC, 1)。“自卑的器官不断努力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NC, 1)。
我们某一个或另一个有机系统——喉咙和吞咽、膝盖及其弯曲灵活性、皮肤及其表达/保护敏感性——成为我们心理注意力集中于其上的情结或形象,就像汉斯·卡斯托尔普(Hans Castorp)在荣格身上看到的小湿斑是魔山心理活动的形象来源。
自卑的器官会“说话”;正如阿德勒所称,有一种“器官方言”或“器官俚语”,一旦我们学会了它的语言,它就能告诉我们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受损的器官获得了持续的关注;像一个主导的形象一样,它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材料”(NC, 7),用于我们的心理幻想和行为。因此,这些由于内省和专注而被赋予的自卑之处恰恰是最具潜力的地方(NC, 8)。“我们所有的文化都是基于自卑感建立的”(L, 45)。
我们不应过于字面化和狭隘地理解器官的位置或自卑感。阿德勒所指的还包括任何极端的独特性,包括极大的美丽(OC67, 473)。尽管如此,灵魂的生活源自并因此需要一种特定的有机形象中定位的独特自卑感,这一位置不仅成为普遍生物自卑感的一个部分代表,还特别是一个肉体中的形象,像守护灵一样,引导和保护个体心理生活的实际成长。我们围绕着我们的弱点成长并从中生活。所以,任何失去这种有机自卑感的治愈幻想——在身体形象中的具体定位——如果深入到阿德勒的思想深处,也失去了对灵魂本身的感知。他在给Lou Salomé的一封信中强调(LA-S, 161):“心灵是低等生物的生命潜能。” 看来,要感受到灵魂的存在,就必须感受到自卑。通过阿德勒,古老的寻找灵魂的身体定位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一个人的灵魂就是其最薄弱的地方。
最薄弱的地方当然是防御聚集之处。我们在最敏感的地方最为固执;在最暴露的地方,我们花费最多的努力去掩饰。对于心理治疗而言,阿德勒的器官自卑理论意味着当我们紧密处理这些防御时,我们就最接近灵魂。治疗的任务不是打破防御和克服抵抗,而是重新发现这些行为的必要性,这些正是心灵对其弱点的回应。灵魂是由其自身的防御构成的。
阿德勒关于器官自卑的观点提供了多个治愈洞见。首先,它将“无意识”从一个心理区域转移到了自卑感的体验中。无意识是对不完美的直接痛苦感受,我们通过防御自卑感不断产生无意识。其次,阿德勒指出身体症状的价值。因为它们提醒我们自卑感,使我们与灵魂保持联系。“在你的症状中就是你的灵魂”,可以作为一个座右铭。第三,阿德勒重新定义了灵魂与精神之间的古老张力,并发现在人类生活中从童年早期就存在这种张力。向上追求的部分,历史上被认为是精神的部分,贬低另一部分,认为自己完美而另一半则是女性化的和低下的。灵魂被精神的层级视角驱赶到更远、更低的地方,即有机体的身体,在那里灵魂以症状的形式显现其存在。
神经质思维与阴阳同体 自卑感在我们的思维方式中显现,因为我们感到自卑和不安全,因此构建了心理结构以抵御这些感觉。这些结构作为引导性的虚构,主宰性的幻想,通过它们我们感知世界。其中最基本的一种神经质保护机制,也许是所有其他机制的基础,阿德勒称之为“对立性思维”,它“根据对立的原则运作”(NC, 24ff., 334ff.)。心灵设立对立的两极:强/弱、上/下、男/女——这些引导性的虚构决定了我们的体验方式。对立将世界清晰地分割,为我们在强有力的行为中施展权力提供了机会,使我们免于感到软弱和无能。更重要的是,对立性思维本身是一种对现实的呵护,防止我们面对世界的真正复杂性,在阿德勒看来,现实是带有细微差别的,而不是简单的对立(L, 74)。对他而言,认为抽象的对立反映了现实就是一种神经质的思维方式,因为所有的对立最终都指向了社会中男性和女性所体现的优劣权力结构。
因此,对立性思维不是服务于现实逻辑,而是助长了一种对现实的权力魔力;它也体现了原始思维的特点(正如列维-斯特劳斯在其神话的二元结构中所“发现”的那样)。如阿德勒所说,“无论是在神话、传说、宇宙起源论、神祇起源论、原始艺术、精神病态产物以及哲学的开端中……现象都被抽象的虚构清晰地分隔开来。这种冲动……源于自我保护的趋势”(A&A, 248)。亚里士多德范畴中的“对立”和毕达哥拉斯表格中的“对立面”也都源于不确定性的感觉……不应陷入认为这是事物本质的常见错误”(NC, 25; A&A, 229)。
对立思维的最终基础是男/女这一对,即“唯一的真正对立”(NC, 99),这可以追溯到早期童年经历中的“心理阴阳同体”(Adler 1910年的论文标题)。心灵兼具男女特质(IP, 21),从童年起,我们将弱点和自卑感与女性联系起来,同时还有由弱点引起的矛盾情绪。此外,阴阳同体的矛盾本身表明了自卑,并以强烈对立的方式被感知,从而保护我们免受其困扰(NC, 353)。社会使我们相信“只有两种性别角色是可能的”(U, 135),于是发生了一种“解剖”(NC, 345)。面对不确定性时,我们采取明确的非此即彼的态度,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正是荣格与自我意识(CW 5: 4–20; 8: 557)以及神经症的一侧性(CW 16: 257; 3: 456)相关联的思维方式。
无意识的发现与双性同体的揭示 我们注意到,无意识的“发现”与双性同体的“揭示”是同时发生的。自那时以来,从弗利斯、魏宁格、埃利斯和龙勃罗梭到弗洛伊德、阿德勒和荣格,再到纽曼、两分脑理论以及中性时尚潮流,深度心理学一直在将这两种双重性质混合在一起。双性同体变得与二元心智难以区分,以至于两种心理活动被贴上了性别标签,而自我分裂的心智则用性别语言来想象(IP, 21)。
我怀疑在这虚构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原型人物,正是阿德勒所命名的赫尔玛佛洛狄托斯(Hermaphroditus),这个形象不仅结合了两种性别,还结合了深度心理学的主要主题:神秘的秘密与解释学以及对经历之事进行性化的爱欲想象。赫尔玛佛洛狄托斯是赫尔墨斯(Hermes)和阿芙罗狄蒂(Aphrodite)的孩子,它象征着一种既羞耻、充满情欲、不自然、不可思议又怪异,但却能引发无法满足的好奇心的整个神话主题。
这一形象同时呈现为对立的两极,这正是其本质,但又不能被字面理解。我们面对的是令人困惑的矛盾,一方面是带有性成分的解释冲动(hermeneutic urge),另一方面是不可理解的未知(hermetic secret 的抵抗)。尽管这个形象可能令人反感,但它毕竟是阿芙罗狄蒂的孩子,总是充满了诱惑力。像阴阳人一样,深度心理学总是提出更多待解之谜,可以在不色情化的情况下赋予事物情欲色彩,并可以将幻想转化为不可能的爱情,这些爱情并非为了自然繁殖。尽管深度心理学试图将这些现象归结为各种理性的解释,但更好的做法是在阿德勒所唤起的形象中寻找其神话基础。
不仅是阿德勒,弗洛伊德和荣格也似乎基于阴阳人构建了他们对分析目标的理解。对于弗洛伊德而言,目标是克服男性对阉割的恐惧和女性对拥有阴茎的愿望;对于荣格而言,目标体现在明确的性意象中,如乱伦、神圣婚姻和阴阳人的结合(coniunctio)。只有赫尔玛佛洛狄托斯这种怪诞的形象才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些严肃、冷静、科学的思想会以如此奇特、几乎色情的器官语言表达出来。
如果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心理上的阴阳同体是所有三种深度治疗中治愈概念的核心,那么任何分离性的举动都是不利的。我们不应依赖英雄式的自我形象,带着他的决断之剑来引导我们走向治愈。他只是另一种男性对抗自卑的方式,他的俄狄浦斯脚、阿喀琉斯之踵和赫拉克勒斯装束都是其内在阴阳同体的标志。心理上的阴阳同体持有并置而不对立的感觉。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深度心理学如何在其理论框架内融合了性别的多样性,并探讨了人类心灵深处复杂且矛盾的本质。
对立思维与阴阳同体的矛盾 意识与无意识、男性与女性、积极与消极、私人灵魂与公共世界之间的对立割裂了阴阳同体所固有的矛盾情感。因为赫尔玛佛洛狄托斯(Hermaphroditus)呈现了一种形象,在其中自然的事物变成了非自然,这是一种原始的“反自然”形象。自然的身体和生物性别姿态通过非自然的幻想配置被重新评估。自然通过想象性的变形而转变,physis(自然)通过poiesis(创造)被重塑。
这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虚构能够治愈:荒诞的、无法实现的、非字面的,从中排除了单一意义的可能性。这不是虚构的本质吗?这就是为什么在几个世纪的启蒙之后,心理治疗在绝望中转向神话以寻找支持其疗法的理由,因为在没有神话的情况下,阴阳人成为一个没有虚构历史的可怜而奇怪的跨性别者。如果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是治愈者的原型形象,那么赫尔玛佛洛狄托斯就是治愈本身的原型形象,是心灵治愈的想象,是治愈的虚构,是一个不可能存在于生活中但在想象中不可或缺的虚构治愈者,任何代词都无法准确描述它。
这个形象还帮助我们重新评价对立性思维。它成为一种连体双胞胎式的洞察模式。人们永远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始终不可分割地绑定在一起,从一对中的一个成员进行洞察。在这些成对的关系中,我们能够反思洞察本身,审视自己的视角。每个洞察都假设了一个观察它的视角:无论在我看来显得多么低劣和软弱的事物,都是从其对应的优越和强大的一面看到的。没有什么事物是绝对如此的。我无法看到别人眼中的尘埃而不同时意识到自己眼中的梁木。
因此,当我们遇到对立性思维时,我们的问题将不再是如何结合、超越、找到综合的第三条道路或孕育出一个阴阳人。因为这样的做法会把对立视为字面意义上的真实,阻碍思维从神经质结构中解脱出来,从弗洛伊德的事实走向阿德勒的虚构(LA-S, 52, 127)。相反,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已经做了什么,以至于失去了与灵魂共生的另一个自我——那种矛盾的、自卑的、甚至是羞耻的感觉,即我们心灵中的阴阳同体。这个隐藏在“对立面”背后的形象(用作对其的防御),也正是治疗在其工作中以目标形式体现的形象——一项奇特、最不自然和充满幻想甚至令人羞耻的工作。
对立思维与阴阳同体的矛盾 意识与无意识、男性与女性、积极与消极、私人灵魂与公共世界之间的对立割裂了阴阳同体所固有的矛盾情感。因为赫尔玛佛洛狄托斯(Hermaphroditus)呈现了一种形象,在其中自然的事物变成了非自然,这是一种原始的“反自然”形象。自然的身体和生物性别姿态通过非自然的幻想配置被重新评估。自然通过想象性的变形而转变,physis(自然)通过poiesis(创造)被重塑。
这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虚构能够治愈:荒诞的、无法实现的、非字面的,从中排除了单一意义的可能性。这不是虚构的本质吗?这就是为什么在几个世纪的启蒙之后,心理治疗在绝望中转向神话以寻找支持其疗法的理由,因为在没有神话的情况下,阴阳人成为一个没有虚构历史的可怜而奇怪的跨性别者。如果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是治愈者的原型形象,那么赫尔玛佛洛狄托斯就是治愈本身的原型形象,是心灵治愈的想象,是治愈的虚构,是一个不可能存在于生活中但在想象中不可或缺的虚构治愈者,任何代词都无法准确描述它。
这个形象还帮助我们重新评价对立性思维。它成为一种连体双胞胎式的洞察模式。人们永远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始终不可分割地绑定在一起,从一对中的一个成员进行洞察。在这些成对的关系中,我们能够反思洞察本身,审视自己的视角。每个洞察都假设了一个观察它的视角:无论在我看来显得多么低劣和软弱的事物,都是从其对应的优越和强大的一面看到的。没有什么事物是绝对如此的。我无法看到别人眼中的尘埃而不同时意识到自己眼中的梁木。
因此,当我们遇到对立性思维时,我们的问题将不再是如何结合、超越、找到综合的第三条道路或孕育出一个阴阳人。因为这样的做法会把对立视为字面意义上的真实,阻碍思维从神经质结构中解脱出来,从弗洛伊德的事实走向阿德勒的虚构(LA-S, 52, 127)。相反,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已经做了什么,以至于失去了与灵魂共生的另一个自我——那种矛盾的、自卑的、甚至是羞耻的感觉,即我们心灵中的阴阳同体。这个隐藏在“对立面”背后的形象(用作对其的防御),也正是治疗在其工作中以目标形式体现的形象——一项奇特、最不自然和充满幻想甚至令人羞耻的工作。
虚构的目标 阿德勒称主要的有害运动远离灵魂的双重性质为“男性抗议”,即追求胜利、占据上风的需求。他也称之为“追求完美”或“优越”。起初,他设想了多种基础: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生存斗争;生物学上的器官劣势及克服弱点的需求;尼采的权力意志。(与此同时,荣格[CW 1]则用英雄神话来描述从模糊到定向的太阳意识的运动。)随着阿德勒思想的成熟,他不再基于个体以外的任何地方解释追求完美的冲动。这种冲动是人类本性的固有特征,“一种努力、一种渴望,没有它生活将是不可想象的”(A&A, 104)。在他的晚期著作中,前景和背景被颠倒了:不是自卑感驱使我们走向优越,而是我们的自卑感源于内在的追求完美的冲动。不再是恐惧的灵魂及其有机弱点通过更高的精神来补偿,而是精神宣称了超出灵魂所能实现的东西。
我们必须小心不要仅用荣格的观点来理解阿德勒,认为他所说的“伟大的向上驱动”是指自我的字面现实。这是一个微妙且重要的点。阿德勒说:“追求完美是天生的。这并不是指有一种具体的驱动力……能够完成一切并只需要发展自身”(A&A, 104)。我认为他是在区分一种内在的精神最终主义,它赋予所有心理努力以特征,以及灵魂通过虚构目标来形象化这些理想目的的方式。他警告不要将“天生的”视为具体的驱动力(在弗洛伊德的意义上),或作为需要证据的经验事实(在荣格的意义上)。我们追求完美,但完美没有具体的经验目标。阿德勒可能会首先回答我们关于渴望灵魂的问题,说灵魂渴望是因为其终极原因、其目的必须保持未完成。它的每一个动作本质上都是有目的的,但它永远无法将其目的性表达为任何具体的字面目标。
这是阿德勒思考的微妙之处,因为他的“追求完美”是一种无法固定于其任何显现的精神概念,即使它赋予所有努力以意义。在这里,阿德勒接近于认为最终目的是看待所有心理事件的一种视角——将其视为有目的的——而不是像荣格有时倾向于将目的具体化为自我的可证明的个性化过程。阿德
虚构的目标(续) 阿德勒能够做出这种非字面化的转变,而弗洛伊德和荣格未能做到,是因为他有不同于他们的来源:汉斯·瓦伊廷格(Hans Vaihinger)的《仿佛哲学》(Philosophy of As If)。阿德勒经常承认对这本书的巨大债务(参见 IP, 214, 230;NC 各处;ELL, 606–8, 630–31;A&A, 76–89)。尽管阿德勒并非在所有地方都能将他自己的字面化理解为“仿佛”,但他的心理学中最具有特征性和价值的部分之一就是他对心灵虚构本质的理解。正如瓦伊廷格所说:“主观即虚构”(V, 108)。心灵构建并发明形象,心智将其作为引导;阿德勒称之为“引导性虚构”。
阿德勒的这一观点强调了我们内心的虚构性质。我们的心理活动不仅受到现实的驱动,还通过这些虚构的目标来指引和赋予意义。例如,“追求完美”并不是一个可以实现的具体目标,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驱动力,它赋予我们的努力以方向和意义,但又不被具体的事物所固定。
灵魂的双重性质与男性抗议 阿德勒所说的“男性抗议”指的是追求胜利、占据上风的需求,这是对灵魂双重性质的一种有害偏离。他认为,这种抗议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生物器官劣势及克服弱点的需求、尼采的权力意志等多方面。随着阿德勒思想的发展,他逐渐认识到追求完美的冲动是人类本性的固有特征,是一种无法具体化的内在驱动力。
阿德勒在其晚期著作中颠倒了前景和背景的关系:不是自卑感驱使我们走向优越,而是我们的自卑感源于内在的追求完美的冲动。不再是恐惧的灵魂及其有机弱点通过更高的精神来补偿,而是精神宣称了超出灵魂所能实现的东西。这种观点强调了灵魂的矛盾性:一方面追求完美,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和不足。
心理治疗中的对立思维 当我们遇到对立思维时,我们的问题不再是如何结合、超越、找到综合的第三条道路或孕育出一个阴阳人。因为这样的做法会把对立视为字面意义上的真实,阻碍思维从神经质结构中解脱出来,从弗洛伊德的事实走向阿德勒的虚构(LA-S, 52, 127)。相反,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已经做了什么,以至于失去了与灵魂共生的另一个自我——那种矛盾的、自卑的、甚至是羞耻的感觉,即我们心灵中的阴阳同体。
这个隐藏在“对立面”背后的形象(用作对其的防御),也正是治疗在其工作中以目标形式体现的形象——一项奇特、最不自然和充满幻想甚至令人羞耻的工作。通过揭示和理解这些对立面,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探讨心灵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从而找到治愈和成长的道路。
总结来说,阿德勒的心理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让我们看到心灵不仅仅是受现实驱动的,还通过虚构的目标来赋予生活以意义。这种理解有助于我们在心理治疗中更好地处理对立思维和内心冲突,最终实现心灵的整合与和谐。
完美是一种必要的虚构 因此,完美是一种必要的虚构,从实用角度看是必需的,正如真理“仅仅是便利的最大错误”(V, 108)。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所追求的完美目标在每一个客观和字面意义上都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我们也能够认识到这种虚构的完美是多么必要。心灵抛出目标作为诱饵来捕捉生活的鱼,虚构用以激发和引导行动。正如荣格所说:“一个指向超越的精神目标对灵魂的健康是绝对必要的”(CW 17: 291)。再次强调,不是具体的目标或声明的目的,而是阿德勒和荣格所强调的那种目的感是富有成效的。这是最终主义的观点:“没有无目的的心理过程”,荣格如是说(CW 5: 90)。这一切都很重要,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人们感到有目的性,有一种道路的感觉,自己正在沿着一条路前进,这个过程被称为阿德勒的“追求完美”,荣格的“个体化”。
希腊语中的“道路”是methodos,即方法。阿德勒和荣格各自讨论的内容体现在心理治疗的方法中,其本质目的是通过其方法保持那种道路感。我们只能通过不让目的性具体化为明确的目标来保持这条道路的前进。目标,尤其是最高尚和最美好的目标,往往会变成过度评价的想法,成为滋养大规模偏执妄想的根源,这些广泛的理想特征在于规模和重要性,定义了许多现代治疗学派的积极目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看到了目标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比如对人生目的的压倒性信念、必须做的事情、存在的理由,结果却成为了阻碍道路的目标。因此,心理治疗关注的是较低层次的人,较小的轨道作为目标;或许可以将其定义为小道的方法,其中小本身就是道路。
治愈的虚构 既然目标是一种指引性的虚构,它就是一种治愈的虚构。“被治愈”是促使人们进入治疗的目标,而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目标是虚构时,我们就从这个目标中得到了治愈。现在,作为虚构的目标已经成为了一种心理现实,本身成了一种心理现实,确实,道路变成了目标。这种非字面化的治愈方法如此讽刺、滑稽、悖论,似乎同时实现了并挫败了我们的努力(仿佛“想要”的两种含义突然结合在一起),这体现了赫尔墨斯(Hermes)——灵魂和道路的引导者——那变幻莫测的意识。
通过这种理解,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目标是虚构的,但它作为一种心理现实,为我们提供了前行的方向,并帮助我们在心理治疗中找到意义和方向。这种看似矛盾的过程实际上是心灵成长的一部分,它引导我们超越字面意义上的目标,转向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自我认知
完美是一种必要的虚构 因此,完美是一种必要的虚构,从实用角度来看是必需的,正如真理“仅仅是便利的最大错误”(V, 108)。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所追求的完美目标在每一个客观和字面意义上都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我们也能够认识到这种虚构的完美是多么必要。心灵抛出目标作为诱饵来捕捉生活的鱼,虚构用以激发和引导行动。正如荣格所说:“一个指向超越的精神目标对灵魂的健康是绝对必要的”(CW 17: 291)。再次强调,不是具体的目标或声明的目的,而是阿德勒和荣格所强调的那种目的感是富有成效的。这是最终主义的观点:“没有无目的的心理过程”,荣格如是说(CW 5: 90)。这一切都很重要,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人们感到有目的性,有一种道路的感觉,自己正在沿着一条路前进,这个过程被称为阿德勒的“追求完美”,荣格的“个体化”。
希腊语中的“道路”是methodos,即方法。阿德勒和荣格各自讨论的内容体现在心理治疗的方法中,其本质目的是通过其方法保持那种道路感。我们只能通过不让目的性具体化为明确的目标来保持这条道路的前进。目标,尤其是最高尚和最美好的目标,往往会变成过度评价的想法,成为滋养大规模偏执妄想的根源,这些广泛的理想特征在于规模和重要性,定义了许多现代治疗学派的积极目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看到了目标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比如对人生目的的压倒性信念、必须做的事情、存在的理由,结果却成为了阻碍道路的目标。因此,心理治疗关注的是较低层次的人,较小的轨道作为目标;或许可以将其定义为小道的方法,其中小本身就是道路。
治愈的虚构 既然目标是一种指引性的虚构,它就是一种治愈的虚构。“被治愈”是促使人们进入治疗的目标,而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目标是虚构时,我们就从这个目标中得到了治愈。现在,作为虚构的目标已经成为了一种心理现实,本身成了一种心理现实,确实,道路变成了目标。这种非字面化的治愈方法如此讽刺、滑稽、悖论,似乎同时实现了并挫败了我们的努力(仿佛“想要”的两种含义突然结合在一起),这体现了赫尔墨斯(Hermes)——灵魂和道路的引导者——那变幻莫测的意识。
心理治疗的最佳目标是调整虚构感 因此,心理治疗所能做的最佳工作是调整个体的虚构感。这样一来,治疗所追求的目标——成熟、完整、圆满、自我实现——可以被视为引导性的虚构,而不是封闭道路的终点。治疗不再是支持“伟大的向上驱力”,而是将那些固定了目的的虚构非字面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实际上通过自己的目标来抵御灵魂内在的“朝向性”。这是一种“视角”的治疗(U, 14)。精神的目标并不会因此成为可以被冷嘲热讽地贬低的幻觉,仅仅因为它们是“虚构的”。我们只是不再以字面的方式去理解和看待这些目标和真理。作为虚构的视角或幻想,它们是富有成效且实用的,因为虚构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更自觉、更实用、更有成果的错误”(V, 94)。
似乎虚构感本身成为了心理治疗的目标,并且是我们完善自我的唯一途径。这表明,灵魂可能追求的唯一完美是其虚构理解的完美,即在它的形象中实现自己,而这些形象本身就是虚构之一。治疗使灵魂经历一个过程,将其对自身的实体化(ELL, 608)转化为视角。这种方法保持了道路的开放性,阿德勒的方法似乎最接近宗教理念,即最终目标是道路本身,在这种情况下,是虚构的道路。
共同感(Gemeinschaftsgefühl) 阿德勒理论的第四个主要组成部分是共同感(Gemeinschaftsgefühl),即社区感或社会兴趣。“我们拒绝孤立地认识和考察一个人”(A&A, 126),因为无法逃避“共同体生活的讽刺逻辑”(A&A, 127)。尽管存在教条式的字面解释,但阿德勒的思想仍带有主观主义的转折,因为社会兴趣不是一种社会事实,而是一种社会情感,“一种对全人类亲密归属的感觉”(OC72),从永恒的角度来看(A&A, 142)。社会嵌入的铁律不是从社会学角度,而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待的。这不仅仅是社会优先,而是心灵本质上具有人际性(mitmenschlich)。
对于阿德勒来说,他关注的不仅是环境本身,而是这些环境对个体的意义(L, 9f.),包括其社会意义。我们必须记住,阿德勒的社会兴趣,从他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到后来的利他主义理想主义,都是心理-社会性的,就像弗洛伊德对性欲的关注是心理-性的。阿德勒和弗洛伊德后来都被不如他们细腻的思维所字面化了。正如认为弗洛伊德的兴趣在于性欲本身是一个误解一样,认为阿德勒的关注在于社会(或荣格在于宗教)也是一个误解。阿德勒在其心理学中表述的是心灵的内在利他主义,正如弗洛伊德详细阐述了心灵的性欲,以及荣格的心灵宗教性。
因此,社会存在是人类存在的必要条件。个体越成熟,这种社会兴趣就越能决定其行为和目标。作为有灵魂的存在,我们天生感到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类紧密相连。荣格通过历史上、文化和本能中的原型模式客观地展示了这种普遍联系,而阿德勒则关注这种联系的情感和活动——它是如何在实践中运作的。人类在面对其普遍社区的利他情感时是如何表现的?这里的哲学背景是康德的伦理学,即人际关系的绝对命令。
总结 总之,心理治疗的核心在于帮助个体认识到,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并非终极现实,而是引导他们前行的虚构。这些虚构并不是否定或贬低,而是提供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实践价值。同时,阿德勒强调的社会兴趣提醒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感和利他行为是人类存在的本质特征,是我们在生活中必须重视和培养的部分。
如何将康德的伦理理想与尼采的权力意志结合起来? 如何在世界上将康德的伦理理想与尼采的权力意志结合在一起?答案就在世界中!阿德勒理论通过借鉴康德的理念解决了“两大趋势”之间的表面冲突:即先天的社会兴趣(Gemeinschaftsgefühl)和对优越性的先天追求(U, 120)。为了使引导性虚构具有启发性而非神经质,它必须是合理的,并反映常识以及关于世界的普遍有效的结论。只有当一个人的行为合理时,他才能成为优越的,这意味着承认社会兴趣,从而使自己的行为从世界的角度看是优越的,并且对他人的有用。
因此,在阿德勒看来,天才不是离群索居、超前于时代的人,也不是社会的局外人。“一个天才首先是一个极具用处的人。”“人类只称那些为公共福利做出巨大贡献的个人为天才。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给人类留下任何好处的天才”(A&A, 153)。处于极端顶端的优越性终极虚构,即天才的幻想,也是为了服务社会兴趣。事实上,天才最能感知到共同体生活的铁律,并表达出“宇宙的一般相互依存性,这种依存性存在于我们内部,我们无法完全从中抽象出来,并赋予我们感知他人情感的能力”(ELL, 609)。
因此,当我们再次问阿德勒,灵魂想要什么?它的先天意图是什么?我们现在听到他回答:它渴望社区。它希望在一个反映宇宙意义的世界中理性地生活,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灵魂作为这一秩序的潜力以目的为导向,并赋予每个行为意义,仿佛每个行为都“为生活做出了贡献”,推动其向共同体和宇宙的完美发展。“贡献是生命的真实意义”(L, 14)。
但是——而且这个“但是”非常重要——“意义的领域,”阿德勒说,“就是错误的领域”(L, 9),因此,我们赋予灵魂所欲求的每一个意义,以及他说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意义,“都或多或少包含着错误”。因此,灵魂所欲求的必须是对它所提出的每一种意义的虚构误解。这可能是唯一能够让人类共同体实现阿德勒所设想的完美的途径。
总结 总之,阿德勒认为,康德的伦理理想和尼采的权力意志可以在现实中找到结合点。通过合理的社会兴趣和对优越性的追求,个体可以实现对社会的贡献,而这正是天才的本质。灵魂的真正愿望是追求共同体和宇宙的完美,而这一过程中的每一个意义都是带有一定错误的理解。这种虚构的误解不仅不会阻碍进步,反而为人类共同体提供了实现完美的可能路径。
我们不能用任何确定性或目标来回答灵魂的渴望 我们不能用任何确定性或目标来回答灵魂的渴望,而不同时意识到这个目标是一种虚构,并且将其字面化是一种错误——即使这是一种必要的错误。确定性是对单一意义的认同;一个人将自己的私人意义确立为“终极立场”(L, 146),这只会孤立自己,违背我们的先天利他主义,使我们与人类社会疏远。这种孤立也是疯狂的表现。(“最高的孤立程度表现为疯狂”,[L, 184])。因此,即使是阿德勒自己的社区目标,如果以字面的确定性来看待,也会使我们孤立,如我们在改革者、善意者和恐怖分子中所见。他们越是以确信的方式认同自己的Gemeinschaftsgefühl(社会兴趣),就变得越孤立和疯狂。(然而,在他们失败和无助的时刻,他们会同理地融入他们试图主导的社区)。
Gemeinschaftsgefühl与灵魂的需求 Gemeinschaftsgefühl无法直接回答灵魂想要什么或呈现其目标;它只能作为反映我们所有目标的工具。这些目标是否有助于他人?它们是否体现了对他人的关怀?因此,Gemeinschaftsgefühl提供了一种发现我们孤立的虚构和错误的方式。如果我们有任何共同之处,那是在我们对错误的同理心和由虚构感带来的幽默宽容中。我们之所以为人,更多是因为我们的不足,而不是因为我们理想的目标。所以,不完美感,即荣格所说的阴影,是实现阿德勒Gemeinschaftsgefühl目标的唯一可能基础。荣格也说过类似的话(CW 10: 579):“关系不是建立在……完美之上……而是建立在不完美之上,基于弱点、无助……依赖的基础和动机。”
荣格的观点与阿德勒的转折 以荣格的一句话结束会错过阿德勒的独特视角。弱者的阴影不仅是道德上的;它也是幽默的。进入不完美的最佳途径是幽默、自嘲、在笑声中溶解,这种可以接受的羞辱不需要事后补偿。不完美的感觉可能是通向社会情感的一种方式;而更为可靠的方式是人类共有的幽默感。
原型心理学中的虚构感 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并不声称是一套要验证的假设,而是一套虚构(ELL, 631)。当弗洛伊德在给荣格的信中和荣格在给弗洛伊德的信中都说阿德勒不是心理学家(FJL, 147 F 和 217 J)时,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理解他们的意思。在考察了阿德勒的视角后,我们现在更能注意到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学设定的限制。如果不考虑阿德勒的观点,心理治疗将缩小视野并失去其原本的一部分根基。
总结 总之,我们不能通过确定性或具体目标来完全回答灵魂的渴望,因为这样做会使我们陷入孤立和疯狂。Gemeinschaftsgefühl作为一种工具,帮助我们反思和修正自己的目标,使我们意识到自身和社会的联系。不完美感和幽默感是通向社会情感的关键,而阿德勒的虚构理论为心理治疗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超越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局限。
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学”的定义 当弗洛伊德和荣格使用“心理学”一词时,他们当然指的是自己的研究项目——绘制深层心理的地图,探索其不可见的层次和动态机制——以解释人类生活的所有表面行为,从症状和观点到宗教和文化。对他们来说,心理学意味着:对普遍存在于个体生命之下的客观但不可见过程进行详细解释。弗洛伊德和荣格都是神话创造者和宇宙起源论者,他们构建的世界观之间的差异虽然显著,但与阿德勒相比,并不是根本性的。
阿德勒的不同之处 阿德勒所做的却是另一回事——这本身就很了不起。想象一下,在弗洛伊德天才思想萌发之初就加入了他紧密的小圈子,并且也在荣格个性的影响范围内待了九年,不仅提出了不同的心理学理论,而且基于完全不同的前提工作,从而对心理学本身有了不同的理解。阿德勒并没有试图建立一个客观的解释系统。他没有涉及区域、层次、心理能量学的核心、心因性、转化和极点,也没有一群在幕后活动的精灵。他不是一个神话创造者。
不同的基础和影响 通常,阿德勒与弗洛伊德和荣格之间的差异被归结为不同的哲学基础和社会学影响。埃伦伯格(Ellenberger)则提出了一个更有趣也更具心理学意义的对比(ELL, 889–91)。他认为,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基本理论源于他们在“创造性疾病”期间的个人经历。个人的、类似萨满教的幻象成为自我验证的信念体系,随后需要通过实证验证和信徒的灌输(培训分析)来巩固。相比之下,阿德勒的思想反映了“客观临床研究”(同上)。因此,可以推测,他更少寻求验证,而更多地进行比喻的非字面化。
对埃伦伯格观点的保留意见 我并不完全同意埃伦伯格的观点。不能说三者中任何一人更不客观或更自闭偏执。在我看来,弗洛伊德和荣格属于古老智者的预言传统,背后移动的是原型的老者形象(senex)。尽管阿德勒努力告诉我们如何生活以及生活应有何种意义,他的心理学仍然具有主观性和解释学的特点。它总是将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的虚构、权力驱动和自卑感。弗洛伊德和荣格为我们提供了意义,而阿德勒则迫使我们透过这些意义看透本质。因此,阿德勒是所谓“后现代意识”的先驱,比弗洛伊德和荣格更为明显,后者在阐述心灵的客观性质时提供了元心理学假设系统。相反,阿德勒开辟了将心理学作为一种虚构模式的道路。随着经典深度心理学逐渐演变为正统,阿德勒的思想对其既是一种补充也是一种挑战,这种作用比五十年前或七十年前更大,当时这些思想被视为关于意识的客观概念,而不是作为意识的方法。
阿德勒的现象学观点 阿德勒是一位现象学家,他希望从意识内部理解意识,而不依赖于外部结构,因为这些外部结构总是意识的虚构(参见 LA-S, 43)。因此,他写道:“无意识……并不是隐藏在我们心灵的某个无意识或下意识角落,而是我们意识的一部分,其意义我们尚未完全理解”(A&A, 232f.)。
心理理解的本质 需要理解的是主观性的虚构本质,以及心理理解本身的本质。因此,“无意识”主要指的是我们对塑造我们生活的主观虚构不清楚。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变得“有意识”意味着认识到所有行为背后的游戏幻想;而心灵对心理治疗理解的需求意味着它希望意识到自己的幻想。
关于心灵的疯狂问题 例如,让我们看看阿德勒如何处理关于心灵的反复出现的问题:什么是疯狂?正常、神经质和精神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弗洛伊德和荣格都从主客体关系和能量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给出了系统、动态、科学的解释。阿德勒则提供了一种解释学的解释,完全在意识领域内,探讨意识如何意图世界。(“人类生活在意义的领域中”——这是他一本书的开篇[L, 9]。)
疯狂不是能量固定或撤回、过去情境、未补偿的一边倒、转化为毒素的问题;疯狂是一个解释问题,一种错觉的创作——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疾病,心理障碍,无法用客观术语描述。
虚构到假设再到教条的变化 阿德勒说:“我欣然追随Vaihinger的观点,他认为历史上观念倾向于从虚构(不真实但实用的构造)发展为假设,再后来成为教条。”“这种强度的变化大致区分了正常个体(将虚构视为便捷工具)、神经质者(试图实现虚构)和精神病患者(将虚构具体化为教条)的思维方式”(NC, 169; A&A, 247)。
正常人与神经质者的区别 阿德勒说,正常人以比喻的方式看待指导原则和目标,有“仿佛”的感觉。“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都是语言表达”,是启发性和实用的构造。“然而,神经质者抓住虚构的稻草,将其实体化,赋予其现实价值。”最终,“在精神病中,虚构被提升为教条。符号作为‘言说方式’主导着我们的言语和思想”(NC, 29–30)。使疯狂的是字面主义。
总结 总之,阿德勒认为,意识的理解应从内部进行,无意识是我们意识的一部分。心理理解的关键在于认识到我们生活中的主观虚构,并通过心理治疗意识到这些虚构。疯狂不是能量问题,而是解释和认知的问题,涉及虚构的过度字面化。阿德勒强调,正常人将虚构视为实用工具,而神经质者和精神病患者则分别试图实现和具体化这些虚构。
阿德勒心理健康的洞见 深入探讨阿德勒关于心理健康和疯狂的心理学,往往会因为弗洛伊德学派和荣格学派过于字面化地理解他们的指导性虚构而被视为“非心理学”。当阿德勒说“必须避免将性虚构,即所谓的‘言说方式’或我称之为‘性行话’当作原始体验”(NC, 158)时,弗洛伊德学派被迫重新审视其关于性力比多的元心理学理论。如果按照阿德勒的观点,私人世界和对立思维是神经质的表现,那么荣格学派则需要重新审视其内向性和对立性的理论。如果荣格学派和弗洛伊德学派不愿意将其所有假设置于“仿佛”的模式中,他们就会失去对所有心理学陈述的暂时性和脆弱性的敏感,失去与心灵本身的联系,并退回到基于被提升为积极理论原则的神经质防御机制的治疗。
对心理治疗的阿德勒式批判 我们现在开始了对心理治疗的阿德勒式批判。我们始终围绕着第一个问题:灵魂想要什么?假设灵魂以那些被压制、被忽视的声音说话,如孩子、女性、祖先和死者、动物、弱者和受伤者、叛逆者和丑陋者、被审判和囚禁的阴影,那么任何心理治疗的任务就是保持与这些被忽视者的联系并为之所动。
然而,从阿德勒的角度看,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摆脱自卑感,由此发展出神经症。当治疗通过教条和职业的字面化虚构来保护自己免受必要的自卑感时,治疗本身也可能变得神经质。这时它甚至失去了意识,即使是以意识的名义。它有风险不再是为心灵而进行的心灵治疗,而是成为一种私人的世界活动,称为“分析学校”,发展出一种生活方式以凌驾于心灵之上。
在过去的十年左右,一些荣格心理学思想家在不同地方提出了对治疗的批判,偶尔以原型心理学的共同名义出现,他们的著作展示了与我在此介绍的阿德勒思想惊人相似的方面。我想回顾他们的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额外的乐趣,因为他们是我的同事和朋友。
总结 总之,阿德勒对心理健康和疯狂的见解揭示了弗洛伊德和荣格学派在过于字面化其理论时的局限性。阿德勒强调,心理学陈述应保持其暂时性和虚构性,否则会失去与心灵的真正联系。阿德勒式的批判指出,心理治疗不应忽视自卑感,而应通过与被忽视者建立联系来促进真正的治愈。此外,近年来荣格学派内部也出现了类似的批判声音,进一步丰富了这一领域的讨论。
斯图加特的沃尔夫冈·吉格尔里希 在斯图加特,沃尔夫冈·吉格尔里希将对虚构的考察直接带入了理论本身。他试图表明,神经症不仅仅是患者的一种状态,由治疗来治愈;而是当心理治疗中使用的概念未被审视时,神经症会得到助长和固化。治愈、治疗、积极与消极、自我与无意识、母权制和发展阶段,这些都不是字面上的“现实”,而是启发性的虚构或幻想。如果心理治疗要保持与其学科自身“神经症”的联系(如吉格尔里希所称),就必须认识到这些是虚构。正如他所说:“心理学本身必须成为它自己的第一个病人”(SP 1977, 168)。
克拉克大学的玛丽·沃特斯 克拉克大学的玛丽·沃特斯也提出了类似的呼吁,要求在心理理论中保持与自卑感的联系。她的研究重点是积极想象的方法。她指出,神经质的概念在旨在治愈神经症的疗法中仍然起作用。在指导人们如何处理内心空间中的图像时,最常见的企图是主宰和利用较低、较暗、较弱和较丑的心灵,以实现自我优越的虚构目标。我们问的不是它们想要什么,而是我们的自我想要什么。她的工作证实了一种基本的原型态度,这种态度在阿德勒和荣格那里也能找到:只要个体将灵魂想象为他自己“私人的内心世界”,他就自然会认为可以用自己的意图主宰这个空间。实际上,个体存在于更广泛的心理和社会背景中。
苏黎世的阿道夫·古根布吕尔-克莱 在苏黎世,阿道夫·古根布吕尔-克莱在其简短而根本性的著作中发展了对立思维的思想,这也可以被称为阿德勒式的。他的关注点也是阿德勒式的:权力、所有助人职业中对优越性的追求以及弱者和强者(患者与医生、学生与教师等)之间的两极分化。他认为,这种破坏性的对立发生在医生失去对自己脆弱性的认识、教师失去对自己的无知的认识、社会工作者失去对自己的非道德行为的认识时。古根布吕尔认为,帮助和治愈完全依赖于保持对自卑感的阴影意识。
总结 吉格尔里希、沃特斯和古根布吕尔-克莱的工作共同强调了在心理治疗中保持对自卑感的敏感性的重要性。吉格尔里希指出,心理治疗中的概念如果不被审视,可能会助长神经症;沃特斯揭示了治疗过程中存在的自我中心倾向;而古根布吕尔-克莱则强调了助人者保持自我反省的重要性,特别是对自身弱点的认识。这些见解提醒我们,心理治疗不仅应关注症状的缓解,还应深入探讨其背后的虚构和假设,以实现更深层次的治愈。
苏黎世的阿尔弗雷德·齐格勒 苏黎世的另一位荣格学派精神科医生阿尔弗雷德·齐格勒(Alfred Ziegler)从事心身医学和机械梦研究。他的研究(参见 SP 1976)延续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另一个主题:器官自卑感。齐格勒通过对其对梦境和所谓的“心身症状”的研究发现,我们的痛苦是心理物理性的,且具有独特性。统计上,梦中表现出更多的不悦而非愉悦;身体长期处于自卑状态,并且不可治愈地对无症状健康和积极、促进生命等引导性虚构免疫。我们的自卑感反映了人类心理物理存在根本的有机自卑,这种存在只能在相对不适的状态下维持其意识的紧张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失去对有机自卑感的认知不仅是错觉性的,而且是自杀性的。
委内瑞拉的拉斐尔·洛佩兹-佩德拉扎 阿德勒的另一个概念,即心灵两性同体论,一直是委内瑞拉的拉斐尔·洛佩兹-佩德拉扎(Rafael López-Pedraza)的主要研究课题。他在加拉加斯大学的研讨会上探讨了一种意识形式,这种意识形式体现在赫尔墨斯、心灵和卢娜的神话中,从未放弃其弱点,始终处于边界线上,不分离成男性与女性、善与恶、进步与退步的对立字面主义。这些对立只作为引导性虚构,完全以其治疗效果,即对灵魂的影响来判断。他一直在神话人物,尤其是赫尔墨斯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原型意识,这与普罗米修斯式的自我及其必要的对立和字面主义完全不同。
帕特里夏·贝里的女神研究 在几篇关于盖亚、得墨忒耳和珀尔塞福涅女神的论文中,帕特里夏·贝里(Patricia Berry)将自卑感的概念深入到原型层面,触及母性和物质形象内部的空虚。存在的支持基础本质上是缺乏的,总是渴望着某种东西,而这种渴望正是心理治疗试图通过实践和理论中的各种实质化来克服的。她的工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来理解自卑和极端,一种回归或追溯到空虚作为本质本身的途径,从而使心理治疗不必成为对抗必要病理或灵魂痛苦的防御系统,而是开放我们通往更深层次的基础。
总结 齐格勒的研究强调了心身痛苦的独特性和不可避免性,指出身体的慢性自卑感和对健康幻想的免疫力。洛佩兹-佩德拉扎的工作则探讨了心灵两性同体论,强调保持弱点的重要性,并避免对立的字面主义。贝里的研究将自卑感带入了原型深度,揭示了母性和物质形象中的内在空虚,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使心理治疗可以不再是对抗痛苦的防御系统,而是通向更深层次理解的途径。
苏黎世的阿尔弗雷德·齐格勒 苏黎世的另一位荣格学派精神科医生阿尔弗雷德·齐格勒(Alfred Ziegler)从事心身医学和机械梦研究。他的研究(参见 SP 1976)延续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另一个主题:器官自卑感。齐格勒通过对其对梦境和所谓的“心身症状”的研究发现,我们的痛苦是心理物理性的,且具有独特性。统计上,梦中表现出更多的不悦而非愉悦;身体长期处于自卑状态,并且不可治愈地对无症状健康和积极、促进生命等引导性虚构免疫。我们的自卑感反映了人类心理物理存在根本的有机自卑,这种存在只能在相对不适的状态下维持其意识的紧张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失去对有机自卑感的认知不仅是错觉性的,而且是自杀性的。
委内瑞拉的拉斐尔·洛佩兹-佩德拉扎 阿德勒的另一个概念,即心灵两性同体论,一直是委内瑞拉的拉斐尔·洛佩兹-佩德拉扎(Rafael López-Pedraza)的主要研究课题。他在加拉加斯大学的研讨会上探讨了一种意识形式,这种意识形式体现在赫尔墨斯、心灵和卢娜的神话中,从未放弃其弱点,始终处于边界线上,不分离成男性与女性、善与恶、进步与退步的对立字面主义。这些对立只作为引导性虚构,完全以其治疗效果,即对灵魂的影响来判断。他一直在神话人物,尤其是赫尔墨斯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原型意识,这与普罗米修斯式的自我及其必要的对立和字面主义完全不同。
帕特里夏·贝里的女神研究 在几篇关于盖亚、得墨忒耳和珀尔塞福涅女神的论文中,帕特里夏·贝里(Patricia Berry)将自卑感的概念深入到原型层面,触及母性和物质形象内部的空虚。存在的支持基础本质上是缺乏的,总是渴望着某种东西,而这种渴望正是心理治疗试图通过实践和理论中的各种实质化来克服的。她的工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来理解自卑和极端,一种回归或追溯到空虚作为本质本身的途径,从而使心理治疗不必成为对抗必要病理或灵魂痛苦的防御系统,而是开放我们通往更深层次的基础。
总结 齐格勒的研究强调了心身痛苦的独特性和不可避免性,指出身体的慢性自卑感和对健康幻想的免疫力。洛佩兹-佩德拉扎的工作则探讨了心灵两性同体论,强调保持弱点的重要性,并避免对立的字面主义。贝里的研究将自卑感带入了原型深度,揭示了母性和物质形象中的内在空虚,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使心理治疗可以不再是对抗痛苦的防御系统,而是通向更深层次理解的途径。
索诺玛州立大学的戈登·塔彭 在索诺玛州立大学,戈登·塔彭(Gordon Tappan)曾是一位阿德勒学派的精神科医生,后来成为荣格学派的追随者。他在研究生教育中进一步结合了自卑感和社会感。他创新的原型心理学学位项目依赖于他在社会群体中的治疗师-教育者的角色。他追随了阿德勒一生的兴趣之一——教育(参见 [19]),在这个项目中实践了灵魂对心智的需求以及心智对灵魂的需求。他的工作将学术纪律与个人形象结合起来,试图弥合心理的逻各斯(logos)与其治疗之间的分裂。
康涅狄格大学的查尔斯·博尔和彼得·库格勒 在康涅狄格大学,查尔斯·博尔(Charles Boer)和彼得·库格勒(Peter Kugler)(SP 1977)提出了一个感知理论,该理论——如同阿德勒所尝试的那样——拆解了心灵中的私人世界、私人的无意识和私人体验的意象等概念。他们的理论重新赋予街道上的世界以重要性,即它如何立即被想象出来。这种心理学回归街道是达拉斯人文研究所的罗伯特·萨德尔洛(Robert Sardello)发起的项目的首要关注点。
达拉斯人文研究所的罗伯特·萨德尔洛 他的主要隐喻“城市”使阿德勒的社会和教育兴趣得以深入到更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学中。通过使用隐喻和想象的方法来审视我们日常城市生活中的现象,他的研究将城市的灵魂与灵魂的城市联系起来。保罗·库格勒(Paul Kugler)关于器官语言的工作也在这里进行,即将身体转化为言语意象。库格勒使我们更接近于这样一个观念:我们的引导性虚构最好体现在言说方式(modus dicendi)中,即那些“主导我们言语和思想”的词语(阿德勒语),从而开辟了一种新的方法来探讨精神病的诗学,即当语言被字面理解时所固有的疯狂。
总结 塔彭的工作通过结合自卑感和社会感,在教育中实践了阿德勒的思想,强调了灵魂和心智之间的相互需求。博尔和库格勒的感知理论挑战了传统的私人无意识观念,重新重视外部世界的直接体验。萨德尔洛则通过“城市”的隐喻,将心理学带回日常生活,探讨城市生活的灵魂,并通过隐喻和想象的方法将其与个体的灵魂联系起来。库格勒的研究则揭示了身体语言与言语表达之间的关系,指出我们的引导性虚构最能体现在言语表达中,这为理解精神病的语言表现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时间限制下的简要评述 时间限制了这篇关于我的“Gemeinschaftsgefühl”(社会兴趣)的论述,仅能对少数几个人物作简要评论。然而,我不能不提及大卫·米勒(David Miller)和鲁道夫·里特塞玛(Rudolf Ritsema)的重要工作。在米勒众多复杂贡献中,我想特别指出他的方法论。与其说是他勤奋的学术研究及其从中得出的研究成果和思想,不如说是他通过阿德勒的“junktim”(即瞬间洞察)、隐喻、语言并置、反转和奇特的思想、领域和时期的组合,尤其是通过幽默,使每一句话都透出一种虚构感。他的写作风格开启了一种心理治疗的智力方法,因为这种严肃性防止了自我字面意义上的认真。他尝试创造一种边界的诗学,试图阻止心灵分裂成所谓的“理智”和“疯狂”。
鲁道夫·里特塞玛自1972年以来在《春之年刊》上连载发表的《易经》研究,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西方语言习惯的心理学洞见,其中字面主义的虚构最为隐蔽地嵌入。里特塞玛展示了如何在使用词语时坚持意象。他的“意象语法”打破了依赖因果关系和线性思维、陈述的积极性、教条等精神习惯——这些正是阿德勒所警告的通向疯狂的道路。里特塞玛对《易经》的审视还暗示,那两个守护着心理治疗入口、像复活节岛上的哑石巨人般的图腾柱——我指的是男性和女性——是现代单一体的具象化,是一对被具体化的神经质对立面,无法从阴/阳意象的流动变化中获得支持,而这些意象总是微妙、分化且精确的。
这些朋友的工作,以及我自己反复撰写的关于失败、抑郁、背叛、自杀、受伤、异常、衰老和从冥界出发的文章,或许有助于传达当代心理治疗中基于体验性自卑的一股潮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像心理治疗中的道家,坚守低处、黑暗和弱小的地方,坚守着学科赋予的卑微、黑暗和脆弱的灵魂状态。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工作如同禅宗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工作如同禅宗,试图看穿意识中的主观虚构(ELL, 624),消解那些意识所认同并命名为成为意识方法的字面主义:对立思维、创造个体主观性的私人世界和解释这些世界的客观概念体系,或是虚构目标及其伴随的乐观情感。我们的“禅”时刻警惕着,以防心理治疗的概念及其关于无形事物的理论掩盖了灵魂的鲜明存在。
第四节 社会感知 所有精神障碍唯一共同的特点是失去了“sensus communis”(社会和公共感知)以及补偿性地发展出一种“sensus privatus”(私人的推理方式)。——伊曼努尔·康德
现在我们回到最初关于灵魂愿望的问题,并转向实际对话。在这些对话中,倾听灵魂的困难似乎不那么阻碍我们,因此我们有更好的机会听到它的愿望。
第一个例子来自一位年轻的离异教师,一位与女儿同住的德国女性。她体现了荣格意义上的强烈阿尼姆斯发展,或阿德勒意义上的男性抗议。她自己的女儿并没有承载她的灵魂价值观,因为她的女儿太像年轻版的自己,是一个适应性强、积极进取的小女孩。相反,在她的幻想中出现了另一个小女孩,一个仿佛是她的女儿,有着大眼睛和黝黑的皮肤,就像我们在饥荒海报和救助儿童呼吁中看到的形象。有时这个小女孩也是一个7到11岁之间的男孩:心灵上的阴阳人。我们正好在问题被提出的地方进入对话。这位女士说:“那你想要什么呢?”
孩子与女人的对话
孩子:让我自己待着,永远不用做任何事。你总是逼我。
女人:我希望你长大。(请注意,我们已经从孩子的愿望转向了女人的愿望。孩子处于守势。)
孩子:这样有什么好?
女人:那样你就不会成为那么沉重的负担。
孩子:如果我必须为了你的缘故而长大,那我不干。
女人:真固执!(女人写道:“我当时非常愤怒[rasend],呼吸急促。”)
孩子开始哭泣,然后说:“教我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想学习。”(这时,女人突然发现自己也在抽泣,因为她毕竟是一名教师。她说她哭“不是作为孩子,而是作为她自己”。她意识到这个灵魂中的孩子是她成为教师的原因——既是天职也是职业。)第二天晚上,她回到对话中:
女人:一开始你说你想自己待着,然后又说要教我。我不明白你。
孩子:你不明白我。
女人:如果我让你自己待着,我就没有教你;如果我在教你,就没有让你自己待着。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你。
孩子:你不知道该怎么对付我。
女人:你让我觉得自己很蠢。和你在一起时,我从未感到如此低人一等。
孩子:很好,现在你可以教我了。
女人:我还是不明白。
孩子:当你明白了,你就不能教我了,因为那时你不再尊重我的无知。对于你来说,理解我就意味着逼迫我。
请教给我你知道的东西,你读过的东西。教我心理学,关于心灵的知识。我想学会思考,学会理解,而不是如何行为。这里可以看出思维与情感之间的紧密互动。它们并不是对立面。在这里,对孩子的情感表达就是教会他思考。我还想指出这段对话中的阿德勒内容:只有当她承认自己的自卑感,针对这种自卑感(即孩子)的治疗才开始。但我通过这段灵魂虚构或主动想象的主要意图是展示心理学对心理治疗的相关性,即灵魂想要学习心理学,想要对自己进行深思熟虑的表述,这是它治愈的一种方式。
这位女士倾听了。她开始以不同的方式阅读心理学,不是为了获取信息来应用于教育,也不是为了成为一名分析师,而是结合她的经历,尤其是她的自卑感、她软弱且沉默的孩子。
我想再读几段其他人的例子,说明灵魂对心理学的渴望,对心理学智慧和智力的需求,以及对心智敏锐、准确和深刻的运用。有时,灵魂形象会说:“别这么傻”,或者“动动脑子”,或者“停下这些空谈,想想你在说什么!”
我们的下一个例子来自战后几年的一位英国男子。他曾受过伤,在殖民地军队中过着英雄般的生活。他的左肩受伤,心脏也受到影响。在想象中,他刚刚开始与一个自称谢巴的畸形驼背黑人妇女对话。
谢巴与马克的对话 谢巴:我无法忍受让你看到我。你为什么要来?我受不了。走吧。
马克:我怎么能走呢?这就像要我离开我的心和左臂。
谢巴:我是你的心和左臂。这就是我的驼背在你身上的样子。
马克:日本人打你的时候也打了我,是吗?
谢巴:你很勇敢。
马克:你的赞美?
谢巴:你很勇敢。
马克:我可以碰你吗?
(他写道:谢巴站在一个浅绿色的房间里,赤裸着身体。她极度畸形:弯腰驼背,后脑勺略低于驼峰的最高点。她是黑色皮肤,身体非常瘦弱,但仍有昔日美丽的痕迹。他走近她,触摸她的驼背,并缓缓地轻抚它。她哭泣了。)
谢巴:他们根本不该让你进来。离开我,离开我。
马克:我会回来的。
(他确实按她所愿离开了,表现出对何时结束的高度敏感。第二天,他陪她在实际的泰晤士河堤岸散步,并边走边记录下这些对话。)
谢巴:我以前从未出去过。
马克:从来没有吗?
谢巴:不是像这样……不是独自一人。只是在另一个女人的存在中混杂在一起。她的存在融入了我的存在,除非我想把她从你身边赶走。或者把你从她身边赶走……(在这段话中她变得气喘吁吁)。请慢一点。
马克:(放慢脚步)这样可以吗?
谢巴:还是太快了。这是你第一次看到我。
马克:(尽可能缓慢地行走)这样可以吗?
谢巴:如果我要和你在一起,有时你得把一切都放慢——走路、思考、说话。(他们走到一个角落,遇到快速移动的繁忙交通。)
谢巴:哦,我很害怕。
马克:别担心。没关系。你觉得怎么样(他们一起过马路)?
谢巴:你可能无法理解我说的——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就只是和你一起散步。
将灵魂带入街头,并在街头照顾它,而不是在他人存在的混乱中,也不是在个人内心的独白和情感中。而是将心灵带入生活——随着生活的步伐前行——这是谢巴所教导的所罗门式的智慧。
这段对话的一个特征在年轻外科医生乌尔里希的案例中早已出现。当情感变得非常强烈时,叙述会转为间接表达,仿佛自我试图从想象中的强度中抽离。在乌尔里希的案例中,他不让那个灰暗的人直接说话;而在马克的案例中,则是他看到谢巴赤裸、黑色且畸形的身体,以及触摸她身体的那一瞬间。
他们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世界、街头还是身体,不仅使马克重新连接到他在“另一个女人的存在混乱中”失去的灵魂(阿尼玛),也使他意识到自己过快的生活节奏,并重新找回了他的勇气和生活的决心。阿德勒说过,没有目标的勇气是毫无用处的。谢巴通过提及马克的勇敢,恢复了他在战争时期所拥有的勇气,那时目标是明确的。现在,她将这种勇气与她自己联系起来,成为他们在心灵塑造中的对话。他们整个相遇的过程,包括他们在街头的漫步,都体现了面对残缺丑陋灵魂所需的勇气,以及像街头繁忙交通一样认真对待自己的自卑感。
马克和谢巴之间对话更深层次、更具哲学意味的含义,在我们最后一个摘录中得到了更好的呈现。这次摘自一位经验丰富的折衷派心理治疗师,他曾到苏黎世接受更深入的荣格训练。再次重复我们的主题:
他:你想怎么样?
“我想出去,”一个他称为“灵魂之声”、“阿尼玛”、“胸腔之声”或“我的人”的声音说。
他:出去!听起来你像是个囚犯。
灵魂之声:我没有这么说。我不是在责怪你。你无论好坏地把我留在里面。保护我。但我想出去。
他:我不明白。(同样的句子!)我花了这么多年才找到你,并把你作为心理学因素引入内心,正如荣格所说,[21]这样我们才能进行这样的对话,让你出去意味着又要开始那些投射。
灵魂之声:你害怕让我出去,那么你在保持一种不好的状态:不是保护我,而是保护你自己。我是个囚犯。
他:仅仅是想让你留在心里并保持心理上的存在,就让你成了囚犯吗?
灵魂之声:你是把我囚禁在你的心理系统中,阻止我随心所欲地出现。
他:你所说的“随心所欲”让我害怕:这意味着阿尼玛的吸引力、愚蠢的商业投机、无谓的追逐。当你“出去”时,我就变成了一个傻瓜。我承受不起。我必须保护自己。
他对这种对立的状态感到不满,他自己作为灵魂的看守。她让他困惑不已。一方面,当他顺从她的意愿时,他觉得自己不够强大;另一方面,当他坚持自己的方式时,他又变得强硬和过于自信。他试图找到一种既柔软又可塑的方式,同时又不会让自己如此脆弱以至于需要掩饰和封闭。两天后,他再次回到对话中:
他:我对你就太强硬了。我没有倾听。我只是解释并告诉你我的恐惧。
胸腔之声:没关系。不急。我喜欢你的错误。[22]
翻译如下: 他:即使是和你在一起?
胸腔之声:每次你犯错时,你都离我更近,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当你处于顶峰时,对我而言你是最糟糕的。【再次注意阿德勒的语言风格。】你现在应该知道,你只有在生病或有心脏症状时才会找到我。
他:但我的错误正是使我们疏远的原因。我指的是像这次这样总是解释而不倾听。
胸腔之声:这并不重要,只要你能感觉到你的错误与我有关,它困扰着你,啃噬着你,无论最近发生了什么,比如两天前的事,一直在折磨你。这就是我喜欢分析的原因,也是你成为一个好分析师的原因。它让你担忧,不舒服,就像鞋里有一颗小石子。每走一步都有点疼。
他:我可以回到我的问题吗?
胸腔之声:当然可以。你不需要我的许可。那又是你的一个错误。直接和我说吧。你在想什么?不要这么小心翼翼。
请注意,即使是这位资深的分析师也难以找到与灵魂对话的正确方式。你是否注意到他变得多么顺从和自卑,而其他人则变得专横?现在我们进入关于灵魂意图的更哲学的部分。
他:我的问题是:你所说的“出去”是什么意思?
胸腔之声:成为你小中的大。只要我在里面——在你的内心,在你的心理学中,在你的投射中——我就永远无法完全展现自己。你还没有真正认出我。
他:但你不应该是待在里面吗?作为我的内在自我?
胸腔之声:你被困在词语里了。内在只是意味着更深。向内走只是意味着更深入地进入事物,进入它们的核心和灵魂。内在是一种向内的空间感,是胸腔中回响的空洞。它不是一个地方,也不意味着你所学到并如此字面理解的所有东西:内倾、内省、内化。
他:我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
胸腔之声:那就别说。
这段对话展示了即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分析师也难以找到与灵魂沟通的恰当方式。他在面对胸腔之声时表现出顺从和自卑的态度,而胸腔之声则试图引导他更深刻地理解“内在”的意义,并挑战他对心理学概念的固有认知。
一个星期多过去了,他才再次拿起这个问题,尽管他一直在努力应对她“想要出去”的愿望,却没有找到解决办法。事实上,他并没有再次主动提起这件事,而是在一次湖中游泳后发生了变化。当他从水中出来时,感受到身体被充满存在感的空间包裹着,空气有一种密度。他清楚地听到她说,声音如此响亮,仿佛是一种幻觉:“现在我出来了。现在你进来了。”
当他告诉我这些时,我提到了炼金术中的灵魂凝结;它变得浓稠,被感知为一种存在。这显然是像化学过程一样发生的。经过长时间的熬煮、搅拌和包容,突然之间,就像制作酱汁一样,凝固发生了。
他们之间的对话随后展开如下:
他:我现在明白了:所有这些女人,所有这些我经历的事情,都是你,阿尼玛,引导我进入的,我把它们称为投射,是为了让我感受到身处其中的感觉,感觉自己比所经历的事物更渺小、更低微。这就是为什么它总是太多。这就是阿尼玛占有我的秘密:向我展示你占有我,并且比我更大。如果我能承认这一点……不,如果我能保持这种对灵魂的低微意识,意识到我总是在某种心理状态下被拥抱,那么我不需要通过被占有来证明我是被拥抱的。
阿尼玛之声:我不能保证任何事情。我不服从补偿法则。那会把我重新关在某个东西里面。
他:那么这只是感觉到你在我周围的临在吗?
阿尼玛之声:这不是“只是”。也不是“感觉”。
他:那是什么呢?
阿尼玛之声:是存在。存在于灵魂中。
他:这是你想的,灵魂想要的吗?
阿尼玛之声:出去;无处不在;空间。
他:我在你的空间里移动。
阿尼玛之声:我在我们的空间里移动你。
他:我们的空间?你移动我?
阿尼玛之声:我的意象移动你,除非你移动,在水中游动时,你不会感受到空间。
这段文字描述了一个人在经历了与阿尼玛(内在女性形象)的深层交流后的心灵转变。他在自然环境中的一次体验让他深刻感受到灵魂的存在,并通过对话逐渐理解了灵魂的需求和本质。阿尼玛强调的是存在的状态,而不是简单的感知或感觉,表明心灵活动和意象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个体的心理状态和行为。
灵魂的空间只有通过你的行动才能形成——不仅是四肢的动作,还包括心灵和情感的活动。是的,还包括心灵的症状。除非你行动、做事、表现、思考、生活、愿望、欲望、想象,否则我是空虚的。我什么都不是,除非你在我的内容中移动。你是我的心理活动的场所;但不要把我局限在这些活动中。灵魂永远不等同于它的行为。我不是行为本身,而是行为中的意象。然而,不要试图从行为中提取我。我对任何你试图安置我的地方都是独立的,同时又完全依赖于进出那些我被保持的地方。我的广阔性完全取决于向外移动。
这段对话见证了灵魂的哲学维度。它让我们想起了科宾意义上的叙述(récit)。这些材料值得古代作家关注,因为它涉及古老的哲学问题。熟悉心理学历史的人会认出赫拉克利特的再现:一个无界限的灵魂怎能被“困”在一个渺小的人体内?人们会回想起狄奥提玛教导苏格拉底的教学风格,会记起普罗提诺坚持灵魂在个体意识中的自由移动及其与意象的内在联系,还会想起奥古斯丁在其《忏悔录》中对内外、大小问题的探讨。甚至亚里士多德的影子也在这段对话中浮现,他认为灵魂是第一推动者,其运动就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还会听到荣格的声音,他说“意象即心灵”(CW 13: 75),他说意识来自阿尼玛,后者是意识背后的生机,从中产生意识(CW 13: 62;CW 9.1: 57),他还说“人存在于心灵之中。”[23]
然而,这里有一个转折点:这段对话对患者的实际影响并不是哲学或想象力的提升,也不是对其内在性的进一步探索。相反,这位患者转向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方向。他发现了政治和社会世界。当他回到家后,他放弃了团体治疗,认为这是一种妥协,因为团体治疗不能让灵魂真正释放出来。相反,他加入了有社会目标的实际团体——医疗保险改革团体和环境保护团体。他开始在夜校教授课程,接受了专业协会的志愿者工作,同时也继续进行个人心理治疗实践。他找到了阿德勒认为的心理治疗唯一现实的目标——社会兴趣感(Gemeinschaftsgefühl)。
现在,阿德勒学派认为,社会兴趣感“不能通过理性的自觉决定来实现”(OC76, 15)。简单地敦促自己参与是行不通的。必须有一种宇宙观的转变,使一个人真正感受到身份的扩展。阿德勒写道:
“正确地”听、看或说话意味着……与他或它融为一体。认同能力使我们能够拥有友谊、爱人、同情心……这是社会兴趣的基础(A&A, 136),它可以扩展到……动物、植物、无生命物体,最终延伸至整个宇宙(U, 43)。
这段文字探讨了灵魂的本质及其与人类行为、思想和情感的关系,引用了多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观点,强调了灵魂的广度和深度。最终,它展示了如何通过实际的社会行动实现心理治疗的目标,反映了阿德勒关于社会兴趣感的重要思想。
我们目睹了这种身份的转变。最初位于患者胸腔最私密处的声音,被称为“阿尼玛”或“我的人”,赋予了他强烈的个人身份感,使他紧紧抓住灵魂作为自己私密的内在事件。这是一种所有权的感觉。然而,这种内在性滋生了自卑感:它在我里面;它渺小,我伟大;它在内部和下方,我在顶部并包含着它。我们观察到的运动是从“我的灵魂”到“灵魂”,从“我的阿尼玛”到“世界灵魂”,从主观感受转向被赋予灵魂的客观世界。请记住,灵魂的声音拒绝被视为仅仅是他的感受。
释放灵魂脱离字面意义上的内在性与凝聚它是同步进行的。只要它必须被保持,就会被想象为脆弱、易碎、有翅膀,像水汽般总想飞出去消失,如同一个仙女化作另一个人更坚实的形式。如果我们如此小心翼翼地保持灵魂,我们不是在溺爱它作为一个病人吗?我们不是进一步将心灵与街头的普通生活分离,剥夺灵魂的社区感和社区的灵魂感吗?
阿德勒警告不要将社会情感具体化为具有特定目标的具体社区。Gemeinschaftsgefühl “从来不是(仅仅)当下的社区或社会,也不是特定的政治或宗教形式。” 它意味着“永恒视角下的社区”(A&A, 142)。尽管这位男士确实进入了实际的社会服务领域,但他看到的不是这些服务的目标,而是这些服务成为了一个扩大的同情心可以生活和呼吸的地方。
如果我们问这种身份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并因此更深入地问社会兴趣本身是如何产生的(因为它不能通过自觉决定来实现),那么我们可以察觉到一种神话在起作用,使得认同能力成为可能。这个男人与灵魂的长期接触导致了爱。心灵引导到了爱欲。我们回到了我在《分析的神话》中试图呈现的内容:心灵与爱欲之间的关系作为心理治疗的主要神话。
我们的例子表明,他并不是先爱上灵魂,然后再将这份爱转移到世界上作为一种道德责任:善待他人。也不是因为灵魂先爱上了他,所以他才能将这份爱返还给世界。爱本身改变了性质,正如爱神与心灵的神话一样。现在,他不再是以“我”对“你”的方式去爱灵魂或关心它。现在,心灵与爱欲已经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当他与心灵在一起时,有一种爱包括了他作为其意象之一,并自然而然地扩展为同理心。通过感受到自己内心人物的重要性,他感到被他们所爱。不再是一个主体爱另一个对象。
这段文字探讨了个体如何从狭隘的自我意识转向更广阔的社会意识,以及这种转变如何通过与心灵的深层次互动而发生。它强调了心灵与爱的关系,并引用了阿德勒关于社会兴趣感的思想,指出真正的社会兴趣感是超越具体目标和形式的,而是一种永恒的社区感。
不是对世界的爱引导他走向世界,而是对灵魂的爱,因为灵魂作为世界灵魂(anima mundi),本身就是世界,是灵魂形成的场所。通过灵魂间接通往世界的爱经历了心理的多重错误迷宫。阿德勒可能会说,错误使爱变得心理学化,这种爱是对所爱事物身份的智能、差异化的理解。我们只有在能够识别每个面孔在其独特意象中的身份时,才能“正确”地识别。
我们的患者与他的病人和政治委员会的工作需要一种敏锐的爱的感觉,同时这也是一种心灵的感觉。他处理的不是人道主义原则和广泛的神秘情感,而是小而独特的个体差异的艺术。人(荣格说,个性化意味着差异化)。这种爱是差异化的观点也在一次进一步的对话中得到了澄清,我们将以此结束这段讨论。
他开始说:我看不到树木了,只看到森林。自从我感受到被你浓厚的存在感包裹以来,我感到被淹没。我想这就像湖中的体验。
声音:或者说是子宫。个体发生重演系统发生:灵魂-阿尼玛首先回归到母亲-阿尼玛。你正在重新连接到所有生命的源泉。沉浸在你自己的胸腔中。
他:我在你的空间里似乎失去了自己的空间。
声音:那么为自己创造一个空间吧。
他:所以你是要一个自我吗?
声音:你在解释了。我说的是为你自己创造一个空间。我没有提到自我:那是什么?你想知道灵魂想要什么;现在你知道了一部分;它希望你创造一个空间的地方。
他:我明白了!我一直处于虚无的状态,到处游荡,没有结构,没有层级,不知道什么东西属于哪里,无论是对我自己还是对任何人,除非我能安置它们。
声音:是的。问题不在于给他人空间或感受他们的空间,而是感知他们各自所在的确切位置,他们在其中移动的位置,他们所属房屋的哪一部分,准确且微小。位置赋予空间以意义。画布由细微的笔触构成,雕塑由雕刻而成,交响乐由微小的音符组成。分子,每个都在确切的位置。每个意象都是一个定位。你动得太快了,不够细致。
这段文字探讨了个体如何通过理解和接受灵魂的内在体验来找到自己的位置,并通过细微而精确的方式感知他人的确切位置。它强调了在心理治疗和个人成长过程中,细腻感知和定位的重要性,以及这种过程如何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
她的教导开始变得神秘莫测,我们在这里中断,因为理解她的陈述花费了比我们能支配的更多时间。但我们可以对最初的问题得出以下结论:
灵魂有许多愿望——被爱、被倾听、被命名和看见、被教导、被释放,走向街头,走出心理系统的监狱,走出内向虚构的束缚,这种虚构迫使它通过投射来获得外界的认可。我们也知道,它对其守护者的生活和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兴趣;但它对这些生活和行为的兴趣并不是为了帮助或治愈它们。相反,这似乎是一种为了灵魂本身而对生活的兴趣。它似乎在要求我们将首要的重要性从生活转移到灵魂上,让生活以灵魂为标准获得价值,而不是将灵魂的价值仅仅基于生活。因此,它不容忍在生活中被忽视——这一点最为重要;它就像古代的神祇,认为不敬是一切大罪中最大的罪,即忽视。
我们还看到,在心灵中,其逻各斯(logos)与治疗之间存在着一种活生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心灵需要心理学作为其治疗的必要条件,并且它需要心理治疗来构建其心理学。即使灵魂警惕于被囚禁在这种逻各斯中,在具体化的结构、系统、语言中,它依然是深刻哲学性的。正如我们所见,它进行哲学思考。心灵是一种智慧,它希望得到一种聪明的心理学回应。它的固有劣势并不意味着愚蠢;它不能依赖低级心理学的陈词滥调,甚至不能简单地接受大师们的高级思想。请记住那个说“我喜欢你的错误”的声音;那个说“我不服从补偿法则”的声音。心灵的治疗希望每个人都能研究心灵的逻各斯,成为自己的心理学家。
我们说过,心理学对灵魂的愿望给出了三个主要回答——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荣格主义——这取决于如何理解“愿望”这个词,是作为可怕的深渊、对实现的愿望,还是对完整性的追求。我们还可以从阿德勒那里读到另一个回答:灵魂的愿望是灵魂的缺失,即它所缺乏的东西。这个回答指出,劣势是其本质的一部分,并不仅仅是精神对完美的幻想的结果。其愿望的基础是“劣等者”,即最深层的心理形象,这些来自下界的声音通过破坏、贬低和压制那些忽视劣势的具体化,使所有积极的确定性无效。灵魂的愿望与其共生,就像阿里斯托芬《会饮篇》中的两性人愿望一样,像哈迪斯中灵魂的愿望,以及我们在对话中听到的声音的愿望。
这段文字探讨了灵魂的多种愿望及其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强调了灵魂在心理治疗和个人成长中的核心地位。它指出,真正的心理学不仅应关注治疗,还应帮助个体理解和表达自己内在的灵魂需求。同时,它也指出了不同心理学流派对灵魂需求的不同理解,以及阿德勒关于灵魂缺失的观点。
灵魂的这种渴望是否反映了爱欲(Eros)的本质,而爱欲的母亲是贫困、匮乏和需求的化身潘妮娅(Penia)?每次我们陷入爱河时,不论是治疗中的移情作用,还是在创作一件富有想象力的作品如诗歌或小说时产生的爱意,这种渴望不都存在吗?即使我们富有创造力和机智(爱欲的父亲波罗斯Poros代表聪明的资源),[25] 我们仍然感到无助。爱欲本身使我们感到自卑,那种惊愕的感觉是我们不够好,没有能力,甚至我们的灵魂也感到缺乏,因此一直处于渴望之中。需要是灵魂爱欲困境的母亲;灵魂的渴望与其爱欲密不可分,这似乎是它最想要的东西,同时也是这种渴望的起源。
如果灵魂的渴望是先验的,那么失落就是灵魂的一种永久可能性。我们可能在最强烈地感受到失落时,才最接近灵魂或处于灵魂之中(esse in anima)。于是,渴望感属于灵魂的存在论以及我们所说的“心理状态”。没有任何心理行为能完全满足,没有任何解释能像钥匙开锁那样准确无误,任何灵魂间的关系也无法弥补反映心灵本质的缺失与失败。不完美是其本质,我们只有在渴望中才能完整。总会有错误发生,而这正是赋予心理治疗勇气的价值所在。心理治疗若要保持其特性,只能接受自身的自卑。
然而,就像对话中的患者一样,心理治疗也有困难听到自身低等部分的声音。它也试图远离自己的阴影、疾病和祖先。这种远离自卑的行为构成了“心理治疗的自卑情结”,它出现在当下的实践中,并在其历史记忆中显现出来。这些实践和记忆并非建立在积极的知识上,而是回应了那些处于渴望中的灵魂;甚至这种心理治疗的回应也是多面且自相矛盾的,正如其创始人一样。这段历史的一部分是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这位“次要”的先辈之一。我们在这一章中恢复阿德勒的目的,是为了将他及其对心理治疗自卑贡献重新带回给我们。
因为整个治疗作品及其在同情感之爱中追求完美的愿景,永远无法离开那微小的起点,鞋里的小石子,或是那小小的湿斑,这些都会将我们带回到因有机生命体的实体化而带来的自卑感。因此,即使我们对“灵魂想要什么?”的回答也不能让我们完全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并不会因此万事如意;一切并不会都好。然而,我们正试图通过这个问题与灵魂保持联系。对于心理治疗来说,记住的不是它想要什么,而是它确实在渴望,而灵魂永恒的渴望正是心理治疗永恒的问题。
这段文字探讨了灵魂的渴望与其内在自卑感之间的深刻联系,强调了心理治疗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所面临的挑战和复杂性。它指出,真正的心理治疗不仅仅是提供解决方案,而是持续关注并理解灵魂的永恒渴望。
他的问题试图区分心理上的阴阳人;详见下文“神经质思维与阴阳人”。 对于有占星倾向的人来说,这三位伟人分别出生在固定星座(弗洛伊德:5月6日金牛座;阿德勒:2月7日水瓶座;荣格:7月28日狮子座),他们之间的共识比他们的不容忍和坚持己见更令人惊讶。 R. J. Huber 和 R. Steir 最近做了一项比较研究,题为《社会兴趣与个性化:荣格与阿德勒的比较》,发表于《Character Potential: A Record of Research》第7卷(1976年),第174-180页。本世纪中叶的标准比较作品包括“深度心理学的比较学派”,其中两部由荣格介绍:G. 阿德勒的《灵魂的发现》(1934年)和 W. M. Kranefeldt 的《心灵的秘密途径》(1930-1934年)。 J. T. Rowling 在《皇家医学学会会刊》第54卷(1961年)第410页上发表了关于“木乃伊的病理变化”的文章。Erik Hornung 告诉我,器官与神祇之间的关联并不严格;我们不能用我们一神论心态下的系统性认同来解读埃及多神论幻想的自由。 关于荣格思想中心理意象与身体器官的关系,请参阅荣格,《昆达利尼瑜伽的心理评论》,发表于《Spring: An Annual of Archetypal Psychology and Jungian Thought》(1976年和1977年);G. R. Heyer,《心灵的有机体:分析心理治疗导论》,E. 和 C. Paul 译(伦敦: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1933年);S. R. Bach,《重病患者的自发绘画:对心身医学的贡献》,Documenta Geigy, Acta Psychosomatica(巴塞尔:J. R. Geigy AG, 1969年)。 心理学家从赫拉克利特到柯勒律治再到荣格,以及哲学家如黑格尔和马克思所提出的“现实的辩证性质”,还有“辩证方法”(例如尼采),可以从阿德勒的角度被严厉批评为神经质的思维方式,除非这些方式被视为实用工具或假设行动,其背后是对多样性的掌握。进一步参阅:R. H. Dolliver,《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与辩证法》,《行为科学史杂志》第10卷(1974年),第16-20页;H. L. Ansbacher,《男性抗议:一个文化心理学术语》,即将出版的作品的手稿(作者提供,1977年)。
翻译如下: “生活与神经症中的心理阴阳人”,发表于《医学进展》第28卷(1910年),第486-493页,最近由 Ansbacher 在上述文献中讨论。另见:“心理阴阳人与男性抗议”(IP,16–22)。 从深度病理学的角度对我的主题进行最佳研究的是 Rafael López-Pedraza 的著作《赫尔墨斯和他的孩子们》(苏黎世:Spring Publications, 1977),尤其是关于赫马佛洛狄托斯的第一章。对于心理学中对立主义的批评,请参阅我写的《梦与地下世界》(纽约:Harper & Row, 1979)。关于共轭意识的两个例子,请参阅我写的“老者与青年”,收录于《少年论文集》(达拉斯:Spring Publications, 1979)。 阿德勒最根本的字面主义是性别对,即男性-女性,“唯一的真正对立面”(NC, 99),其他对立面都可以归结为这一对。关于字面主义和性别思维的关系,请参阅 P. Berry 的《性别的教条》,收录于她的《回声的微妙身体:对原型心理学的贡献》(康涅狄格州普特南:Spring Publications, 2008)。我认为阿德勒的男性-女性对立面代表了另一个基本的隐喻对,即精神/灵魂,这对不能像男性和女性那样以经验性和具体的方式理解。 R. J. Huber,《重新审视社会兴趣:再次审视阿德勒》,《Character Potential: A Record of Research》(1975年),第69页及以下。 注意这里荣格和阿德勒在意义问题上的不同。荣格经常强调意义是人们寻找或在实现自我时整合的东西,而阿德勒则认为意义已经存在,我们生活在意义之中。荣格的意义感是预言性和宗教性的,而阿德勒的意义感是解释性和实用性的。 参阅《珀西瓦尔的叙述:一个患者对其精神病的描述,1830–32》,由 Gregory Bateson 编辑(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1),这是一份19世纪早期被囚禁的“疯人”的证词,他将自己的一段疯狂时期归因于对精神语言的“字面化”。 例如 G. J. Mozdzierz、F. J. Macchitelli 和 J. Lisiecki,《心理治疗中的悖论:阿德勒视角》,发表于《个体心理学杂志》第32卷(1976年),第169-184页。
“生活与神经症中的心理阴阳人”,发表于《医学进展》第28卷(1910年),第486-493页,最近由 Ansbacher 在上述文献中讨论。另见:“心理阴阳人与男性抗议”(IP,16–22)。 从深度病理学的角度对我的主题进行最佳研究的是 Rafael López-Pedraza 的著作《赫尔墨斯和他的孩子们》(苏黎世:Spring Publications, 1977),尤其是关于赫马佛洛狄托斯的第一章。对于心理学中对立主义的批评,请参阅我写的《梦与地下世界》(纽约:Harper & Row, 1979)。关于共轭意识的两个例子,请参阅我写的“老者与青年”,收录于《少年论文集》(达拉斯:Spring Publications, 1979)。 阿德勒最根本的字面主义是性别对,即男性-女性,“唯一的真正对立面”(NC, 99),其他对立面都可以归结为这一对。关于字面主义和性别思维的关系,请参阅 P. Berry 的《性别的教条》,收录于她的《回声的微妙身体:对原型心理学的贡献》(康涅狄格州普特南:Spring Publications, 2008)。我认为阿德勒的男性-女性对立面代表了另一个基本的隐喻对,即精神/灵魂,这对不能像男性和女性那样以经验性和具体的方式理解。 R. J. Huber,《重新审视社会兴趣:再次审视阿德勒》,《Character Potential: A Record of Research》(1975年),第69页及以下。 注意这里荣格和阿德勒在意义问题上的不同。荣格经常强调意义是人们寻找或在实现自我时整合的东西,而阿德勒则认为意义已经存在,我们生活在意义之中。荣格的意义感是预言性和宗教性的,而阿德勒的意义感是解释性和实用性的。 参阅《珀西瓦尔的叙述:一个患者对其精神病的描述,1830–32》,由 Gregory Bateson 编辑(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1),这是一份19世纪早期被囚禁的“疯人”的证词,他将自己的一段疯狂时期归因于对精神语言的“字面化”。 例如 G. J. Mozdzierz、F. J. Macchitelli 和 J. Lisiecki,《心理治疗中的悖论:阿德勒视角》,发表于《个体心理学杂志》第32卷(1976年),第169-184页。 这段文字涉及多个心理学和哲学概念,包括阿德勒和荣格的思想差异、性别对立面的理解、以及对深层病理学的研究。它还探讨了字面主义在心理学中的应用,并引用了历史文献来支持这些观点。
“联结词(Junktim):将现实中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关联的两个思想和情感复合体有意连接起来,以增强情感。隐喻也有类似的起源”(IP, 39n;参见 A&A, 283)。阿德勒的“联结词”与荣格的“情结”相似。这两个术语在意义构建上也类似于希腊语中的“症状”(symptoma),即偶然的同时发生。荣格从客观角度看待情结,认为它是心灵的基本数据,呈现其情感的实证内容,因此可以通过联想实验来证明情结的存在。然而,阿德勒则将“联结词”视为一种有意的发明,用以强化情感,类似于梦和诗歌中的夸张和浓缩修辞手法(L, 79;U, 116;IP, 219n;A&A, 360–61)。如果我们现在将“情结”和“联结词”结合起来理解,我们可以把情结既看作是心理能量核心的经验事实,也看作是我们心理神话的隐喻。将情结重新概念化为语言形象(隐喻)会将心灵的基础从科学描述转向诗意描述。保罗·库格勒通过重新审视荣格关于词语联想的著作,开始这种对荣格经验主义科学基础的重大转变,强调其语言和意象意义。保罗·库格勒,《话语的炼金术:意象、声音与心灵》(Einsiedeln:Daimon Verlag, 2002)。有趣的是,在荣格82岁时(给汉哈特的信,收录于 C. G. 荣格《书信集》,3卷,由 A. Jaffé 和 G. 阿德勒编辑(Olten:Walter Verlag, 1972], 3: 79),他仍然记得阿德勒的“联结词”,尽管荣格将其视为同步性概念的前身(因果无关事件的同时发生,symptoma)。弗洛伊德在他的晚期论文《非专业分析》中提到过“治疗与研究之间的联结词”。这个术语在德语中通常出现在法律-政治语境中。 M. 沃特斯,《醒来的梦》(康涅狄格州普特南:Spring Publications, 1998)。 A. 古根比尔-克雷格,《治愈职业中的权力》(康涅狄格州普特南:Spring Publications, 2009)。 “得墨忒耳/珀尔塞福涅与神经症”,发表于《Spring: An Annual of Archetypal Psychology and Jungian Thought》(1975年);《母亲怎么了?》《论简化》和《激进的女人》,收录于贝瑞的《回声的微妙身体》。 “原型心理学与教育”,论文提交至1977年达拉斯大学第一届国际原型心理学研讨会。 参阅《埃拉诺斯年鉴》第44卷(1975年)、第46卷(1977年)和第50卷(1981年);还有《Spring: An Annual of Archetypal Psychology and Jungian Thought》(1973年、1976年和1980年);《神祇与游戏:迈向一种游戏神学》(纽约和克利夫兰:World Publishing Co., 1970)。 这段文字探讨了阿德勒的“联结词”和荣格的“情结”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并讨论了它们在心理学和文学中的应用。此外,它还提到了一些相关的文献和研究,涉及原型心理学、治愈职业中的权力问题以及神话和神经症的关系。
参见 CW 7: 339,以及我在文章《阿尼玛(II)》中对误解荣格“整合阿尼玛”概念的讨论,发表于《Spring: An Annual of Archetypal Psychology and Jungian Thought》(1974年),第119-124页。 参见 U, 13 和 27;L, 9 关于错误的重要性,以及通过错误是认识灵魂和找到意义的唯一途径。 荣格,《书信集》,2: 188 和 225。关于阿尼玛与心灵的关系以及内外问题,请参阅我的文章《阿尼玛》,发表于《Spring: An Annual of Archetypal Psychology and Jungian Thought》(1973年),第119-130页。 “社会情感或许是阿德勒心理学中最难正确理解的概念。如果将其视为哲学或道德,则会错过其本质。‘如果有人跟我谈论道德,’阿德勒曾说过,‘我会看看他的手是否在偷我的口袋。’心理学不是为了说教……它的目标是治疗。社会情感……是人们必须具备的生活基本假设,以保持心理健康。”(W, 208-209) 对于厄洛斯的父亲和母亲的隐喻(源自我在本章题词中引用的柏拉图《会饮篇》的描述)进行详细的心理学解释,请参阅 Sears Jayne 翻译的马西利奥·费奇诺的《柏拉图〈会饮篇〉中的爱的注释》(康涅狄格州普特南:Spring Publications, 1985)。 缩写说明: A&A = Heinz L. 和 Rowena R. Ansbacher,《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从其著作中选编的系统呈现》(纽约:Basic Books, 1956)。 CP =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集》。由 Joan Riviere 监督翻译,共5卷(伦敦:Hogarth Press 和精神分析研究所,1924-1950)。 CW = C. G. 荣格的《文集》,由 R. F. C. Hull 翻译,共20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3-1979),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按段落编号引用。 ELL = 亨利·F. 埃伦伯格,《无意识的发现》(伦敦:Allen Lane, 1970)。 FJL = 弗洛伊德/荣格书信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 C. G. 荣格之间的通信,由 W. McGuire 编辑(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4)。 IP =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个体心理学的实践与理论》,由 P. Radin 翻译(伦敦:Routledge & Kegan Paul, 1929)。 L =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伦敦:G. Allen & Unwin, 1932)。 LA-S = 路易丝·安德烈亚斯-萨洛美日记,由 S.A. Leavy 翻译(伦敦:Hogarth Press 和精神分析研究所,1965)。 这段文字涉及多个心理学概念及其文献出处,特别是荣格和阿德勒的思想,包括他们对“阿尼玛”、社会情感的理解,以及相关的经典文献和翻译作品。
MDR = C. G. 荣格,《回忆、梦、反思》,由 Aniela Jaffé 记录和编辑,由 R. 和 C. Winston 翻译(纽约:Vintage Books, 1989)。 NC =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神经症的构成:比较个体心理学与心理治疗概要》,由 B. Glueck 和 J. E. Lind 翻译(纽约:Moffat, Yard and Company, 1917)。 OC67 = Walter E. O’Connell,《个体心理学》,《新天主教百科全书》,第7卷(华盛顿特区:美国天主教大学出版社,1967)。 OC72 = Walter E. O’Connell,《弗兰克尔、阿德勒与灵性》,发表于《宗教与健康杂志》11/2期(1972年)。 OC76 = Walter E. O’Connell,《“阿德勒的朋友”现象》,发表于《个体心理学杂志》32期(1976年)。 OC77 = Walter E. O’Connell,《幽默感:个人和理论的实际体现者》,收录于 A. Chapman 和 H. Foot 编辑的《It’s a Funny Thing, Humour》(牛津:Pergamon, 1977)。 OI =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器官低劣及其心理补偿的研究:对临床医学的贡献》,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Monograph Series No. 24,由 S. E. Jelliffe 翻译(纽约: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Publishing Company, 1917)。 SE =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全集》,由 J. Strachey 编辑,共24卷(伦敦:Hogarth Press 和精神分析研究所,1953-1974)。 SP = 《Spring:原型心理学与荣格思想年刊》(1970-1988年)。 U =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理解人性》,由 W.B. Wolfe 翻译(伦敦:G. Allen & Unwin, 1928)。 UE = James Hillman 的著作统一版,共11卷(康涅狄格州普特南:Spring Publications, 2004-)。 V = 汉斯·瓦伊辛格,《“仿佛”哲学:人类的理论、实践和宗教虚构系统》,由 C. K. Ogden 翻译(伦敦:Routledge & Kegan Paul, 1935)。 W = Lewis Way,《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对其心理学的介绍》(哈蒙兹沃思:Penguin Books, 1956)。 这段文字列出了多个心理学经典文献及其出版信息,涵盖了荣格、阿德勒、弗洛伊德等重要心理学家的著作,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和翻译作品。这些文献为理解和发展心理学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