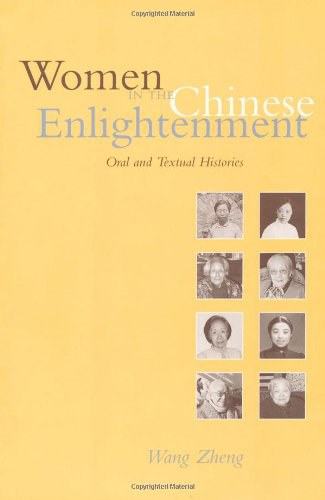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更新图书信息或封面
作者: Wang Zheng / 王政
出版社: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副标题: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出版年: 1999-7-5
页数: 417
定价: USD 33.95
装帧: Paperback
ISBN: 9780520218741
豆瓣评分
9.6
224人评价
5星82.1%
4星14.7%
3星3.1%
2星0.0%
1星0.0%
评价:
写笔记 写书评 加入购书单
添加到书单分享到
推荐
内容简介 · · · · · · Centering on five life stories by Chinese women activists born just after the turn of this century, this first history of Chinese May Fourth feminism disrupt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master narrative of Chinese women's liberation, reconfigures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and addresses the question of how feminism engendered social change cross-culturally.
In this multilayered book, the first-person narratives are complemented by a history of the discursive process and the author's sophisticated intertextual readings. Together, the parts form a fascinating historical portrait of how educated Chinese men and women actively deployed and appropriated ideologies from the West in their pursuit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self-emancipation. As Wang demonstrates, feminism was embraced by men as instrumental to China's modernity and by women as pointing to a new way of life.
投诉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的创作者 · · · · · · 王政 王政 作者
作者简介 · · · · · · Wang Zheng is an Affiliated Scholar at 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Women and Gender at Stanford University. Wang's work in English includes the coediting of From the Soil: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by Fei Xiaotong (California, 1992).
原文摘录 · · · · · · ( 全部 ) His attack on the gender system in China allowed him to express his alienation from the ancient culture. His embrace of Nora revealed not only his frustration with the Chinese hierarchical and patriarchal family, but also-at a more profound level-his resentment of the burdens and constraints he experienced in a social structure based on networks of hierarchical and differential human relationships and their associated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namely, Confucian ethics). He himself dreamed of being an independent person with individual freedom. Moreover; his fundamental crisis was generated by a painful realization of his peripheral and subaltern position in China's semicolonization by the West. The comforting, centuries-old sense of superiority enjoyed by Chinese male literati was ... (查看原文) 达西 2赞 2016-01-30 01:35:35 —— 引自第59页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世界局势向新文化主义者传递了一个信息:人文主义,或者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即“人的发现”,应当包括妇女。欧洲是先“人的发现”,过了两个世纪才有“女性的发现”。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是两个发现并提,更难。 ⭐⭐ 真正的新女性——超越那些在男性文学表述中作为一种修辞而出现的新女性——的主体建构。*** 男性创作的非文学文本仅仅是一种不同的表述方式而已。对于儒家文化中妇女受压迫的批判以及对于妇女解放的鼓吹,都突出了“近代知识分子拼命地想要”借性别问题来“表述自己”这一点。他攻击中国的性别体系,表达了对旧文化的疏离。他拥护娜拉,不仅显示出他对中国的等级制和父权制家庭感到失落,而且在更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他对于所在的社会体系中体验到的负担与束缚感到愤恨,这种社会体系是基于有等级、有区别的人际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的责任与义务(即儒家道德)而成的网络。他梦想自己成为一个拥有个体自由的独立的人。 此外,他根本的危机还是源于他痛苦地意识到在被西方半殖民化的中国,他处于边缘和从属的地位。中国男性文人几个世纪以来所享有的令人鼓舞的优越感被强大而“优越的”西方大大地破坏了。近代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地界定了妇女这个“受压迫的”、“低下的”社会群体,以此重新肯定了他们自身的优越性。简而言之,他们大声疾呼妇女解放也就是在表述或者说表达他们自身有意无意的渴望、冲突与危机。 (查看原文)
芝士草莓蛋糕 2022-09-05 22:25:01 海南 希望更多的她们被大众看到,当我们谈论五四时候,脑海里反应的不再是是所谓的知识“精英”男性,也不要相信他们构筑的虚假女性解放。许多优秀的革命女前辈们给我们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阅读时有感慨,男性在中西冲击的动荡年代借由解放受奴役的女性,自己却做着压迫者的姿态(比如鲁迅不让自己女学生许广平(他的事实婚姻妻子)外出工作,说出:“你在家里不要出去,帮帮我,让我写文章。”
5 有用咩咩蚌 2021-01-27 20:47:07 心情很复杂。作者要通过这些口述记录表达新文化时期的话语和主张,即一种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对于我国妇女解放的影响,它夹杂着对儒教父权体制的反抗、对人权的要求。作者同时又将这种倾向的女权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去审视女权主义不同功能下的发展、以及在不同指导思想下的运作。刘王立明、陆礼华、朱素萼、王伊蔚、陈泳声、黄定慧六位女性不同的政治身份下形成的不同女权实践让我们看到女性解放在不同环境下的走向。话语和符号是一种生产出来的东西,它可化作一种实践起作用。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在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协同变奏,历史就是一场拉锯战。看了这段历史,更觉得今天我国的女权问题实在太复杂了,政治利益、资本全球化运作、东西古今思潮、社会分层、城乡二元下的差异全部交织,要看懂这个现实图景需要厚重的积淀。 (收起)
1 有用isolde 2012-10-11 19:39:34 http://iask.sina.com.cn/u/1407955112/ish?folderid=850918
1 有用mundane 2024-05-10 12:56:34 广西 “除个别外,我的访谈对象都是二十世纪初接受了大学或中学教育,而且在二 三十年代开始职业生涯的妇女。除教育和职业外,本文中的妇女还有一个共同点: 她们富于创造力的、活跃的生活在1949年后嘎然而止。”
35 有用会打字的跳舞机 2015-10-08 14:41:43 主持人时间没控制好,一不留神大家就分享了近4小时,基本在闲聊这些妇女怎么惨,没有围绕问题展开讨论。这些妇女49年前都好厉害啊!之后事业基本都陷入停滞。最惨是黄定慧,一切听从组织分配,从来没有为自己做选择。最酷是陈泳声,哪个党派也不靠,不舒服就走,一生换了无数职业,还曾中了头等彩票去德国看世界杯,我们都对这个细节耿耿于怀!
更多短评 112 条
我要写书评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的书评 · · · · · · ( 全部 5 条 ) 热门 最新 好友 只看本版本的评论 小当家 2018-03-24 19:05:35 五四女性:被遮掩与忽视的历史 《五四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是王政在1999年出版的英文著作,英文名是《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这本书在国内一直没有正式出版,最后是由几位青年学者共同翻译完成,王政公开了电子版。
在国内,研究妇女运动或者女权史的,往往止于1949年。比较典型的像李木兰写的《性别、政治与民主:近代中国的妇女参政》,也只写到1948年,因为在1949年新中国宣布成立时,也同时在宪法中写入了男女平等的条例。因此,民国时期轰轰烈烈的妇女参政运动到了1949年就“自然而然”地结束。
长期的官方叙事都将妇女解放与共产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在共产党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时,必然也赋予了妇女独立自主的意识和权利。因此,由共产主义带领大家走向平等似乎是是一件不证自明的事情。
然而,正如李木兰想要证明,中国妇女的参政权并不是因为共和国的建立就被赋予,而是建立在无数妇女的血泪之上,王政也通过对主流叙事之外的女性采访来还原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妇女运动也不是只由共产党员来完成,无数无党派人士、国民党妇女,都曾经参与过这一运动中来,她们虽然不被主流记载叙述,但她们做的事情却丝毫不少。
王政在她的另一本书《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中提到,女权主义的学术改造有一个很常用的方式,就是“添加妇女”。比如在历史研究中挖掘起过重大作用的妇女,在文学艺术领域内挖掘女作家、女艺术家。当问出“妇女在哪儿”时,就是在挖掘人类另一半的历史。
王政的发现是,官方叙述中1949年以前的妇女只有三种典型:“参加了共产主义革命从而成为英雄的妇女;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压迫从而成为受害者,被共产党解放的妇女;依赖丈夫生存的资产阶级太太,她们是颓废、寄生、剥削的阶级,被革命所消灭。”所以她问的是,“那些没有加入共产党的城市女权主义者后来怎样了,那些加入共产党的命运又如何?”
五四时期的女权运动
这样问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男女平等”的口号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发明。对于被侵略的民族国家来说,解放妇女跟振兴民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精英男性常常是这一运动的主导者和先行者。
尽管“女权”一词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进入中国,但“妇女问题”一词却是在五四时期得到了最为广泛的传播和普及。
1919前后正在进行的新文化运动使很多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妇女问题,对儒家的批判也带来了对个人主义的推崇。晚清改革家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改变妇女缠足习俗、女子教育制度化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因为他们认为是中国妇女的落后阻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
同样是民族进步的逻辑,新文化主义者们并不满足于这些问题,在他们看来,如果妇女的从属地位和导致这种地位的文化不能发生改变,那么中国就不能说获得了一种“新文化”。因此,像陈独秀这样的新文化主义者迫切地号召大家关注妇女问题。
1918年,《玩偶之家》被译成中文,在出走之前说出“我是一个人,和你一样。不管怎样,我要尽力成为一个人。”的娜拉成了中国受过教育妇女心中的西方行为榜样。同年,周作人发表了他翻译的《贞操论》,对主流性道德公然宣战,鲁迅也在《我之节烈观》中猛烈抨击了贞操道德。
如果说20世纪初的中国文人发现了什么新鲜又有强烈吸引的东西,那便是人文主义,是“人”的发现,当然也包括妇女。这期间非常多的妇女开始走上街头,开展运动。她们可能以形形色色的身份在战斗着,但在后来的叙事中,被颂扬的就只剩下了共产党员。
这并不公平,因为民间的女权运动在1919-1927这段时间一直保持着活力,既不分党派,也不论身份。变化发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中共变成了非法的逃亡组织,共产党无法继续在国统区公开动员妇女,所以在为其自身生存艰苦奋斗的同时,女权主义议题就不再那么重要,但妇女本身成了共产主义革命要争取的群体。
有没有“不狭隘”的女权主义
如何争取妇女,官方的叙事中很少使用“女权运动”这个词,而是更多地使用“妇女运动”,妇女运动似乎和其他的阶级斗争、工农运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在这个过程中,妇女问题不被看做是最要紧的问题,因为整个反帝反封建的任务都还没有完成,这个时候就算为妇女争权利,也是在为那些资本主义少奶奶争取权利,所以,鼓励更多的妇女投入到共产主义革命中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原本为了争取妇女平权的运动则被称为“狭隘的女权主义运动”、“资本主义女权运动”。
这是跟新文化运动有趣的悖论。在新文化运动中,一个妇女独立、解放、获得平等的权利就是为了民族振兴,而在共产主义革命中,一个妇女应当先想着民族振兴,不要光想着妇女解放。就连中共女党员蔡畅都曾说,我们不应该过于关注妇女解放,而是应该关注“拯救孩子”、“家庭兴盛”、“健康长寿”这些问题。
今天的人同样用这套逻辑来批评女权主义或其他主义:
你们看到某某事件为什么不发声,你们只顾自己的利益。 老龄化这么严重,你们还在鼓吹妇女不生育。 有人连饭都吃不饱,你们还在鼓吹动物权。
事实上,期待一种完美的“主义”是不可能的,一种思潮只能应对一类问题,个人的利益只能个人去争取,斗争也只能由近到远,有小到大。五四女性的故事告诉我们,根植在人们思维中的父权制,并不会通过工农阶级的斗争被终结。女权主义者也并没有义务去解决全世界的问题,像早年的“妇女参政论”者那样执着于一个具体的目标才更有可能成功。
有人的愿景是解放世界,有人的愿景只是妇女平权,没有谁该被指责,当革命战士要求妇女们把民族放在第一位时,像刘王立明这样“狭隘的女权主义者”会说:即使在民族危亡之际,妇女的权利和所遭受的痛苦也不应该被遗忘。
找回中国妇女的能动性
在1949年之后,“男女平等”作为一项已经实现的目标被写进国家法律中,妇联成了妇女利益与声音的唯一合法的代表,这一将妇女问题体制化的做法,使得民间的女权运动更难有施展的空间。
现在要问,在中国共产党之外,中国妇女做过什么。不能因为历史没有记载,我们就当历史没有发生过。
在王政的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以完全不同的姿态展开运动的妇女们。她们有些人可能秉持着完全不参与政治派系的理念,有些人则可能是忠诚的党员。《五四女性》记载了5个这样的故事,这些人的故事是让人感动又悲伤的。
坚持十几年创办体育学校,发展女子体育的陆礼华,曾经培养了无数中国近现代的体育强队和奥运选手,晚年她在毛衫厂做工人,人们会悄悄嘀咕说,“看,那就是陆礼华,两江的校长。现在她就和毛线打交道。”她想的却是,“那有什么错?我凭自己的劳动过日子。我是努力跟上时代的人。”
作为律师的朱素萼始终用自己的专业身份替妇女们辩护,对她来说,筹钱,慈善和志愿活动都属于女权运动。她们还出版了《中国妇女》,自己编辑采写跟女权有关的文章。尽管她是一个国民党员,但在妇女问题上却并没有吝啬于为共产党员提供帮助。但还是免不了在文革中被“关照”,直到1979年平反。
曾经的《女声》主编王伊蔚,晚年只能居住在7平米的房间里,她花费6个月的工资为自己刻一块墓碑,为的是记住自己曾经为妇女运动做过的事情,和那些共同战斗过的姐妹。而这些成就,并不会被官方的史料所记载。
曾经的大学老师,出国留学过的陈泳声,老年时没有钱请保姆,还会想着自己办一个英语补习班赚钱,而那时候她已经93岁了,甚至在95岁时政府要出钱给她请保姆时也被拒绝了,这个不愿意被称为“某某夫人”的女性依然保留着五四时期的词汇——“独立人格”。
而像黄定慧,这个职业被定义为“革命家”,援救过无数共产主义战士,在革命中心武汉最为出名的妇女,在1949年之后监狱里就呆了17年。当她说“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出狱时已经快70岁了”,这句话已经有了千斤的重量。她的两任前夫都被追认为英雄,而她的贡献甚至都还没有被认可。
我们不能简单地下定义说,中国妇女运动是一场英明领导下的解放。中国妇女并不只是被领导这一种角色,在时局面前,她们曾经尽过自己最大努力去做成事情。认识中国妇女本身的能动性,才是认识到那一代女性所追求的品质——独立、自由。 投诉 有用 166 没用 2有关键情节透露 166 2 9回应收起 momo 2025-02-23 18:06:36 我们本可以更自由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在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叙事之外,五四新文化女权主义所培养的一代女权主义者,包括无党派者、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如何作为能动的新女性主体,而非被动的“大众”或被共产党话语所规范的“女英雄”,推动了近代女权运动的发展和民族解放。在两党漫长的争斗中,在共产党建立和巩固政权、建构权威历史记忆的过程中,她们又是如何被放逐、被隐形,被迫磋磨了人生。
我们丧失的是“妇女自由联合”的五四传统。民族主义使女权主义话语获得了合法性,使得公共领域向女性敞开,但是,反过来讲,也唯有从属于民族主义的女权主义才是规范的和标准的。这就像是女性终于被允许进入一间此前都拒绝她进入的房间,但是却只被告知只能坐那几个角落里的座位,不可逾越半分。
一场为城市妇女开辟了社会空间的自发女权运动变成了政党控制的妇女解放运动。虽然后者相比当时的女权运动,更广泛地改变了中国妇女的生活,但最终却在党国一体的情况下关闭了妇女自发活动的社会空间。 中国近代的男性知识分子,之所以会发表支持女权的言论,一是因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女权被认定为是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一环;第二,通过把女性放置在愚昧、不开化、急需自强的待解放者的位置上,相对应地,男知识分子就成为了启蒙者和解放者,他们从“东亚病夫”的现实那里遭遇的受挫感得到了弥补,得以重新赋予自我以精英的身份优越和话语权力;第三,绝大多数男知识分子,张口闭口只谈女性自强,而绝口不谈男人所拥有的特权。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女性不自由只是因为女性自己不努力,男人不是女性的敌人,是女人要为自己的被压迫地位负全责。此外,他们也会选取对自己有利的话语进行大肆宣传,其实本质上是男权的自我更新。例如,大力宣扬“恋爱婚姻自由”,反对鼓励女子保持独身、致力于革命事业的“妇女主义”,一方面既能赋予自己抛弃包办妻子的行为以合法性,另一方面又能蒙骗本来立志于独身的新女性掉入男缘陷阱。第四,实际行动和言论的落差,让他们最大程度上使自己免受于女性地位提升的威胁。虽然教育平等和职业平等有所推进,公共领域向女性开放了大门,但当她们跨过门槛后,却发现自己依然要面临重重阻碍。不仅是就业选择十分有限,女性还要面临被排挤、被边缘化、被造黄谣的恶意,她们的贡献也被漠视,甚至被掠夺。例如陈泳声被自己创办的残疾儿童学校解雇,成就斐然的地下党员黄定慧,她的两任前夫都被表彰为共产党英雄,她却仅仅因为第三任丈夫去了台湾就遭受了反复的清算和侮辱。最让我愤怒的是,黄定慧自始至终都只是遵从命令,包括她的第三次昏因,也是为了开展地下工作的便利才有的。但解放后,她却因此遭到怀疑,承受了十七年的牢狱之灾。
这本书还解答了我的另一个疑惑:为什么那么多进步女性,最初都会有一个“开明的父亲”鼓励她们放足,允许她们接受教育?我一直不信任这样的叙事,首先这真的是出于“开明”吗?其次母亲去哪里了?为什么不是母亲鼓励女儿放足,不是母亲鼓励女儿去读书,不是母亲给予女儿更多精神和物质支持?这本身就已经暗示了女男的不平等。
王政回答了这个问题:在部分地区,女子教育是当地士绅家庭权力地位的象征,这种现象在封建社会里也自有脉络。此外,据我了解,过去让女儿接受教育,也不过是为了让她能够更好地相夫教子,想要在别的领域施展才华,都是不被包容的,闺阁才女自焚诗稿是非常常见的事。
让女儿去读书,并不能证明一个父权大家长有多么高的女权意识。相反,一个看似开明的父亲,更有可能坑害女儿一生。黄定慧的父亲在这五位女性的父亲里似乎是最开明的一个,但黄定慧本人却是牵扯男缘最深的那一位,也是我最不忍卒读的一位。一个伪装良好的父亲,会是黄定慧选择加入专制的CPC、没有把独身主义坚持到底、至死也没有彻底叛逃出党的英雄模板的根源之一吗?她为什么会是五位女性里最悲惨的一个?在我的生活里我也经常会觉得,无法和一个与父亲关系和睦的女人谈论女权主义。
最后,我真的很喜欢教育家陈泳声女士,坚强、勇敢、洒脱,一辈子都保持独身,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党派,这份工作做不顺心了就走人,“享受自由的迁徙”,老年也不愿意接受政府的无偿补助,而是坚持发挥自己的英语特长来找一份谋生的工作。虽然还是有男性朋友,但相对来说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
我年轻时,遇到了很多对我感兴趣的男人。但我决定不结婚,我对男人的兴趣不比对女人的多。五四运动初期,一个男人给我写信,说他想和我交朋友。我说:“你究竟在干什么,闹革命还是交朋友?” 全书好几次提到,很多革命女性和职业女性最初都发誓不结昏,最后还是掉进了陷阱。看到一个个女性在艰难的革命和抗战岁月还要生好几个孩子,生下来之后又要被迫母子分离,我真的如鲠在喉。我最近总是想,女人在男权社会里,处处被男缘拖累,都能取得那么多卓越的成就,如果在女权社会,我们又会有怎样的丰功伟绩呢?我们本可以更自由。
© 本文版权归作者 momo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投诉 有用 5 没用 0 5 0回应收起 逖枣 2022-12-30 15:50:56 《五四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 读的中文版,感谢作者王政、赵婧译、候艳兴校。
偶然被(茶余饭后小组)推荐看到这本书,它吸引我的点是从近代五四时期讲述独立女性的故事,差不多100年前。想知道当时女性的困境和思想发展。
个人认为中国女性不同于国外女性在于国家历史悠久,掺杂的思想太多发展也快。女性问题不单是父权或男权,还有刻在基因骨子里的传统思想和我们社会法律制度的问题。
书中描述了近代的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新思潮如何影响当时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拥有不可被剥夺权利纯粹且抽象的人这一人道主义者概念”、“自由、平等、独立”,向西方学习如何变强是当时知识分子所关注的,接受教育改变旧观念也是迫切需要的。当时的知识男性愿意支持女性主义兴办女校,是认为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强国保种”。知识女性则是在民族主义+独立自主思想下不断奋斗,她们在历史中也充分发挥了能动性,在公共领域中有着职业成就,办体校、当教师、律师、主编、革命者。她们不是被动的追随者,而是参与历史变革中的建构者与能动者。
我时刻提醒自己,关注女性题材是从我们女生角度来看世界,以此为参考,它只是作为思想启蒙和独立宣言。不是评判一切事务的标准,别让自己走入极端与仇视,要保持独立思考。
贴一些我喜欢的语句:
“女子本身,应知道自己是个人。所以要把能力充分发展,做凡是“人”当做的事,又知道“人”但当服从真理,那荒谬的“名分”“伪道德”便该唾弃他,破坏他,我们“人”个个是进化历程中的一个队员,个个要做到独立健全的地步,个个应享有光明、高洁、自由的幸福”。
“今日之义务轻一分,日后之权利减十分”
© 本文版权归作者 逖枣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投诉 有用 4 没用 0有关键情节透露 4 3回应收起 離微 2013-11-25 01:57:24 women's self liberation Wang’s monograph was a reflection of women’s movement during the May Fourth era (which, according to her definition, spanned from the Republican Revolution to the end of 1920s). A scholar on Chinese women’s history, Wang questioned, examined, and eventually disavow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elf-proclaimed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women-- that the benevolent party bestowed the liberation and emancipation to Chinese women who were denied freedom in the feudal society before 1949. Wang conducted extensive interviews with May Fourth women, those highly educated female activists who were born in or shortly after 1900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feminist movements. Among them, Lu Lihua (1900-1997. 陸禮華) was the founder and principal of Liangjiang Women’s Physical Education Normal School (兩江女子體育專科學校). Zhu Su’e (朱素萼, 1901- ?) was an attorney who opened her own law office in 1930 and defended women’s rights by accepting divorce lawsuits free of charge. Chen Yongsheng (陳泳聲, 1900-1997) was a professor who received a bachelor’s degree from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later served as the dean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today’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Wang Yiwei (王伊蔚, 1905-1993) held a bachelor’s degree in Journalism from Fudan University and became the founder and editor in chief of the magazine “The Women’s Voice” (《女聲》) as early as 1932. Huang Dinghui (黃定慧, 1907-2011) was a senior communist party member who served as a special agent and once saved the life of Zhou Enlai. These women survived to the 1990s and presented us a different account of Chinese women’s pre-1949 history. A feminist historian, Wang Zheng was especially aware of the patriarchal hegemony on voice. Although male New Culturalists’ writings about feminist movements 女權運動 were abundant, Wang chose the oral narratives of those historical women who personally experienced, participated, and contributed to those movements over the voice of the male literati and their imagined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In the meanwhile, by giving credit to those unsung avant-garde feminist heroines, Wang also successfully deconstructed the CCP’s myth of Chinese women’s liberation. In her point of view, Chinese women had begun the search and fight for emancipation as early as Qiu Jin’s generation and the May Fourth feminist activists furthered the course by and for themselves. However, most of them were silenced after 1949 because the initiative to play a dramatic role was highly limited under the omnipresent state control of the CCP. Wang’s critical position toward the socialist party-state is obvious when she obliquely commented that “the early Chinese women’s movement owes much to the weakness of the republican state. (Wang. 186)”
May Forth elite women who emerged as the main leaders of women’s movementS were mostly educated upper class women. They were exposed to Anglo-American feminism which was generally referred to as liberal feminism, and prioritized women’s education. However, after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a jointed crusade achieved by both the Nationalist Party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liberal feminism gradually declined due to the rise of the increasingly popular Marxist feminism. Marxist feminism rose during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mostly hailed by Communists who believed feminist revolution could not be realized until there was a thorough proletarian revolution. 投诉 有用 2 没用 0有关键情节透露 2 0回应收起 芝士草莓蛋糕 2024-03-19 22:43:49 口述文本和现实记忆:2024年的上海和她们 长居一隅人会变得僵化,读书也一样,很多书几年前读过,几年后又有所不同,这仅仅是我读这本书的一年多之后的感受,这次记忆和书中人有所串联。人的记忆有时候因时间、温度、气味会有不一样的味道,而几年后我重新到达上海,在城区古老的街道中行走,这些文字是凭着感觉写的,难免有些遣词造句的疏忽。
22年时间我们读了很多书,大量的女性题材文本,如果要谈及印象深刻,只有几本,这些书籍都不是权贵的叙述,也不是高深理论,你不需要调动很多脑细胞去加深理解,但是阅读的时间里,你有一种时空的共鸣。
三月中旬的上海,天气晴好,后续有些阴冷加持,我们走在太原路上。家人说想看看这本书里老人们的住过的地方,当然我们无从找寻,这本是极难的事情,我们只是在道路中慢慢行走。太原路上也有一位女士住过,我们很难猜测这边的房子一百年前的主人是谁,之后又是谁,房子里面现在住着什么样的人,说过什么样的话。唯独能感受到是文字与时空交叠的力量,或许有些东西无法用文字表达出来,近代以来的女性形象,是不是读过很多书就能获得?
历史叙述太喜欢从权贵之家说起,平凡人见微知著的历史往往被公众所忽略,何况本书里有许多做大事的女人们,读起来会有一种力量,女人因为壁垒、障碍不能得到成长,所学之才“自愿”奉献给厨房、孩子、丈夫,总有同化者想要继续这样的困境。
愿所有大女人们都能活出自信、勇敢、坚毅、洒脱、耀眼的样子。
ps:感受极多,只能书写至此。
© 本文版权归作者 芝士草莓蛋糕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投诉 有用 0 没用 0有关键情节透露 0回应收起
更多书评 5篇
读书笔记 · · · · · · 我来写笔记 按有用程度 按页码先后 最新笔记 Oloroso 展开 口述的记忆 Oloroso
在读王政老师的书前先读了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的开头。王和陈都承认,五四运动对于中国女性运动的发端有着无可取代的作用。王政因此将五四运动视为中国的“启蒙运动”。王政对于口述史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原有的中国妇女史观点,可读性很强。 王探寻了女性作为主体,在五四时期拥有的能动性(Agency)。王政并没有在书中介绍为何使用“Agency”一词,根据我的理解,可以借助James Wertsh的“mediated action”理论进... 2022-02-03 20:23:17 3人喜欢
达西 展开 第59页 Creating a female discourse 达西 (我反对)
His attack on the gender system in China allowed him to express his alienation from the ancient culture. His embrace of Nora revealed not only his frustration with the Chinese hierarchical and patriarchal family, but also-at a more profound level-his resentment of the burdens and constraints he experienced in a social structure based on networks of hierarchical and differential human relationsh... 2016-01-30 01:35:35 2人喜欢
琴流感 展开 第一章 琴流感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世界局势向新文化主义者传递了一个信息:人文主义,或者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即“人的发现”,应当包括妇女。欧洲是先“人的发现”,过了两个世纪才有“女性的发现”。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是两个发现并提,更难。 ⭐⭐ 真正的新女性——超越那些在男性文学表述中作为一种修辞而出现的新女性——的主体建构。*** 男性创作的非文学文本仅仅是一种不同的表述方式而已。对于儒家文化中妇女受压迫的批判以及... 2023-07-23 08:2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