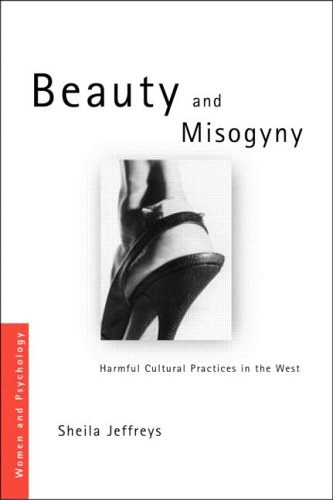Beauty and Misogyny
Beauty and Misogyny Beauty and Misogyny 更新图书信息或封面
作者: Sheila Jeffreys
出版社: Routledge
出版年: 2005-8
页数: 206
定价: $ 175.15
装帧: Hardcover
ISBN: 9780415351836
豆瓣评分
9.2
79人评价
5星79.7%
4星17.7%
3星2.5%
2星0.0%
1星0.0%
评价:
写笔记 写书评 加入购书单
添加到书单分享到
推荐
内容简介 · · · · · · Should western beauty practices, ranging from lipstick to labiaplasty, be included within the United Nations understandings of harmful traditional/cultural practices? By examining the role of common beauty practices in damaging the health of women, creating sexual difference, and enforcing female deference, this book argues that they should. In the 1970s feminists criticized pervasive beauty regimes such as dieting and depilation, but some 'new' feminists argue that beauty practices are no longer oppressive now that women can 'choose' them. However,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the brutality of western beauty practices seems to have become much more severe, requiring the breaking of skin, spilling of blood and rearrangement or amputation of body parts. Beauty and Misogyny seeks to make sense of why beauty practices are not only just as persistent, but in many ways more extreme. It examines the pervasive use of makeup, the misogyny of fashion and high-heeled shoes, and looks at the role of pornography in the creation of increasingly popular beauty practices such as breast implants, genital waxing and surgical alteration of the labia. It looks at the cosmetic surgery and body piercing/cutting industries as being forms of self-mutilation by proxy, in which the surgeons and piercers serve as proxies to harm women's bodies, and concludes by considering how a culture of resistance to these practices can be created. This essential work will appeal to students and teachers of feminist psychology, gender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 and feminist sociology at both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levels, and to anyone with an interest in feminism, women and beauty, and women's health.
投诉 Beauty and Misogyny的创作者 · · · · · · Sheila Jeffreys Sheila Jeffreys 作者
原文摘录 · · · · · · ( 全部 ) Postmodern thinking rejects the notion that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a ruling class which can create dominant ideas. (查看原文) Clytemnestra 4 回复 2022-08-25 18:33:55 The effect of the cultural turn on feminist ideas about beauty is three-fold. Women are seen as having choice and agency in relation to beautypractices, or even being empowered by them. Women are represented as having the power to "play"*with beauty practices because instead of beingoppressive they can now be reinterpreted as fun. *酷儿理论家对Judith Butler曲解。 (查看原文)
曹难搞 2022-10-26 18:13:38 陕西 Beauty is a trap to women. 女人被禁锢被裹挟着戴着脚链在指压板上跳舞,天真地以为这是自由。 无论多么钻心刻骨的痛苦,在男人眼里都是取悦自己的春药。 翻译的过程几次都因为愤怒或难过不得不停下来,很难想象作者究竟是如何忍着不适去查阅资料的。
15 有用月小兰 2024-02-04 21:05:54 上海 在父权逻辑下,“服美役”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是女性生物学中固有的,反对的女性会引发愤怒、嘲讽。 在父权逻辑下,“美役”具有自然的道德性,不遵守的女性会被视为放荡、不光彩,对社会结构构成威胁。 这种逻辑匪夷所思。一个人,若将父权逻辑理性奉为圭臬,认为男性代表了理性,ta的话还有多少可信度呢?
7 有用Clytemnestra 2022-08-25 14:46:42 浙江 ①70sRF美批评涌现,Andrea Dworkin(男女角色分化的主要基础),Sandra Bartky(性客体化,性功能/肉体与其余人格的分离)。80s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90sLF宣扬agency、choice、empowerment(后现代主义接管左翼思想的体现)→女性沦为“知识渊博”的消费者。②sexual difference/deference(femininity-subordination+性刺激)。③色情业(联合时尚、娱乐、广告业)推动beauty practices,面纱、化妆对应贞女-妓女的二元论,口红、裹脚、高跟鞋源自卖淫、植根性虐。 LF的所谓自愿选择,不是自由的标志而是对压迫的和解;自然说掩盖政治对美的建构;愉悦的背后是焦虑,而对美的热情正是意识形态运作所需的。 (收起)
0 有用Momo 2023-03-10 18:16:25 吉林 masochism,alienation,self-mutilation,cutting up women.经常阅读到身体出现疼痛幻觉
4 有用a-verve 2023-02-23 00:08:47 荷兰 自由人们醒醒吧
更多短评 30 条
我要写书评 Beauty and Misogyny的书评 · · · · · · ( 全部 6 条 ) 热门 最新 好友 只看本版本的评论 观苔 2022-12-30 14:42:00 男权社会:施虐与受虐 本文为对此书的读书笔记,选取本书中的几个主要论点并延伸。
一、男权社会的基础:性别
性是生物学因素,但是性别差异是社会的基础和要求,是文化的建构。“男性与女性两种性别的想法源于男性主导文化的需要,通过将婴儿在出生时归入这两种身份类别之一,能够识别男性统治阶级和女性从属阶级的成员。然后,男性主导和女性从属的性别被强加给那些占据适当地位类别的人。”女人的“不同”是以男人作为参照物,就是波伏娃所说的他者。也如恩格斯所说,统治阶级以性别分工的形式掩盖了性别压制的政治事实,从而占据女性的生育和生产。父权社会的异性恋、婚姻都是一种社会制度,是不断加固其统治地位、社会结构稳定的措施,是对女性是否“可用”的区分。另外,虽然社会划分男和女两种性别,但是女性包括女人和她的身体。在男权社会下,女性具有一种身份认定障碍,正如女性对男性来说是他者一样,女性的身体对于她来说也是永恒的他者。
二、男权社会的方式:施虐与受虐
(一)施虐
在男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一种规训方式是施虐,可以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显性的方式就是使用暴力和强制手段规训和惩罚女性,如对于妇女各项权利的剥夺,规定妇女的着装等,还有女性需要遭受的身体与语言暴力,如强奸、性骚扰、家庭暴力等。这种方式在男权社会中占少数,更多的是对女性的隐性施虐,前者是容易辨认的、直接的,后者则是有多幅面孔的、难以察觉的,通过文化或传统的方式进行,主要包括“美”与“爱”两种方式。
“美”是政治建构的,并包含种族、阶级和性别偏见,可以等同于“女性气质”。“文化对身体的控制是从属社会群体的行为,人类被训练和期望使用他们的身体的方式源于他们在权力等级中的位置。”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就如同当权者和下属的关系,并通过“女性气质”进一步强化。男性给女性灌输天然爱美的思想,并且通过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营造“追求更美”的社会氛围,使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感到自卑,沉浸于美化实践,过度关注自己的外表。女性进一步将父权的要求内化,把自己物化成审美的客体和取悦男性的性客体。美化实践包括化妆、着装、整容手术、切割手术,从口红、紧身胸衣到植入手术、切割手术没有质的不同,只有量的差异。然而美的受益者却是男性,他们感受自己的男性气质并且因为女性的痛苦得到满足。女性不做美化实践的“不自信”正暴露了男权的压迫,本质还是制造差异,制造“女性气质”的问题。着装的差异除了区分性别,还有激发男性性本能和“男性气质”的再确认的功能,使男性获得生理和心理的满足。因此,所谓“女性气质”是从属阶级为了表明对统治阶级的尊重而作出的行为。
第二种方式是“爱”,在本书中没有提及。这里的”爱“建立在异性恋的基础上,异性恋是一种政治制度,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男权社会以男性与女性相互吸引作为社会惯例,并用婚姻固化”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位。男权为了建立婚姻戴上的最温情的面纱就是“爱”,用广告或者各种作品来建立起女性被爱的需要,使进入家庭的女性可以”正当地“被剥削,获得了她的生产和生育能力。婚后的女性转向一个“母亲”的角色,这就是男权对女性的二元划分的一极。母亲这个角色如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所说,一种与“抹大拉的玛丽亚”相对的“圣母玛利亚”,代表着纯洁、贞洁、神圣。男权用“伟大”“奉献”“牺牲”等字眼紧紧套住女人,从而使她母亲的角色完全压过作为个体的存在。
(二)受虐
男权社会的第二种对女性的规训方式是受虐,也包括显性和隐性两种。显性的受虐如书里提及的“异装癖”和“变性人”。这里的受虐不是男性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什么伤害,而且男性通过为自己增加“女性气质”来“自我降级”,使自己带有性魅力,或者满足自己被掌控的受虐癖好。然而他们的妻子却仍要满足他们的性幻想,承担多种服务。因此,从易装或者易性男性中可以得出“美”没有生物学的基础,并揭示了女性气质的实质——性玩具。这种行为进一步固化了男女的性别差异,也体现出男性甚至有成为女人的权利,与女权追求的“消除性别”背道而驰。
隐性的受虐主要通过色情产业和时尚产业的密切结合,使展现女性魅力的卖淫式服装大为流行。“时尚鼓吹自己是自由精神的代言人。无论时尚发生什么变化,女性和男性的穿着总是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使女性的性别等级得以与男性区分开来,并且在最近几十年中,将整整一半的人类变成了玩具,以在另一半中制造性兴奋。”男同性恋设计师将施虐和受虐的SM纳入时装,表达了他们对女性的厌恶和对“女性气质”的矛盾心理。色情与时尚的联手共同打造性的神话,使得裸体女性变成习惯,这切合对女性的二元划分的另一极——妓女。时尚将“性魅力”包装成女性的武器、力量和征服男性的工具,以此种方式为女性“赋权”。实质上是帮助了男性主流文化中的卖淫正常化,满足了男性的恋物癖和受虐欲望,却对女性造成了诸多伤害,比如对于体毛的仇恨、阴唇焦虑等等。设计师鼓励“大胆穿衣”,然而真正如此穿着的女性却会被骚扰,男权把女性限制在对所谓“穿衣自由”的抗争上,女性却没发现二者是同质的,美和暴力。伊斯兰妇女被迫穿罩衫和面纱早已昭示了男性对女性的看法:从头发丝到脚趾头每一处都是性的象征,女性是一个性器。在穿衣这个圈子里挣扎毫无意义,我们需要跳出来。
“施虐受虐本身是表现性别权力差异的最极端和最令人兴奋的方式。”不论是施虐受虐,都是男性的主体性,并不代表权力的让渡。“在一个女性无法获得合理薪酬或晋升、暴力和骚扰盛行的世界里,穿着性感似乎是获得某种权力的一种方式,但只有极少数人,如麦当娜,能够做到这一点赚大钱并从中获得社会影响力。”除此之外,生活在男性暴力社会中女性的常反应为一种社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促使被胁迫者关心和支持胁迫者的利益。如波伏娃所说主动与男性连接从而获得权力和利益。由此,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女性都没有“选择”一说。并且男性以“执行者是女性”从而导致女性群体的自我仇恨与分裂。
三、男权社会的帮凶: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是男权社会的帮凶,他们构建所谓的女性身体的”缺陷“和虚假的完美形象,促进女性为自己的容貌和身体消费。美容产业、医疗产业、色情产业环环相扣,他们宣称“美”为自由和独立的标志,是一种人权的要求。男权和资本主义不分你我,在庞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面前相互勾结,不断固化社会结构。(书中大量探讨,上文中穿插涉及,不系统展开。)
四、总结
男权社会区分性别来确定主体和客体,也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因此性别解放是一种阶级斗争。男性不论是采用施虐和受虐的方式,女性都没有所谓“选择”的权利。我们和穆斯林妇女也没有质的差异,只有受压迫方式不同。他们的男权是直接的、暴力的,明确宣布女性为男性的附属物品,而更多的父权是间接的、隐身的,从社会传统与文化入手,再佐之暴力。“自由、选择、自主性、自我,这些都是我们文化中强有力的词语,是值得称道的词语。但它们也是在许多人的经验中越来越空洞的话语"。向下的自由不是自由,我们应该停止一切美容实践,停止把自己物化为审美景观,停止把自己当成性客体,反思自己,用真正的行动去获得地位、获得权力、获得财富、改变社会。
余论
此书中虽没有涉及多元性取向的社会问题(LGBTQ+),但在b站up主“未明子”的视频“男权主义必然失败:‘只有一种性别存在’——性多元主义与女性主义的联合之路”中提及,不论是传统的一元性取向还是被西方国家接受的多元性取向社会,仍然都是两极的,只有痛苦和享乐两极,也就是施虐和受虐两种方式。他们仍然遵循男权的逻辑思维,并且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只不过可以在更多的已划分的社会角色中对号入座。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消除性别和被设定的性取向,打破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进行永不妥协的自我探索。
投诉 来自豆瓣App 有用 19 没用 0有关键情节透露 19 2回应收起 MC Shady Diva 2022-10-17 15:58:22 【翻译/备份】第二章 有害的文化习俗(cultural practices)和西方文化 我在此论证,西方文化中的美容行为(beauty practices)应该被理解为有害的文化习俗(cultural practices)。西方的美容行为,如化妆和隆胸手术,对妇女有不同程度的伤害。 例如,与化妆相比,切除身体部位的整容手术与女性割礼(译者注:出于传统或宗教原因切割女孩或妇女的部分外性器官的做法)明显更类似。然而,本章节论证,从口红到侵入性整容手术这一系列的西方美容行为,都符合联合国对有害文化习俗的理解标准,尽管它们在影响的极端程度上可能有所不同。有害文化/传统习俗的概念,源于联合国对识别并消除对妇女和儿童伤害类型上的关注,而这些伤害类型并不容易被纳入人权框架 (UN, 1995)。它在国际人权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但仅限于非西方文化中的女性割礼等做法。然而,对于相当类似的做法,如在西方国家为了将人们纳入性别刻板印象的范畴而切割生殖器的做法,却不承认其有害。事实上,西方会有一种产生 "习俗"的 "文化 "这种想法很可能看上去很陌生。 在西方,有害的做法通常被粉饰为来自消费者的 "选择"、来自"科学 "和 "医学 ",或 "时尚";这也就是所谓市场规律。文化可能被看作是存在于非西方的反动(reactionary )的东西。西方有的则是科学和市场。在这一章中,我论证了西方男性主导的文化确实产生了对女性有害的做法,包括美容行为。
在过去十年中,一种特别残酷的西方美容行为——阴唇整形术,在美容外科医生中越来越受欢迎。在互联网上搜索 "阴唇整形"一词,发现了2200个网站,其中大部分是提供这种手术的美国整容外科医生。一名阴唇整形术的外科医生将这种手术描述为“一种缩小和/或重塑小阴唇的外科手术”(LabiaplastySurgeon.com, 2002)。 这些网站将这种做法常规地列在其他提供的手术中,这些手术包括了切开女性的身体以满足男性的欲望。同样在西方国家,"变性 "手术的实施,即对男性和女性进行阉割,乳房、阴茎、子宫被切除或建造,也常常是由同一批外科医生进行的。但这些做法并不被理解为明显有害的,也不作为一种反动文化的证据。例如,变性外科阉割术被从中获利的医学界认为是对 "性别焦虑症 "这种能够致残的病况的治疗,而不是对那些不符合某种性别类别的人手术转移到另一种性别类别的文化要求 (Rottnek, 1999)。
有害文化习俗的概念有助于分析西方以及非西方的此类习俗做法。联合国术语中的有害文化或传统习俗被定性为:对妇女和女孩的健康有害;产生于两性之间的物质力量差异;为男性的利益服务;创造了损害妇女和女孩机会的男子气概和女性气质的刻板观念;被传统正名。这个定义很符合西方的美容行为,如整容手术。这一概念,使这种妇女活生生成为焦点、并沦为评价对象,而不是被视为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甚至是进步的男性统治文化成为可能。
有害的文化习俗
联合国关于有害文化/传统习俗的概念旨在发现文化上被纵容的、形式上对妇女有暴力和歧视的做法。这一概念被庄严载入非常重要并唯一的 "妇女 "公约中——《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CEDAW; UN, 1979)。《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部分第二条(f)声明《公约》缔约各国将“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修改或废除构成对妇女歧视的现行法律、规章、习俗和惯例”(译者注:公约内容翻译均来自官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还强制缔约各国采取措施以便于:
改变男女的社会和文化行为模式,以消除基于性别而分尊卑观念或基于男女定型任务的偏见、习俗和一切其他作法。(UN, 1979, 第一部分第五条(a))
这里的习俗作法的定义很宽泛,足以将美容行为很好地包括在内。美容行为是创造和维持两性之间 "差异 "的主要工具。他们为妇女创造了作为性和美丽物品的定型角色,不得不在化妆、发型、脱毛、乳膏和药水、时尚、肉毒杆菌和整容手术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男人从事本书所述的大多数美容行为,只是为了从受虐狂式的变装中获得性满足。他们不需要为了工作而化妆,也不需要为了取悦主导性别阶层而穿上高跟鞋。事实上,正如我们将在第三章看到的,男人的异装癖给女人带来了相当大的问题,而不是刺激性兴奋。除非我们接受妇女在生物学上被程序设定所以才去进行美容行为,否则需要将之理解为妇女被要求的文化习俗。所有要求一个性别阶级而不是另一个性别阶级的做法,都应该被审查其在维护男性统治中的政治作用。
有害文化/传统习俗的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的几个联合国文件中得到了完善。1995年的一份联合国概况介绍中提供了有害传统习俗的扩展定义:
女性割礼(FGM);强制女性喂养;早婚;阻止妇女控制自己生育的各种禁忌或习俗;营养禁忌和传统生产方式;重男轻女及其对女童地位的影响;杀害女婴;早孕;和嫁妆价格。(UN, 1995, pp. 3±4)
概况介绍中描述的一些做法在西方有类似情况。例如,在男性认为丰满有吸引力的文化中,让女孩为婚姻做准备的强制喂养与西方的美容行为有一些相似之处。将它与它的反面——即饥饿——进行比较是很有启发性的,西方女孩和妇女更有可能为了接近文化上的吸引力标准而参与节食。在西方文化中,女性很可能为了穿上婚纱而限制饮食数周或数月,而不是去增加饮食量。这份概况介绍有效地解释了这种做法如何产生,这也可以解释美容行为的起源。
按照联合国的定义,有害的传统习俗会对妇女和女孩的健康造成损害。女性割礼等做法对健康的破坏性后果是有据可查的(Dorkenoo, 1994)。在西方,有害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可能并不那么迅速得明确或严重。然而,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整容手术的做法,例如西方常见的隆胸手术,对健康造成了损害(Haiken, 1997)。美容做法的心理伤害后果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因为这种做法没有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但它们可能是非常可观的,在构建女性的从属女性气质地位方面扮演了一定角色。
对此类做法对健康的影响的关注产生于西方的一种倾向,即一种希望伤害本身能被轻易测量出来的倾向。对作为平等公民的妇女地位的伤害不太容易衡量,但这可能是所有基于妇女从属地位的文化习俗的一种结果。例如,Ruth Lister关于妇女的公民身份的研究工作论证了,家庭主妇的角色及其伴随的要求,即妇女从事各种形式的无偿劳动,严重损害了妇女的公民身份,并支持了男性的公民身份 (Lister, 1997)。妇女在美容行为上进行的额外劳动,以及这些行为对她们能够占据公共空间、自我感觉和干预公共生活的方式的影响,都可以有效地纳入这一分析中。Nirmal Puwar关于英国女议员经历的研究工作表明,当她们试图在这种极端男性化的文化中生存时,外表上的女性化实践对她们至关重要(Puwar, 2004)。她采访的一位女议员解释说,这些妇女被当作性对象来审视和评论,并且"妇女的性能力一直伴随着她们"(Puwar, 2004, p. 76)。Puwar认为,议员们 "受到了压力,要通过身体着装风格的具象化形式来再现性别差异,因此强调可接受的女性外表形式" (p. 176)。 有一个影响是,她们不断受到议论,但很可能还有更多的影响(此处还未研究),因为她们必须如此明显地成为女性,在寻求在政府中发挥效力的同时,还要戴上展现从属地位的不舒服的耻辱。
概况介绍说,有害的文化习俗是 "社会在妇女和女童上标明的价值的后果。在妇女和女童不能平等地获得教育、财富、健康和就业的环境中,这些做法持续存在。”(UN, 1995, p. 5)。 在西方文化中,对妇女和女童标明的价值与对男性人类的价值明显不同。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可能不再算一个问题,但获得财富和就业的不平等却一直存在。例如,2000/1年,英国女性的每周平均个人总收入为133英镑,而男性则为271英镑(Carvel, 2002)。 妇女和女孩的价值较低,表现在家庭暴力和所有其他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上,表现在色情和其他形式的性产业的存在上。我认为,西方的美容行为源于这种更低的价值。化妆品和高跟鞋、阴唇整形术和隆胸术都是西方对妇女和女孩标明的价值的结果,在那里,妇女的身体被改变和装饰,以表明妇女是为男人的快乐而存在的从属阶层的成员。
概况介绍给出的确认有害文化/传统习俗的其他标准是,它们 "反映了一个社群的成员在通常跨越几代人的时期内所持有的价值观和信仰",并且它们是为了 "男性的利益" (UN, 1995, p. 3)。 美容行为确实反映了关于妇女的长期价值观和信仰,尽管妇女所经受的确切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妇女为了 "美丽 "而改变和装饰自己身体的要求并没有改变,比方说,尽管紧身胸衣(一种强调乳房的塑形女性的工具)可能被乳房植入物取代 (Summers, 2001)。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是,"美 "是女人应该为男人的性兴奋而体现的东西,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是如此。
美容行为可以合理地被理解为是为了男人的利益。尽管西方的女性有时会说,她们选择进行美容行为是为了自己,或者是为了其他女性,不是为了男性,但是男性在好几个方面都会受益。他们获得的好处是,他们优越的性别阶层地位被标示了出来,并且每次看见一个女人时他们都会被提醒他们的优越地位,这会使他们感到满足。他们还获得了被 "美丽 "的女人刺激性欲的好处。这些好处可以归纳为这样的认识:女性被期望成为一种男性的"补充 "和 "赞美 "。女性通过成为 "相反 "和从属的性别来补充男性。女性通过准备努力装饰自己,以获得男性的性兴奋来赞美男性。因此,男人既能感觉到自己是个男人,又能感觉到女人的努力让自己受宠若惊,而且,如果女人穿着高跟鞋的话,还能感觉到为了他们的快乐而忍受的痛苦。那些拒绝美容行为的妇女既不提供补充,也不提供赞美,她们的反抗会遭到占主导地位的性别阶层成员的强烈反感。
概况介绍告诉我们,有害的文化习俗 "一直存在","因为它们没有受到质疑,在实行这些习俗的人眼里有了道德的光环"(UN, 1995, p. 3)。西方的美容行为当然很少受到质疑。它们被理解为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在跨历史和跨文化的情况下被正名是妇女生物学中固有的东西。(Marwick, 1988)。对这些习俗的拒绝带来了愤怒和嘲讽,比如把女权主义者说成是烧胸罩的人,是丑陋的、有多毛腿的,得不到男人的青睐的。西方的美容行为拥有自然的道德性。不遵守这些规定的妇女会被视为 "不听话的(loose)"、名声不好的、不自然的和对社会结构造成威胁的。
联合国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特派调查员Radhika Coomaraswamy解释说,各国试图使其经济现代化的努力,往往使其对侵害妇女权利的有害传统习俗形式维持原样 (Coomaraswamy, 1997)。 在西方,西方人的理解中的所谓"现代 "经济、技术和民主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然而,有争议的、对妇女和女孩有相当大伤害的美容行为却在蓬勃发展,并构成了非常重要的产业基础。现代经济非但没有导致有害行为的减少,反而利用它们来赚取非常可观的利润,如化妆品和时尚。这样一来,现代经济大大增加了消除有害行为的难度。据2003年5月的《经济学人》估计,全球美容业的价值为1600亿美元( The Economist , 2003)。
2002年,Coomaraswamy编写了一份新的有关有害文化习俗的长篇报告。在很大程度上,该报告延续了早期文件中的西方偏见,但西方的美容行为在这里确实得到了一整段的专门介绍。报告说,"在许多社会中,对美的追求往往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妇女。”(Coomaraswamy, 2002, p. 31). 它特别提到了西方的美容行为对瘦的要求。“在21世纪的 "西方 "世界,媒体通过杂志、广告和电视,把瘦削的女性体型作为唯一能被接受的体型这一美丽神话强加给女性”,还有性别歧视的广告。报告称,这种 "不切实际的幻想文化 ""在许多行为中对女性身体造成极大伤害",并特别提到 "针对女性身体每个部位的整容手术","导致了许多妇女的健康问题和并发症"。这一短短提及尽管粗略,但可能表明在Coomaraswamy所说的侵犯 "妇女对身体完整和表达的人权,以及破坏平等和尊严的基本价值 "的做法中需要包括一些西方行为。(2002, p. 3)
然而,在她认定的最严重的类别中,她只包括了非西方的行为。该类别指"包括妇女或女童受到`严重疼痛和折磨'的文化习俗,那些不尊重女性身体完整性的”以及“必须接受最大限度的国际审查和抗议" (Coomaraswamy, 2002, p. 8)。它包括 "女性割礼、荣誉谋杀(译者注:即凶手谋杀家庭成员以达到挽回家族荣誉的目的)、自焚殉夫(译者注:旧时印度教习俗)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残害女性身体的文化习俗"(p. 8)。
报告中描述的一些非西方国家的行为,可以与在西方非常类似的、快速日常化的美容构成之行为,进行有效的比较。例如,我们被告知,"卢旺达和布隆迪的Tutsi族妇女要接受拉长阴唇的做法,目的是让妇女体验到更大的性快感" (Coomaraswamy, 2002, p. 12)。这与西方的阴唇整形术的做法有共同之处。 在阴唇整形术中,美容外科医生切掉小阴唇的一部分以 "美化 "妇女的生殖器。这不是一种可以用传统可以解释或正名的做法,因为它是近代才产生的,但从残害程度、痛苦和潜在的并发症来看,它确实类似于女性割礼,与Tutsi族的习俗形成了惊人的对照。在西方,在阴唇整形外科医生的广告文本中,长阴唇被说成是抑制了性快感并使人难堪。Coomaraswamy从人类尊严来描述传统习俗的危害。这些做法被称为侵犯了妇女的尊严 (Coomaraswamy, 1997)。 妇女的 "尊严 "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人的 "尊严 "则是人权理论和实践的根本。这是一个有用的衡量标准,可以用来衡量西方的美容行为,如阴唇整形术。尽管西方也有与报告中描述的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做法类似的情况(Wynter et al ., 2002),但是它们很可能在联合国文献中被遗漏了。我认为,这是因为西方偏见认为西方的有害文化习俗反映了妇女的选择,而不是通过惩罚的威胁或宗教法令来强制执行的。
西方文化提供 "选择"?
有害的文化习俗被看作存在于妇女没有选择权的文化中。能把"被选择的 "有害传统习俗与强迫性习俗区分开来的这种想法并不符合联合国对这种习俗构成的理解。有害文化习俗的概念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文化可以强制执行,而妇女和女孩不是有自主选择权的人。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西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它所捍卫的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之经济体系,是削弱某种政治批评的强大力量,而这种政治批评承认不平等和压迫是对选择和机会的限制(see Jeffreys, 1997b)。这种意识形态是如此普遍,甚至影响了Radhika Coomaraswamy在其2002年报告中对西方以外的有害行为的讨论。该报告把强制要求妇女穿戴布尔卡罩袍(译者注:存在于伊斯兰文化)等所有包裹性服装的着装规定列为有害的文化习俗。它们是有害的,因为 "它们限制了妇女的行动和她们的表达权",还因为它们对健康有害,"。这种罩袍可能导致哮喘、高血压、听力或视力问题、皮疹、脱发和精神状况的普遍下降'' (Coomaraswamy, 2002, p. 28)。最近出现了另一个健康问题。医生们在《柳叶刀》杂志上写道,佝偻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骨骼因缺乏维生素D而变得脆弱。他们解释说,在中东,"许多母亲患有成人形式的佝偻病,儿童也患有佝偻病",因为妇女被要求遮盖身体,皮肤得不到自然阳光的照射(Lichtarowicz, 2003)。
尽管如此,Coomaraswamy评价道,只有当这种着装规定 在"强加给妇女,而且如果不穿非常繁琐的服装就会受到惩罚 "时,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她们的选择和表达权利显然被剥夺了" (2002, p. 29)。她所采用的选择概念并没有考虑到本章其他地方所讨论的穿戴限制性服装的压力类型,例如在公共场所,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减少骚扰。遮盖物可以减少这种争执,但不代表是自由的,而是对压迫的一种迁就。Coomaraswamy引入 "选择 "的概念是令人担忧的,因为它淡化了有害的文化习俗概念中最有用的一个方面,即在文化期望和习俗充当执行者的情况下这种西方概念的无关性。
甚至备受尊敬的美国女权主义政治哲学家Martha Nussbaum也用这种 "选择 "的论点来区分西方(特别是节食)与西方外的美容行为。Nussbaum认为,诸如女性割礼的做法不应该被视为 "在道德上与美国文化中的节食和塑身做法相提并论" (Nussbaum, 2000, p. 121)。 她认为,女性割礼和节食之间的差异非常大,以至于这样的论点站不住脚。她所做的区分与选择这个议题有关,她认为在西方与节食有关的选择是很普遍的,并且这与这些做法对健康的损害程度有关。她说,女性割礼是 "通过武力进行的,而根据文化构建的美丽形象进行节食则是一种选择,无论说服力有诱人(2000, p. 122)。她认为,女性割礼是不可逆的,而节食不是。她说,女性割礼是在危险和不卫生的条件下进行的,与节食不同,她认为与女性割礼有关的健康问题(可能包括死亡)要严重得多,因此进行比较是不合适的。Nussbaum还说,由于女性割礼通常是在儿童身上进行的,因此同意不是一个问题。她详细介绍了美国和一些非洲国家之间女性识字率的差异,并以此为依据论证非洲妇女没有像美国妇女那样获得选择和同意的机会。她说,女性割礼意味着 "不可逆转地丧失某种性功能的能力",据推测,这比节食带来的损失更大。最后,她认为,女性割礼"与男性统治的习俗有明确的联系",这也意味着她在暗示节食并不是。她还有其他更广泛的论据,认为女性割礼是比美容行为更严重的侵犯妇女权利的行为。她说,美国的女权主义者不成比例地批评了西方的美容行为,而对女性割礼却不太重视,而女权主义者有责任关心西方文化之外的姐妹们的命运,而不是只关心自己。
很难不去同意Nussbaum,也就是西方女权主义者应该关注其他国家的姐妹们的人权。然而,我想说的是,西方女权主义者对其他文化中的有害文化习俗的批评,需要建立在对自己文化中这种习俗的深刻批判之上。Nussbaum关于为什么不该将节食与女性割礼相提并论的论点并不令人信服。西方的节食法对健康造成了持久的损害,特别是极端的饮食失调会导致死亡。例如,2001年《柳叶刀》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研究开始时接受采访的饮食失调患者中,有5人(2%)在5年的跟踪调查中死亡(Ben-Tovim et al ., 2001, p. 1254)。同样,整容手术行为也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正如Elizabeth Haiken在隆胸案中所记录的那样(1997)。阴唇整形术与女性割礼一样,可能导致性功能方面的困难。Nussbaum关于西方妇女有 "选择 "程度的论点可以被看作是揭示了一种西方的偏见,根据这种偏见,西方妇女的优势很大,她们可以 "选择",因此,无论她们被要求参与什么文化习俗,都不像在一些非洲文化中那样严重。自由主义女权思想的一个潜在问题是,西方文化中的权力关系被重塑为简单的 "压力",接受过教育的妇女可以承受 (Jeffreys, 1997b)。
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一些个人主义自由女权主义者甚至也可以找到妇女 "选择 "的证据。其中之一就是西方的阴道瓣(译者注:旧称处女膜)修复手术的行为。阴道瓣修复手术是为了给那些文化要求在新婚之夜出血的妇女创造一个人造的处女膜,以避免新娘和她的家人因失去 "荣誉 "而感到羞耻。对丧失名誉的惩罚可以是 "荣誉谋杀",即妇女被男性家庭成员杀害。从此类文化移民到西方的人,可以从那些给受色情作品影响而认为自己阴唇丑陋的妇女提供阴唇整形术的外科医生那里,获得阴道瓣修复。Sawitri Saharso在其关于21世纪荷兰的阴道瓣修复手术做法的文章中认为,做阴道瓣修复手术的女孩是 "可做选择的道德主体"(Saharso, 2003, p. 20)。她说,女权主义者应该尊重 "其他妇女的选择,即使我们不同意她们的选择。这反过来又意味着,提供阴道瓣修复是一种多元文化和良好女权主义的行为''(p. 21)。这些女孩是 "道德上有能力的行为者,她们确实有选择,并能表达自己的喜好。”(2003, p. 21). 目前,荷兰的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可以免费提供阴道瓣修复,Saharso认为这是一项 "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政策措施,因为它承认文化上知情的折磨"(p. 21)。
Saharso提出的 "选择 "概念是一个非常贫乏的概念,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想把它称为选择。例如,她引用了一位荷兰作家的话,作为她关于女孩 "选择 "阴道瓣修复手术的依据,这位作家认为,可以说她们是在做选择,因为她们确实有其他选择,如离开她们的社区:
她建议,离开社区并不一定意味着沦为一名妓女,因为在荷兰有为离家出走的女孩和妇女提供的庇护所。因此,只有当女孩想留在家庭和社区内,并假定女孩的家庭确实像她预设的那样无情,手术才是唯一可用的解决方案。(quoted in Saharso, 2003, p. 19)
来自移民社区的女孩可能比来自主流文化的女孩更需要家庭和社区的支持。因此,随意假设女孩能够,在被遗弃的情形(她们可能不得不终生躲避因她带来耻辱而寻求报复的家庭)和做手术就使她们能够继续生存之间,做出合理的选择,相当令人惊讶。这些 "选择 "的含义是不平等的,而Saharso建议应将它们视为平等的,这表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中对选择的迷信而导致的奇怪逻辑。
化妆和面纱:相同的区别?
与其说面纱和化妆是妇女受压迫的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如说它们通常被看作是对立的。化妆甚至可以被看作是戴面纱的被解放版本的替代。虽然这显然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伊斯兰文化中受人尊敬的妇女要遮住她们的头和身体,这样男人就不会受到性诱惑,但在西方,妇女的穿着和妆容被期待让男人受到性诱惑,为男人的眼睛创造一场盛宴,可以看出这两者是有联系的。这些期望反映了关于女性在男性统治下的功能之传统二元论。传统上,即使是在西方,妇女也被期望符合处女/妓女的类别。处女在婚前是不被干扰的,直到结婚后,她们在性方面被个体男人所拥有,而妓女的存在一般来说是为了服务男人群体。
遗憾的是,即使是女权主义学者有时也无法从这种二元论中跳出来,想象出一种不属其类的妇女自主生活方式。例如,Lama Abu-Odeh在写到一些穆斯林国家重新采用面纱时说,她作为阿拉伯女权主义者的假设是"阿拉伯妇女应该能够在性方面表达自己,以便她们能够爱、玩、挑逗、调情和兴奋. . 在她们身上,我看到了颠覆和解放的行为''(Abu-Odeh, 1995, p. 527)。 但是,她认为快乐的东西,那些采用面纱的妇女却认为是 "邪恶的"。给妇女选择了让男人性奋而非遮盖的角色,Abu-Odeh陷入了男性统治下的女性的二元论中,即性对象或蒙面者,妓女或修女。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妇女可以在西方和非西方父权文化的定型观念之外,重新发明自己。女性可以获得男性所拥有的特权,即不必担心外表,并能够在公共场合光着脸和头。
面纱和化妆都通常被视为妇女的自愿行为,通过选择来进行并用来表达效果。但同样在这两种情况下,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男性主导地位产生的压力导致了这些行为。例如,贸易历史学家Kathy Peiss认为,美容产品行业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在美国,因为那个时代妇女们开始进入了办公室和其他工作场所等公共世界 (Peiss, 1998)。她认为妇女们把自己当作了她们获得新自由的一个标志。但也有另外一种解释。关于20世纪末穆斯林国家妇女重新采用面纱,女权主义评论家认为,妇女通过遮盖面纱,在公共世界中从事职业和活动时感到更安全、更自由(Abu-Odeh, 1995)。可以说在西方,化妆意味着,在与男性平等的基础上,女性没有自动的、公然大胆冒险的权利。化妆品,就像面纱一样,确保了她们的面部被遮盖,没法粗野地展示她们作为真正和平等的公民,而理论上她们应该那样。化妆品和面纱可能都暴露了女性缺乏权利的问题。
在一些情况下,采用面纱显然是武力和暴力威胁的结果。在伊朗,遮罩是强制性的,由国家强制执行。正如Haleh Afshar所解释的那样,"公开蔑视头巾(hejab)和不戴头巾出现在公共场合,可被处以74下鞭刑。” (Afshar, 1997, p. 319). 没有人认为妇女可以 "选择 "戴面纱,因为执行过程是如此明确和残酷,"被认为遮罩不够的妇女被这些人(真主党the Hezbollahis成员)用刀或枪袭击,能活下来是很幸运的。” (Afshar, 1997, p. 320). 在西方文化中,化妆并不是以如此残酷的方式执行的。
然而,正如Homa Hoodfar所指出的,在不同的国家,甚至在同一个国家,佩戴面纱的原因都可能不同(Hoodfar, 1997)。 在一些情况下,没有明显的武力介入。Lama Abu-Odeh描述了重新采用面纱的情况。她说,在20世纪70年代,妇女 "穿着西方服装在阿拉伯城市的街道上行走:短裙和过膝的连衣裙、高跟鞋,还有夏天用来遮住上臂的袖子。她们的头发通常是暴露在外的,而且还化了妆。” (1995, p. 524).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人,甚至是相同一批妇女,采用了面纱,这里定义为头巾或头罩。Abu-Odeh告诉我们,"她们的身体似乎是(西方价值观、女性身体被 "性化、物化、东西化"的"资本主义 "建设,和女性身体被 "财物化"、"财产化"并被恐吓为家庭(性)荣誉受托者的传统价值观之间的)战场"(p. 524)。采用面纱的妇女是那些因工作或学习而需要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人。她们被男性性骚扰的可能性较小。在她们被骚扰的情况下,如果戴上面纱,她们会觉得更容易去该行为进行反对,因为她们不会被指责为煽动了这种男性的虐待行为。如果被视为无辜的、不应受到这样待遇的受害者,对蒙面的妇女和女孩来说,这样她们更易去感到愤怒,别人也更易为她们感到愤怒。因此,采用面纱可以被看作是,减轻妇女因男性主导地位而遭受的伤害的一种方式。不过,这样的 "选择 "来自于压迫,而不是表明自主权。
Hoodfar解释了在没有残酷惩罚威胁的埃及重新采用面纱的原因。如Hoodfar所说,"重新遮面 "的女性往往是中下阶层、受过大学教育的,和在公共和政府部门工作的白领们。Hoodfar给出的 "重新遮面"的理由并不表明,妇女在做出这一决定时,有合理的替代方案。Hoodfar采访的一位妇女表示,在婚前她对戴面纱的想法有抵触,但在结婚前夕她遇到了来自未来丈夫家庭的巨大压力——反对她出去做教师,而她曾接受过培训,并期待着做教师。她的公婆认为,如果她出去工作,"人们会谈论,她的名声可能会受到质疑。”(Hoodfar, 1997, p. 323)。此外,她还会遭受性骚扰,"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那些不再对妇女有传统尊重的男人可能会骚扰她,当然这也伤害她的自尊心和尊严,以及她丈夫和兄弟的尊严。”(p. 323). 为了除去这些压力,她决定成为一个蒙面的人(muhaggaba)。这让丈夫的家人很高兴。
Hoodfar给出的理由显然与妇女试图去适应男性主导地位有关。她说,面纱显示了妇女对男性统治规则的忠诚,它 "向整个社会、尤其是向丈夫们,响亮而明确地传达出了,佩戴者受到伊斯兰教对其性别角色观念的约束"。(Hoodfar, 1997, p. 323). 戴面纱的妇女可以工作,因为她们在表明她们仍然尊重`传统的价值观和行为'。戴面纱的妇女 "减少了丈夫的不安全感",并向丈夫表明 "作为妻子,她们不是在竞争,而是在与丈夫和谐合作"(p. 324)。作为对所有这些服从信号的交换,面纱 "使妇女处于一种地位,期望并要求其丈夫尊重她们并承认她们的伊斯兰权利"。因此,丈夫可以让妻子保留她们赚的钱,并通过 "尽其所能为家庭提供服务 "来遵守他们的交易(p. 324)。这里给出的任何理由都不能表明,选择这种活动,是因为它给妇女带来除了能减轻男性统治力量之外的满足感。 为了拥有男性所拥有的在公共领域工作的权利,女性必须遮盖,并满足其他刻板印象和对女性从属角色的期望。
另一位接受Hoodfar采访的妇女,在上学后加班不得不乘坐公交车回家时,直接采用了面纱来避免性骚扰,"经常有人对我不好,我晚上回家就会哭"。她决定戴上面纱,以便 "人们知道我是个好女人,而我的处境迫使我在深夜工作。”(1997, p. 325) 寻求一种为了避免在街上被男人攻击的策略,并不是行使自由选择权,而是对压迫的迁就。在埃及会骚扰她的普通男人,可以被看作相当于在伊朗鞭打妇女的真主党(Hezbollahis)平民。Abu-Odeh解释了在阿拉伯城市里,妇女如果不戴面纱而像传统那样暴露的话会受到各种性骚扰:
在街道上和公共汽车上,由于是女性,她们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关注,她们被盯、被吹口哨、被蹭和被掐。男人们经常说"你的乳房真漂亮"或者 "你真漂亮"......她们总是意识到自己被注视着。(Abu-Odeh, 1995, p. 526)
但Abu-Odeh提醒那些认为妇女应该拒绝面纱的女权主义者,这将是 "社会自杀"(1995, p. 529)。穆斯林妇女没有资格公开反对面纱,因为她们会被认为是在为西方辩护。她补充说,伊斯兰教传教士的影响是恢复面纱的另一个原因:"决定戴面纱的妇女通常会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的灌输(来自原教旨主义传教士),她被告知,每个穆斯林妇女都需要遮盖自己的身体,以免勾引男人,这样做是遵从真主(Allah)的旨意 (p. 532)。 这可以很清楚地被看作是宗教灌输,但我们也许有理由质疑,在影响女孩用面纱遮盖自己的这个方面,它是否一定比西方的杂志、时尚及美容文化在让女孩用化妆品遮盖自己方面更有力。
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向非西方国家输出有害行为
在一个据说刚从塔利班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阿富汗(地区),妇女被困在处女/妓女的父权制二元结构中,她们的外表只有两种选择:用布尔卡罩袍遮盖或化妆品。西方的美容行为被视为非常自然、不可避免和对女性有益,以至于它们被当作阿富汗妇女的圣杯。在多年的可怕压迫(她们只被允许穿着全封闭的布尔卡罩袍外出、只能在男人的陪伴下旅行、被剥夺了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并可能在街上被伊斯兰教义的男性监护人殴打而得不到赔偿)之后,能够参与西方的美容行为,特别是脸部和头发的美容,似乎并不是一个迫切的需求。然而,这就是它被推广的方式。
2002年,美国美容业在战争结束后迅速地以急需的美容 "援助 "为名渗透到了阿富汗。这在西方媒体中被表述为一种积极的帮助,而不是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企业。妇女被提供了被化妆品覆盖和性对象化的角色,而不是被以防止她们被男人视为性对象的布尔卡罩袍覆盖。《纽约时报》对此的看法是,尽管经历了20年的战争,"阿富汗妇女仍然坚持她们对美丽的渴望",但 "严重缺乏美容师。而且,她们没有人教、也没有地方可以买到像样的梳子,更不用说从美国普通药妆店的货架上溢出的大量水乳、粉末、眼线笔和腮红了 (Halbfinger, 2002, p. 1)。为了应对这一市场机会,以及展示其公司处理紧急援助(能力)的机会,美国美容行业的 "名人 "们很快就 "赶来救援",领头的是《Vogue》杂志的编辑。这种慷慨的结果是,在阿富汗妇女事务部的大院里开设了一所培训美容从业者的学校,仿佛美容行为确实是妇女的一个重要人权问题,与教育、安全和工作一样。
美国的美容产品制造商自愿提供手册和物品,以帮助创业。《时尚》杂志编辑Anna Wintour说,美容业是 "不可思议的慈善事业",并且美容学校 "不仅帮助阿富汗妇女看起来和感觉更好,还能让她们就业"。但显然,在塔利班控制解除后重新开业的20家美容院的情况造成了一场健康危机,因为条件是如此不卫生和危险。正如一位了解情况的阿富汗难民所报告的那样:
他们使用生锈的剪刀,整个美容院他们只有一把廉价的梳子而且他们不对梳子消毒,没有自来水或Barbisol。他们不对梳子进行消毒,没有自来水或剃须膏,而且还有真实的虱子问题。他们会用木棍和橡皮筋来做烫发。而且没有棉花,所以烫发液会直接滴在客户的脸上。(Halbfinger, 2002, p. 1)
烫发本身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有害的文化习俗,考虑到所涉及的化学品,无论是否流到脸上,它们都是有毒的(Erickson, 2002),但为了资本主义的利益,它已经被转化为一种人权需求。在阿富汗,仅仅翻译现有的美容知识手册是不够的,因为有很多妇女是文盲,所以准备了一个化妆教学的录像课程。
尽管在一场《时尚》杂志的午餐会上,那些争相向美容学校捐款的化妆品公司表示,他们没有竞争销售,但一位高管确实说,"如果美容学校不能在一段时间内创造出对美国化妆品的需求,它就不能算成功。"(Halbfinger, 2002, p. 1). 美国的化妆品公司看到的市场机会不仅仅是在阿富汗。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后,他们迅速进入苏联,为以前被剥夺权利的妇女提供服务,而且他们也正在向中国发展。正如商业历史学家Kathy Peiss所说,即使在 "亚马逊雨林,妇女也在销售雅芳(Avon)、玫琳凯(Mary Kay)和其他美容产品”(Peiss, 2001, p. 20)。但是,像许多参与在阿富汗销售西方美容概念的人一样,Peiss通过强调它为急需就业的妇女提供就业机会,来掩盖这种殖民化活动的压迫性。 正如她所说,"正如一百年前美国的情况一样,在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中,这些 "微型企业 "为一些妇女提供了一个立足点"(Peiss, 2001, p. 20)。
父权制宗教里被遮盖的妇女
尽管西方对妇女性物化的要求,可能与伊斯兰政权要求的遮盖看上去非常不同,但思考西方和伊斯兰文化发展的类似文化基础是很有启发的。妇女蒙头是中东部落的一种文化习俗,最初发源于该地区的一神教,后来传到了世界其他地区。直到最近,西方的一些基督教妇女还被强制要求遮盖头部和身体。20世纪50年代,我在马耳他度过童年,我的父亲被派驻到那里的军队,我记得公共汽车上的告示指示妇女 "穿类似圣母玛丽的衣服"。在欧洲的许多地方,妇女进入教堂仍需盖住头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另一个父权制一神教——犹太教一样,都起源于存在于中东的早期父权制文化。在这些早期文化中,受人尊敬的妇女被要求遮盖起来,如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Gerda Lerner在《父权制的创造》(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中解释说,先于三大宗教的该法典要求不是妓女的妇女遮盖自己,以便她们能够表明她们是个别男人的财产。(Lerner, 1987)。 被卖淫的妇女(通常是奴隶)则不用遮盖,来表示她们是男性群体的财产。
在早期的基督教中,也执行了类似的准则。因此,在《新约》中保罗给哥林多的信中,他提出了遮盖的规矩。他解释说,"每个男人的领袖/头(head)是基督;每个女人的领袖/头(head)是男人;基督的领袖/头(head)是上帝"。而这需要通过蒙住头来证明,所以:
凡祷告或预言的人,都蒙着头,辱没了自己的头/领袖。凡女人露着头祷告或说预言的,都羞辱了她的头/领袖:因为这甚至就像她被剃光头一样。如果妇人不遮盖,也把她剃头:但是如果女人剃光头对她是一种羞耻,那就请她遮盖起来吧。 对于一个男人,因为既是主的形像,又是主的荣耀,实在不应该遮盖他的头: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因为男人不属于女人,女人却属于男人。男人也不是为女人创造的;但女人是为男人创造的。(《哥林多书》Corinthians, 1957, 11: 3±15, p. 181)
女人把头蒙住能表明,她是男人的财产。早期基督教的其他有害做法伴随着着装规范。妇女不能在教堂里发言,尽管她们被允许在回家后向丈夫询问任何不懂的问题,而且她们被要求 "向自己的丈夫顺从,如同向主顺从"(《以弗所书》Ephesians, 1957, 5: 22, p. 200)。
今天比起简单地遮盖妇女,基督教有一个分支走得更远。妇女实际上不予许进入希腊阿托斯山(Mount Athos)的全部境域,该山被希腊东正教的修道院所覆盖,这样可以保护僧侣们不用看到她们。2004年,媒体报道查尔斯王子访问了山上的一座修道院,使这一古老的基督教习俗得到了有影响力的认可(Smith, 2004)。 11世纪以来,该山就禁止女性进入,并以独立的神权共和国的地位,对那些挑战禁令的人进行法律惩罚。自从他的前妻戴安娜去世后,查尔斯曾多次到访,据说他从这个避难所获得了极大的安慰,在这个地方,食堂的读物 "经常以……妇女因夏娃的堕落而造成的罪恶为主题"(Smith, 2004, p. 3)。尽管欧盟试图废除该禁令,但该区域仍然之存在,是对构成父权制基督教基础的仇恨妇女之价值观的有益提醒。
是什么构成了一个有害的文化习俗?
我在本章中提到,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文化和受伊斯兰教影响的文化都对妇女实施了有害的文化习俗。只有决心忽视西方美容行为的政治渊源、功能和后果,才能使人相信,西方文化在允许妇女在外表方面的自由上,显然更加优越。尽管均起源于古代中东的三种父权制宗教文化,一开始都是强制要求妇女遮盖身体,但在西方这种情况已经有了明显改变,即妇女在公共场所进行性徭役。在中东和亚洲的一些地区,遮盖要求已经受到质疑或正在消亡,这一规则又开始被重新强制。最终的结果是,东西方女性外表规则之间显然存在的分歧越来越大。然而,这两套外表规则都要求女性应该 "不同/遵从",都要求女性为男性的性需求服务,要么提供性兴奋,要么隐藏女性的身体,以免男性太兴奋。 在这两种情况下,妇女被要求在公共场所满足男人的需求,并且没有男人所拥有的自由。
因此,与外表有关的有害文化习俗的概念,不应局限于非西方文化。本书所考虑的所有西方美容行为,从化妆到阴唇整形术,都符合辨别有害文化习俗的标准。我认为,它们为两性创造了陈规定型的角色,它们起源于妇女的从属性,并为了男人的利益并被传统所正名。当然,正如我在第6章中对化妆的表达,即使是那些看起来对妇女和女孩的健康只有很小影响的行为,如涂口红,也可能会造成损害。虽然西方的美容行为很少通过实际的身体暴力来执行,但它们都是通过文化来执行的。在西方文化中,不化妆、不给腿部和腋下除毛可能不算"社会自杀",但正如我在化妆那章中所说的,它将影响妇女获得和保持就业的能力,以及她们可能运用到的社会影响力程度。我提到的英国女议员,如果要在立法机构中获得任何正统性,就必须穿着女性化的服装并露出腿部,如果她们让腋毛从上衣中露出来或者腿毛从丝袜中露出来,她们很可能无法生存下去。
然而我知道,整容手术和涂口红等行为造成的损害程度是不一样的。承认西方的美容行为是有害的文化习俗的影响是,各政府将按照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要求,需要调整构成其基础的社会态度。比如一些整容手术的行为,其后果足够严重,对医疗从业人员的法律处罚也很容易实现监管,因此可以通过立法手段来结束这种情况。然而,涂口红和脱毛不该免于被认为有害,并需要补救,尽管法律上可能不合适。它们标志着妇女处于从属地位,清楚地表明了性别角色的陈规定型,即使对妇女健康的影响不是那么严重。因此,致力于结束这种行为的政府角色,或甚至只是减轻应进行这种做法的文化要求的影响,应该是去打击性差异、思想和态度、商业行为的形成,并将这种观念铭刻在西方文化的基石上。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详细研究化妆、高跟鞋和整容手术的行为,以说明它们是如何被实施的,以及它们对妇女的健康,和去获得(西方社会里男性可能认为理所当然的)一般特权的途径的后果是什么:在公共场所素颜出入,去跑步,不把闲暇时光花在保养身体上。读者将能够判断,把这些行为纳入联合国的理解范围是否合适。在下一章中,我将通过异装癖/变性癖,来延伸西方文化中女性美容行为的含义。男性的美容行为表现表明了,这种行为与女性没有生物学上的联系。但不止于此。正如我在这里试图证明的那样,男性行为者从这些行为中获得了性快感,因为他们展示了从属地位。这支持了对美容行为的理解,即为一个下属群体的遵从行为。
投诉 有用 14 没用 0有关键情节透露 14 0回应收起 momo 2024-08-06 13:09:48 脱美役——真正的女性自由第一步 1.五星推荐女性必读书,内容详实、条理清晰、文笔一针见血,阅读沉浸感很强,相信每一位女性都会深有共鸣!
2.化妆、裙子、高跟鞋、整容……本文细致梳理分析了种种"服美役"的现象,本质上是通过强制外表的差异,凸显女性的服从地位,迫使女性承担sexual corvee,服务于男的性需求。服美役符合联合国对于"有害传统/文化做法"的定义: 服美役人为制造sexual difference; 服美役服务于男性的利益; 服美役体现了male dominance,强化了女性subordination的地位; 服美役极大地伤害了女性的身心健康和个体权益……
3.为什么自由人还是坚持捍卫服美役的自由呢?本书也给出了解释: a.自由人花费大量时间、金钱、精力学得"变美"的种种"技能",将自身价值与美役深度绑定,一时之间无法接受这一切根本毫无价值,无法放弃沉没成本 b.自由人不舍得服美役带来的种种服从male dominance的奖励,比如男的对她们的关注 c.自由人坚称服美役是完全自由自主的独立选择,表达了女性追求美的意愿,而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的谎言,仅仅是剪去长发,女性都会面临非议,何谈拥有不服美役的自由? 追求美,为何不断否定自己的身体?追求美,为何自己的本身永远是不够美的?追求美,为何男友是猪头?
4.女性个人可以一步步从自己开始,脱美役,节省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同时立刻感受到真正的自爱;我们自己身体力行,也会带领身边的女性更有勇气与我们同行。没有美役的世界,没有socially constructed gender的世界,对于女性来说,就是自由自在、一身轻松,我们以自己原原本本的身体和面貌骄傲地在这个世界生长立足,专注追求释放自己的全部潜能!
投诉 来自豆瓣App 有用 8 没用 0有关键情节透露 8 0回应收起 曹难搞 2024-06-20 14:30:09 【翻译】第七章 男性的恋足癖、恋物癖与女性残疾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PDF版本:https://pan.quark.cn/s/7154cd2ef0ba
女人穿高跟鞋往往会导致疼痛、残疾、甚至永久的畸形。这种在西方社会中持续存在的、有害的文化习俗需要一些解释。《脚和鞋的性生活》( The Sex Life of the Foot and Shoe) 被誉为男性恋足者的圣经,作者 William Rossi 为了证明这些可能致残的鞋对男人有多重要,在书里说:“男人至今仍无法确定,最伟大的发明究竟是轮胎(wheel)还是高跟鞋(high heel)。“(Rossi, 1989, p. 119) 无论是作者Rossi,时尚设计师,还是那些以妓院的常客、色情作品的消费者为代表的普通男性,这些有恋足癖的男人都很清楚地知道,高跟鞋对女人来说就是一种刑具。正如Rossi所说:"高跟鞋没有实用性,它没有任何功能价值或使用价值。高的鞋跟是一个反自然的装置,它让站立和行走变得不稳定并且让穿着者疲惫。事实上,穿高跟鞋是一系列足病和身体疾病的原因,同时也是一种安全隐患。“(1989, p. 119) 但是对那些男性恋足者来说,这种损伤和痛苦正是他们所迷恋的,也是他们性刺激中最关键的部分。在本章我们会看到详细的说明。我审视了男性对女性畸形和残疾的脚的性兴趣在创造和维持缠足、芭蕾舞和高跟鞋中的起到的作用,并试图去理解男人的性欲对女人生活的影响。
高跟鞋可以在满足男权文化的同时取悦男性。鞋跟是一个很好的区分方式。Rossi 说:“没有任何实际的理由说明为什么男孩和女孩,或者男人和女人,应该穿有明显风格差异的鞋子。唯一的原因是性,这是性别区分的标志。” (1989, p. 17) 当女性只用脚趾困难地在公共场所行走时会被立刻被认出来。然而和女性的孱弱相对的是,男人的两只脚掌都在地上平稳结实地行走。所以说,高跟鞋让女人作为对照补足了男子气概中男人的性角色。女人在登上路沿或从车上下来的时候很容易摔倒并扭伤脚踝,男人不得不在帮助她们的过程中将男子气概淋漓尽致地展示。同时穿高跟鞋也是一种取悦男性的方式。男性通过高跟鞋观赏女性的痛苦,享受女性的依附,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征服的快感,得到了性满足的机会。这是一种非常慷慨的赞美。因此,穿高跟鞋不仅是对男权文化的重要补充,也是取悦男性的有力武器。
恋足癖和恋鞋癖 性学专家认为恋足癖和恋鞋癖是最常见的种类。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性先知”的性学专家Havelock Ellis 认为,男人的脚和鞋是“色情的象征”,恋足癖和恋鞋癖是恋物癖中“最常见”的种类。(Ellis, 1926, p. 15)尽管性学家们很少说明这个事实,但事实上恋物癖主要是男性的行为。有恋物癖的男人更愿意选择女人的某个部位或者服饰的某个部分作为性刺激的焦点,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对这种癖好有很多种解释。有一种说法是,男孩的初次性快感是在意识到身体或衣服的一部分后产生的,因此终身就会将它们和性联系在一起。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很少有女性有恋物癖。另一种说法将恋物癖和阉割的恐惧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用恋物来代替阴茎。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有恋物癖的都是男性,但是只对那些相信心理分析学的人有效。
像其他针对恋物癖的男评论员那样,Ellis用性别不明的语言掩盖了恋物癖几乎都是男性的事实:“甚至对于正常的恋人,脚也是身体最有魅力的部位之一。”(1926, p. 15)女读者会发现自己并不是“正常的恋人”,因为她们并不觉得伴侣的脚是他最有魅力的部位。“然而,在少部分人眼中,脚或鞋是一个女人最性感的部位。”我们可以隐晦地知道Ellis在这里提到的“少部分人”指的是男人(1926, p. 17)。“在一些病态的情况下,女人本身被视为脚或鞋的并不重要的附属物。”(p. 17) Ellis认为,恋物癖是很正常的,因为“恋物癖和其他形式的情欲象征一样,不过是性选择基础上的发展和分离。”(1926, p. 111) 那么根据这个说法,女人一定是不正常的。Ellis认为恋足癖也是正常的,因为“人类喜欢有点弯曲的自然形状”(Rossi, 1989, p. 29)。但相反的是,似乎很少有女人对男人提出,希望他们的脚弯曲的要求。
为了给恋物癖赋予积极的价值,Ellis提出,恋物是一种高级恋人(男人)的行为。因此他这样评价恋物情节:“虽然不敏感的人一般可能根本察觉不到它,但对那些更加警觉并富有想象力的恋人来说,它是激情的高度结晶的一个迷人部分。'' (Ellis, 1926, p. 30) 这暗示着那些不迷恋女人的脚的男人是 “不敏感”的。Ellis对恋物癖的热情可能与他的溲溺癖有关,也就是喜欢听或者看女人排尿。(Jeffreys, 1985/1997) 这看起来很重要,甚至可能取代Ellis和其他性学家告诉我们的正常的性行为——性交。他将溲溺癖纳入色情象征,称它“并非极其罕见”,并归因于像他这样智力水平优越的男性:“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到了。”(Ellis, 1926, p. 59) Ellis补充道:“这是在关于性的正常情感变化范围内的。”尽管他认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溲溺癖都会发生”,但事实上并没有明显的论证支撑这一观点。在男同性恋者的性文化中溲溺癖是非常普遍的,有相当多的色情作品和所谓“水上运动”(water sports)的实践。但在女同性恋者和异性恋女性中却是很不寻常的。
中国的缠足 性学专家、足病医生、像Rossi那样针对恋足癖的作家都曾指出,男人希望女人痛苦地被扭曲的欲望不只出现在西方文化的男性性行为中。这种反常现象在中国持续了一千年,数以百万的女性因此残疾。但是那些记录恋足癖并以此为乐的人认为,这种习俗和西方穿高跟鞋有很多相似之处。大部分西方女性可能意识不到两者之间的联系,但是当她们穿着高跟鞋走路的时候,脚弯曲形成的拱形和缠足永久实现的弧度是相近的。在中国古代,从十一世纪开始,缠足逐渐在上流社会的女性中流行开来。直到十九世纪反对运动开始兴起时,缠足已经遍布社会各个领域了。在女孩六七岁的时候,妈妈开始把她的脚绑起来。用衣服的条带把除了大拇指以外的脚趾全部都捆绑在脚底,并将足弓弯曲成一个尖锐的角度,将脚掌和鞋跟推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肉会开始腐烂,部分会从脚底脱落,有时一个或多个脚趾会掉落。这种痛苦大约会持续一年然后有所减缓,直到两年末双脚坏死就没有痛觉了。”(quoted in Levy, 1966, p. 26) 在这之后,她们的行动就会变得格外困难,不得不减少到在房间里使用放置的工具和膝盖移动。上流社会的女性会把脚一直绑到3寸(10cm),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在某种程度上需要走动,因此脚一般是5寸(16cm)。
探究男人将缠足强加给女人的原因,以及女人将缠足强加给女儿的动机,对于理解现在穿高跟鞋的现象是有指导意义的。一个理由是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建立明确的区别。Levy解释,保守派认为涂胭脂(applyrouge),化妆,穿耳洞,裹脚,“都是使女人符合社会规定的必要行为。女人在每一处目光所及的身体方面都要和男人不同“(1966, p. 31)。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种做法给男人的性刺激。男人声称,由此产生的阴道紧缩的感觉与和处女性交的感觉是一样的(Levy, 1966, p. 34)。女人不得不以微小的步幅行走,但在男人看来这是极具挑逗性的步态,并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这和现代西方男性从高跟鞋中获得的满足是相似的。“男人的眼睛在女人细碎的脚步和臀部的上下移动中获得愉悦。”(Levy, 1966, p. 34 一个娶了缠足女人的中国男人接受了Levy的采访,他关于缠足后步态的吸引力的评论和现在的男性对高跟鞋的看法很像。他批评了缠足结束后中国女性得到的行动自由,“女人现在都有一双大脚。她们在行走的时候又跑又跳,没有给旁观者亲切的感受。”(1966, p. 282) 中国男人从在玩弄残疾的脚的过程中获得了性快感:他们亲吻、吮吸、把脚放在嘴里或阴茎周围,“将西瓜种子和杏仁放在脚趾之间吃掉”,并喝下洗脚水。看女人“剥下因残疾导致的茧子”也能让男人从缠足中获得满足感,这和当代恋足者从高跟鞋导致的伤害中获得的满足是类似的。(Rossi, 1989) 男人强迫女人缠足的另一个动机是限制她们的自由和独立,以此来保护她们的贞洁。缠足起了贞操带的功能。
尽管清楚地知道缠足将带来多少痛苦,妇女依然被迫去包裹女儿的脚。因为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人生除了婚姻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没有一双小脚,就没有男人愿意娶她们。脚越小,女孩作为妻子就越受欢迎。在娼妓中也是一样的。一些被买来的女孩长大后又被卖去做妓女。脚最小的女人需求最多,价格最高。因此,男人之间以婚姻或嫖娼的方式出售、交换女人的交易都使得缠足这一现象一直持续着。
在中国,反对缠足运动始于19世纪,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习俗被完全遗弃。反对缠足的动机是现代和进步的思想以及女性平等。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一代女权主义者认为,缠足包含了西方如今仍然存在的有害的美丽行为,比如女人在芭蕾舞中用脚尖跳舞,穿高跟鞋。Andrea Dworkin称缠足是一个“政治制度”,“反应并延续了女性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上的劣势。”(Dworkin, 1974, p. 96) 它“强化”了女人作为“性对象和母亲”的角色。Dworkin补充道,缠足没有“使男人和女人之间现有的差异正式化”,而是创造了这些差异。因此,“一种性别成为男性是因为让另一种性别变成某种东西,某种其他的东西,某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东西,某种叫做女性的东西。”(1974, p. 107). Dworkin 评论说,缠足这种习俗表明,男人需要女人在痛苦和残疾状态来满足自己。通过女人的残疾,男人“赞美她的痛苦,爱慕她的畸形,彻底夺走她的自由,把她作为性对象拥有,即使他必须毁坏她脚上的骨头来实现。残暴、虐待狂和压迫作为浪漫主义精神的核心实质出现。这种精神是我们所谓文化的根基。''(Dworkin, 1974, p. 112)
一些当代男性恋足者拒绝接受女权主义的论点,并准备为缠足进行辩护。J.J. Leganeur在他的恋足癖网站上告诉我们,缠足和穿高跟鞋很像:“中国的缠足和高跟鞋(以及芭蕾舞鞋)都会给脚色情或性感的感觉。它们都会导致女孩/女人以一种缓慢的、极具挑逗性的步态行走,臀部更加突出,背部更加拱起。”(Leganeur, n.d.a) 他对缠足十分拥护,认为这是两厢情愿的,对男人来说是快乐的,也是女人欲望的结果。
和本书中提到的其他有害的美丽习俗一样,缠足起源于娼妓行业。最初是十一世纪的舞者在皇帝的宫廷中跳舞的时候用到的。这些舞者有可能被卖卖,被迫参与到某种形式的卖淫中。这和日本艺妓的做法是类似的,Fouzia Saeed在《禁忌!红灯区的隐形文化》(Taboo! The Hidden Culture of a Red Light Area) (2001)里描述的巴基斯坦的跳舞女孩也有相似的行为。在巴基斯坦,男顾客会在女孩跳舞时把她们作为性对象挑选,这个时候跳舞的目的就是展示性吸引力。在中国,缠足的习俗从娼妓风靡到其他女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娼妓有害的做法成为了行业外普通女性“美丽”的模板。当代研究缠足的学者Dorothy Ko反思这种做法是如何传播开的:“全国各地的文人在进京赶考的途中会在’快乐屋’(即妓院)和穿着丝绸鞋的迷人妓女面对面玩闹。”(Ko, 2001, p. 42) 有些人会买下女孩带回家当作“家伎或小妾”,Ko 分析:“想象一下正妻看着新得宠的女孩在庭院唱歌跳舞,她被激怒了(或者被迷住了,谁知道呢?),为了包住脚趾并做双新鞋,回到闺房后在储物柜里翻箱倒柜地找出残余的锦缎。”(2001, p. 42)
有趣的是,高跟鞋在美国的起源是类似的。William Rossi说,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一个从法国来的新女孩将高跟鞋带到了新奥尔良的一个妓院。对于顾客来说高跟鞋是如此迷人,以至于妓院的鸨母要求女孩子们在妓院必须穿它。其他妓院纷纷效仿。男顾客们急切地要求他们的妻子买高跟鞋,或者亲自为妻子从巴黎订购。(Rossi, 1989, p. 127) Rossi激动地宣布:“因此,高跟鞋在美国的推出和成功要归功于这个国家早些年前的妓女。”
从后现代文化研究的角度来探究缠足的女权主义学者并没有像女权主义者期待的那样全心全意地谴责缠足这一现象。两位亚洲女学者(Ping, 2000; Ko, 2001) 尤其抛弃了早些女权批评家譬如Andrea Dworkin的见解。Dorothy Ko, 一位研究缠足的主要学者,试图把它从与女性压迫的联系中拯救出来。她声称,缠足不应该普遍地被批评,不能仅仅与压迫女性联系起来:“现代一致的谴责会掩盖习俗的多样性以及意义的不稳定性,而这正是关于缠足唯一突出的事实。”(Ko, 1997a, p. 8) Ko 认为,缠足的女人可能并不会觉得被压迫,“仔细观察后,我们可能会发现之前确信的观念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建立在不加批判地将现代观念强加给过去中国的基础上,而当时的价值观和身体概念与现在是完全不同的。”(1997a, p. 8)她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将缠足视为完全负面的观念来自于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西方殖民者的观点,尽管这似乎与我们所知道的中国近代反缠足运动中出现的全盘批评并不一致。(Ko, 1997b;Levy, 1966) 事实上,Ko认为,缠足的意义取决于旁观者怎么看待。因此,缠足是“一个是令外国人很沮丧的习俗。因为它并能被简化为一个绝对并永恒的核心意义。”(Ko, 1997b, p. 24) 这些殖民者“忙着去解开裹脚布以至于没有揭露’内在的真相’”,因此,“外国人没有意识到缠足的意义总是被构建的,总是由看客的价值观决定的。”她从而采用了文化相对主义者的后现代主义观点,从这种角度看,不可能将任何做法说成是对妇女的压迫,因为有太多的含义,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Ko的书,《步步生莲——缠足的鞋》(Every Step a Lotus. Shoes for Bound Feet)(2001)中有很多巨大的、色彩鲜艳的、闪亮的,缠足者才能穿的鞋的照片。但出版关于缠足,尤其是小鞋的图片有一个问题。这类图书的主要目标客户是男性恋足者,可以视为鼓励他们对于迫害女性的残忍习俗的兴趣。Ko很了解她的恋足癖读者。在书的早些部分,她解释道,尽管是女权批评者的一个完美目标,这个转折(aturn of phrases)并不表明她赞同这种批判,"我们对缠足的反应并不完全是负面的''。(2001, p. 10) 句中的“我们“是谁?是那些博物馆里欣赏鞋子上的刺绣的人,是那些以观看"色情小说和绘画中,男人温柔抚摸爱人脚的场景 "为乐的人,以及她所描述的 "缠足不折不扣的爱好者——即恋足者'' (2001, p. 10)。她解释道,这些恋足者,”甚至发明了让脚以一定弧度弯曲的机器……这种机器很难有大众市场。但几乎没有人会不同意,对漂亮脚的崇拜在许多文化中根深蒂固,包括我们自己的文化。”(Ko, 2001, p. 10) 这些足弓拉伸的机器不仅在恋足癖网站上做广告,在恋足癖的色情作品中也很流行。在这些作品中,妇女用这种机器拉伸她们的足弓,以便她们能够穿上恋足者要求的极端样式的高跟鞋。令人意外的是,她关于缠裹后的脚的描述是“漂亮的”,而不是畸形的。Ko说,她的书的目的是“从妇女文化和物质文化的角度解释缠足在十九世纪之前的起源和传播,呈现出一幅崭新的、更细致的画面。”(Ko, 2001, p. 15) 她陈述道,“’女人是美丽的受害者’或’男对极小的脚的迷恋’等这些通常的解释并不是完全错误,而是过度简化了”。(p. 15) 她说,她不会"否认所涉及的非常真实的痛苦",而是希望通过 "站在妇女的立场上 "来解释这种做法。
正如Ko所说,像其他有害的文化习俗,缠足成为了一种通过妇女强加给年轻女孩的传统:
一旦缠足成为了一种既定的习俗,仅仅“传统”一个光环就是母亲将它传承下去的足够有力的动机。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着亲戚朋友之间的绑脚和换鞋,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仪式。这些仪式——在妇女的房间里瞒着男人——赞美妇女的技能,并成为女性身份的一个焦点。(Ko, 2001, p. 17)
这种由母亲和女儿的代际传播为主要方式的有害习俗的仪式的发展,与今天西方仍在进行的许多习俗的传播方式是相同的,如化妆和高跟鞋。Ko对女人们的的仪式进行了推断:“女儿的第一次缠足是在闺房中进行的,由母亲指导,有时由祖母和阿姨协助:没有男人知道这个仪式过程。" (2001, p. 54) 正如MaryDaly 在《妇产科/生态学》(Gyn/Ecology)(1979)中指出来的,男性的缺席并不意味着男人不是这一习俗的执行者,但确实让他们的责任被掩盖了。Ko将这一仪式与她认为在美国的一个类似仪式进行了比较,"这是一个标志着女孩成年的庄严场合,是她为成为新娘而进行的十年准备的第一步,也是甜蜜十六岁派对的前奏"(Ko, 2001, p. 54)。“甜蜜十六岁”派对不一定是无害的,可能代表着相当野蛮的场合,在这些场合中,女孩们被纳入了西方痛苦的女性形象。但Ko似乎将他们视作无害的,因此她将其和缠足的对比是相当轻松的。她关于女孩的脚是如何穿上三寸金莲鞋的描述传递了一种相当积极向上的方法:“脚的脚尖——大拇指——和鞋尖紧紧地贴合在一起,但是足弓却被舒适地单独留下。有些样式的鞋面很浅,如果没有上面的鞋环和鞋带……鞋就会脱落。”(Ko, 2001, p. 99) 《渴望美丽》(Aching for Beauty)(2000)是另一本关于缠足的当代女性主义学者著作,书中强调了这一习俗的积极方面。作者Wang Ping认为,缠足创造了女性的仪式世界。在过去的一千多年,“中国女人将缠足和写作——两个最有压迫性的父权制习俗,变成了女性文化。她们把缠足变成了女性家族成员、亲戚和朋友之间的纽带。”(Ping, 2000, p. 227) 尽管女人们在高压统治下团结,并组建亲密关系以交换生存技巧可能是必要的,但同时也助长了对压迫的适应,而不是建立妇女机构等值得庆祝的或其他有创造力的举措。
芭蕾舞鞋 思考女性的痛苦和畸形的兴奋可能在于在西方高级文化的象征:芭蕾舞鞋。当芭蕾舞蹈演员用脚尖跳舞时,她们脚的形状就像被捆绑或穿着高跟鞋的脚一样。直到现在,女芭蕾舞演员依然要求穿足尖鞋跳舞并忍受由此带来的痛苦和伤害。似乎男观众从这一重要的西方文化习俗中获得的乐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看到女人用严重受限的脚“优雅地”跳舞,这和中国男人被裹脚女人受限的步态吸引是类似的。对于一些人来说,对疼痛和伤害的了解会增强他们对习俗的热情。十一世纪鼓励舞者用包裹着的脚跳舞的中国皇帝是今天男性芭蕾爱好者的先驱。跳足尖舞的想法应该是起源于十九世纪初的芭蕾舞演员Taglioni。正如舞蹈演员Toni Bentley 所说:“在1822年的首演中,Taglioni将传统芭蕾舞带到了足尖上,并从那时起一直停留在那里,有时是摇摇欲坠的,而且非常痛苦。”(Bentley, 1984, p. 88) 当时的芭蕾舞鞋比现在更不结实,所以痛苦一定是加倍的。即使在今天,这种鞋也完全不适合这样的运动,它没有支撑,是完全虚弱的。观众想看芭蕾舞演员超凡的空灵和优雅,而不是将其作为运动员观赏。因此她不被允许穿上能提供支撑的鞋子。当然,这种鞋也满足了男性恋足者观众。Bentley 解释道,足尖鞋不是用更持久的材料制成的,“因为皮革、橡胶、塑料和合成物是吵闹的、笨拙的、痛苦的,最重要的是,丑陋的。”(1984, p. 88)
鞋子的脆弱性从职业舞者每周需要12双或更多的鞋子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出。(Bentley, 1984) 在穿上这双鞋之前,它必须被塑造出一个形状,因为它对于自己的任务来说是如此不合适:
一双全新的足尖鞋在我们面前以一个有自己意志的敌人呈现,必须加以驯服。在门铰链、锤子、钳子、剪刀、刀片、医用酒精、温水和肌肉力量的综合应用下,再加上对水泥墙的反复敲击,我们真的把一只新鞋从坚硬的不动状态中弯曲、撕裂、拉伸、弄湿,变成一只更安静、更被动的脚的铸件。(Bentley, 1984, p. 8)
Bentley将“芭蕾舞演员的象征性形象”描述为一种通过早期足尖鞋创造的痛苦,她认为这种习俗和缠足很像:“十九世纪的尖头鞋包裹着舞者的脚,就像中国人包裹着他们的小女儿的脚,也像束腰包裹着时尚女性的身体。”(1984, p. 88)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她解释道,鞋只有一个尺码,每双鞋都是“缎面包皮的狭长管状物”,“将脚缠绕并挤压进理想的审美中——一个非人类形状的微型尖头,与进入它的裸脚没有丝毫的相似之处”。尽管今天的鞋更宽一点,有了不同的尺码,但Bentley认为仍然没有很大的改进。
Bentley讲述了她的芭蕾舞团对伦敦制鞋商的一次访问。由于鞋子给女舞者的脚带来的问题,定期访问是必要的。每一个舞者有一个单独的手工艺人(总是男性),以便根据她们脚上的畸形情况来更换鞋子。芭蕾舞引起的脚部变化包括:“跖骨变宽和变硬,各种肿块、疙瘩、鸡眼和老茧都长大了,发生了变化或被去除。有时,由于下脚踝上的肌腱、骨刺或敏感的神经疼痛,鞋跟必须被裁减到几乎没有。”(Bentley, 1984, p. 88) 在2000年的《守卫者》(Guardian)一文中,有些损伤是这样被描述的:“脱下芭蕾舞者的缎面舞鞋,你会发现一地的拇囊炎、水泡、鸡眼和弯曲的脚趾。”(Mackrell, 2002) 舞者Sarah Wildor 说,由于骨头的压力,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脚趾之间长了鸡眼。为了控制鸡眼,她时常进行修剪,但她有"一个非常可怕的软鸡眼,在第四和第五个脚趾之间",其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进行剃骨手术。(Mackrell, 2002) 芭蕾舞者穿着无减震作用的鞋子进行点状工作和跳跃,因此遭受应力性骨折,一位理疗师评价道:“扫描将显示所有潜在的或实际的骨骼应力性骨折的区域。正常人的扫描应该是没有显示的,但古典舞者的扫描通常会显示出严重的应力性骨折。”(Mackrell, 2002) Judith Mackrell 解释,受虐是芭蕾舞者的一部分形象,因此“我们怀着敬畏之心阅读Taglioni为了掌握足尖舞的技巧被父亲训练到晕厥,Anna Pavlova 离开舞台时留下了一串血淋淋的脚印”(2002)。Wildor说,她的脚是“非常痛苦的。在演出过程中疼痛是我脑海里最后考虑的事情,但当我下台后,双脚上的痛苦几乎要杀了我。”(Mackrell, 2002)
恋足者垂涎旧鞋,是因为它们象征着穿着者所承受的痛苦。水泡引起的血迹和脓液让恋足者如此兴奋,以至于“最热情的粉丝渴望得到最喜爱的舞者曾经穿着表演过的、破旧的、血迹斑斑的鞋子”(Mackrell, 2002)。 从Taglioni时代起,这种针对鞋的恋物癖就很明显。据称,她的俄罗斯粉丝将她的舞鞋烹饪并蘸酱汁吃了。(Carter, 2000, p. 81) 这种恋物癖行为类似于中国莲花鞋爱好者用它喝水、闻并品尝。芭蕾舞鞋在恋物者中引起的兴奋,从恋足者的武器库中最极端的"高跟鞋 "被称为 "芭蕾舞鞋 "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在“Jenny”成立的恋物癖网站上有一张这样的照片,妇女穿着鞋的腿和脚,这些鞋的鞋跟呈现出递增的困难程度。它们从2.5英寸(6.35cm)开始,依次写着如下评论:"这没有问题!", "越来越高"、"需要练习 "、"恋物癖穿着",直到8英寸(20cm)的"芭蕾舞 "高跟鞋:"不适合我!”。(Jenny, 2000) 尽管有一个鞋跟在支撑,但站在“芭蕾舞鞋”上,脚基本上是直立着的。行走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大多数恋足者的色情作品中,女人是在斜躺着的状态穿着它的。“Jenny”的网站提供了各种木制或金属制的,可以用来弯曲足弓的足部拉伸机的细节。一个女人正穿着高跟鞋被展览。
男性对高跟鞋的需求 今天西方文化中,男人欣赏高跟鞋的原因在很多方面类似于古代中国男人对缠足的态度。Rossi的书(1989 年)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像他这样的恋足者会要求女人穿高跟鞋,以及他们通过强行妖魔化其他替代选择来实施这一要求。在他看来,女人的鞋可以分为四个类别:性感的,无性的,中性的,异性的。他喜欢的是"性感的",他认为这需要纤细的鞋跟,以使 "脚看起来更小,足弓和脚背更弯曲,腿更长,更有型,臀部和髋部会更扭动。”(Rossi, 1989, p. 90) 鞋子应该是贴紧皮肤的,鞋尖必须是尖头或锥形的,因为"无论方形、圆形或粗壮的鞋尖多么流行,都会使女人的鞋子和脚变得不性感。”(p. 90) 他也认为“半裸”是“性感的鞋”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写道:鞋上的“裸漏”效果在业内称为“鞋舌线”。他们在脚上复制了乳沟:“性感"的鞋子露出了设计师和其他恋物者所谓的 "脚趾沟"。Rossi对“无性的”鞋显然是深恶痛绝的,他描述的方式代表了男权文化对“理智的”鞋的厌恶,正是这种文化迫使女人残疾。他说,"无性的"鞋 "被称为 "实用的 "、"舒适的 "或 "矫形鞋";或在行业里被称为 "老式女跑鞋"。(1989, p. 93) “无性”鞋的外观往往是单调、阴郁、死气沉沉的——低跟或平跟,通常是男式牛津鞋或系带鞋,圆形或略像球形的鞋头……它既没有个性,也没有女性气质。就像从牙齿上切除神经使其失去活力一样。(p. 93)
但Rossi 在发现这些“无性”鞋的过程中变得迷惑。一方面,他说穿着者"大多数是让人没有性欲的女人",她们正好是 "某些宗教召唤的妇女或服务组织的成员,如救世军女兵(Salvation Army lassies) 、门诺派和阿米什人(,Mennonites and Amish);或患有严重足病的女人。然后是那些有性心理抑制或神经问题的妇女,她们用无性鞋作为脚下的贞操带。或者是那些故意将自己的外表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1989, p. 94) 在同一页,他表示“无性的“鞋对穿着者来说有性刺激的作用,因为脚能”完全接触地面“。他引用了一位足科医生的病例研究作为支撑,并在书中其他地方重复了这一论断。女性似乎觉得穿平底鞋更性感,而高跟鞋造成的畸形则抑制了她们的性反应。根据这个逻辑,不是那些穿着”无性鞋”的人,反而是穿高跟鞋的人是”让人失去性欲的女人“。这种混淆是因为Rossi将对性感的认同与男性恋足者对高跟鞋的性反应相提并论,这使他无法认真对待高跟鞋可能对女性的性能力、健康、行动和安全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他唯一具体提到的穿“无性的鞋”的女人叫Eleanor Roosevelt。美国第一夫人Roosevelt是一位坚定的女权主义者,除其他成就外,她将妇女平等纳入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Cook, 1992) Roosevelt还与另一个女人有长期的关系。她的鞋子是由一家矫形鞋制造商专门制作的,因为舒适度很重要。Roosevelt是女性的杰出榜样,不仅仅是在她对合理的鞋子的依恋上。除了为男人提供性刺激,她的生活中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Rossi 对高跟鞋的性感对象一直感到困惑,在书的后部分他断言:“女人在穿高跟鞋的时候有一种受虐的快感。这种受虐癖源于女性通常要忍受的脚部痛苦和变形,以及知道所展示的效果后的一种愉悦的痛苦。”但事实上没有证据支撑。(1989, p. 119) 他们不知道的是,女性的高跟鞋也代表着施虐:"施虐在于高跟鞋本身的生殖崇拜,仿佛女性已经占有了男性的生殖器权力"。(p. 119) 事实上,女人很可能非常想回家脱下高跟鞋,把脚放入一盆愉快的热水中——我曾经在伦敦地铁的高峰时期听到办公室女员工们讨论这种补救措施。Rossi说,高跟鞋给女人带来的伤害,“从女性的角度来说,应该更现实地视为快乐的伤口或性爱的伤疤。”(1989, p. 150) 很显然,他有特权去理解女人的观点,并知道女人心甘情愿通过脚的变形来给予男性和自己快乐。
另一方面,Rossi指出,男性在“观察女人穿高跟鞋”的过程中会得到一种施虐的快乐,这种快乐来自于“看女人穿着既不安全又不舒适的鞋,迫使她们更依赖男性的支持。'' (1989, p. 121) 他所谓的高跟鞋的"情色魔力 "来自于高跟鞋导致的"女性化 "的步态,"女人步幅缩短并以忸怩作态的小碎步行走,暗示着某种程度的无助与束缚。这吸引了许多男人的骑士精神和男子气概。”(p. 121) 此外,男性恋足者,而不是急于脱下高跟鞋的女人,知道脚在高跟鞋中的位置不仅"模拟了性交过程中,特别是在性高潮或射精的时候,脚的反应位置",更导致 "臀部色情地向后推 "。(1989, p. 122) Rossi 声称,关于高跟鞋对女人的作用,许多男人都生活在一个奇异的幻想世界。他们相信 “高跟鞋……会 ‘提升女性生殖区域的性温度’,从而提升她的性欲。当然,这个说法从来没有被证实或者测试过。”(p. 122) 中国男性恋足者也有类似程度和类型的幻想,他们认为缠足可以在阴道内形成层,使得性交更加刺激。这些毫无根据的观念在东西方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
女人穿着高跟鞋不得不以不自然的步态行走所带来的性兴奋,是男人获得最重要的快感之一。Rossi 在这个方面提供了可观的细节并详细地解释:“ 就像女人的行走可以被性化一样,它也可以被去性化(desexed)。行走中脚的位置和状态在‘性等级’上有巨大的差异;也就是说,行走可以是让人有性欲的、厌恶的,或仅仅是中立的。”(Rossi, 1989, p. 140) "发生在双脚远距离分开以拓宽步幅,使行走更安全" 的行走是"无性的"。当女性的走路方式表明她们的两只脚牢牢地踩在地上时,这对男性来说并不性感。当女人用“非常小的脚步”行走时对男人是最刺激的。Rossi告诉我们,这创造了“扭捏的步态”,“和古老的女性束缚概念有关。”(1989, p. 142) 男人总是试图“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限制’他们的女人”,这种想法体现在在他们“强迫”女人“像戴着脚镣那样走路”上。(p. 142) 当看到女人像奴隶戴着镣铐那样走路时,男人会变得兴奋。Rossi解释道,这种行走可以通过紧身短裙和高跟鞋实现:“无论是开衩还是没有开衩的紧身裙都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着装,它的设计和穿着是为了让女性的步幅短小精致。直到十八世纪,新娘的脚链或手铐一直在婚礼上使用,象征着丈夫对妻子的传统束缚。”(1989, p. 142)
高跟鞋通过改变女性的姿态并创造新的轮廓,为男性发明了另一种形式的刺激:"(穿高跟鞋的女人)身体姿态类似撅起的鸽子:胸部和尾巴在高跷上难以平衡。”(Rossi, 1989, p. 147) 有人认为,行走的首要价值在于“锻炼、心灵放松和美学享受”,但Rossi 对这种观点嗤之以鼻。(1989, p. 148) 对于他称之为 "被色情迷住的观众",也就是男人,女性步态的 "主要价值是作为一种色情刺激物"。Rossi说,女性很少走路,相反,"她们表演"。(p. 148)他在这里所说的不是后现代理论的早期版本,即性别是一种表演(Butler, 1993),而是指女人行走的唯一功能是通过她们受伤和受限的步态为男人提供快乐。
最严重的恋足者尤其从女性经历的痛苦中获得真正的快乐。Rossi说,“相当多的男人男人会因为观察女人穿着太紧的鞋走路时明显的痛苦而被激起性欲。有男人承认:’听到女人说穿高跟鞋疼得要死足以让我立刻勃起’”(1989, p. 155)。恋足者对女人的关心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恋足者曾表示,“你可以将全世界女人都在脚踝处砍了,给我脚踝以下的部分就好,其余都给你。” 据Rossi所说,这个言论“也许代表了大部分恋足者”。(1989, p. 172) 这个趣闻让人想起关于十七世纪中国叛军张献忠的缠足的历史。当他占领了两个省后,“砍下女子的脚堆积在一起,称为‘金莲峰’” (Ping, 2000, p. 32) 一个当代的西方恋足者称“……(他)妻子的……大脚趾……几乎是阴茎最好的复制品。恋足者会用脚趾来模拟口交”。(Rossi, 1989, p. 215) 他将妻子身体的一部分变成了假阳具,却不关心这可能会影响她的生活。当她处于困境会有什么感受?对于那些仅靠鞋子就能满足的恋物者,他们从远处将精液射入鞋子。这种鞋太高了以至于不能行走。对于恋足者来说,另一种作用是趴在地上将鞋跟插入自己的肛门。(Finkelstein, 1996)
男恋足网站是获得男性从高跟鞋得到的满足感的一个有用的信息来源。网站似乎对他们的创始人和发起人的性别遮遮掩掩。在J.J. Leganeur 的情况中,没有可识别的名字。在"Jenny "经营的网站上,尽管经常使用女性和男性的名字,"Jenny "和在 "讨论区 "写作的人似乎是简单的顺性别男性。包括Jenny和J.J.在内的许多男人写下他们自己穿高跟鞋的经历,并赞颂生理性别为女性的人穿高跟鞋的情况。他们还撰写了手册,关于如何训练脚去适应穿高跟鞋,以及如何处理练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健康问题。(Leganeur, 2000) 这些作品表面上是针对女性的,但仔细阅读后发现显然是针对男性的。如何穿高跟鞋的手册似乎是男性恋鞋者之间的交易存货,很难想象女人会被这种书吸引。书中写作的语气与出现在男变女的异装网站和其他易装癖网站上的文字相似,都是含糊其辞的。这个细节表明,书写这类材料的男人以及阅读的男人都从中获得了性满足。举例来说, “Jenny”指导读者”找到一双合适高度的鞋子并穿上,在全身镜前侧身站直。对了,最好是在裸体或者只穿内衣内裤的情况下这样做,这会让你更好地欣赏自己的姿态。你会注意到,你的身体重量或重心已经往前移动了。”(Jenny, 2002) 女人似乎并不急于得到这样的建议,但是没有穿高跟鞋长大的男人可能会喜欢它,尤其是怎么走出合适步态的细节指导。“Jenny”特别建议读者买很小的鞋来预防“脚趾垢”。女人恰恰倾向于购买穿着小半码或者一码的鞋子。尽管足病医生极其反对这一趋势,因为它会给女人的脚带来很大的伤害。
高跟鞋穿着者指责鞋子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摇摇晃晃”,即“站立或走路的时候脚踝从一边摇摆到另一边。这个通常是穿着者的错误,因为她的小腿和脚踝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或者技巧。“(Jenny, 2002) Jenny告诉读者,他们本不应该考虑跑步,因为这“很容易让你的脚踝或者鞋跟受伤,甚至是两者都受伤”,但是女人可能需要跑。Jenny给读者推荐例如“穿紧身裙的Stephen”(Stephen at Tight Skirt Page)等其他异装网站。从男性恋足者和恋鞋者视为“女人的”装配物中得到性兴奋的人已经建立了强大的互联网络,通过网络,他们可以点进数以千计的能够满足他们特殊癖好的网站。
恋鞋癖不仅仅是异性恋男人的问题。一个美国的同性恋男人的恋足者和恋鞋者组织,足部联谊会(the Foot Fraternity)有1,000会员。同性恋恋物者对有男子气概的脚和鞋更感兴趣,而不是女性的。对262名小组成员的调查发现,这些人的主要兴趣是干净的脚(60%)、靴子(52%)、鞋子(49%)、运动鞋(47%)和臭袜子(45%)。(Weinberg et al., 1994) 研究者认为,同性恋和异性恋恋物者的兴趣点很相似,都是关于传统的的性别差异。异性恋恋足者通过“高跟鞋,丝袜等”专注于“唤起女性气质”(1994, p. 618) 研究者评论:“因此异性恋和同性恋恋物者都在唤起性别。而文化上构建的性别差异似乎是一般性唤起的基础。”(p. 618) 三分之二的受访者都对性虐恋感兴趣,而男性的鞋“很适合需要强调支配和权力的场景”。(1994, p. 622)
穿高跟鞋对健康的影响 辨别有害的文化习俗最重要的标准是危害妇女和女童的健康。正是这种伤害使人们有理由给这种习俗贴上有害的标签,而在穿高跟鞋的情况下,严重损害健康的证据是很多的。美国矫形外科医师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Orthopaedic Surgeons,AAOS)的全球鞋类调查显示,参与问卷的十分之八的女性认为,她们的脚伤主要是因为高跟鞋。2001年的调查报告发现,59%的女性每天至少穿一小时不舒服的鞋子,77%给出的理由是“工作”或“造型”需要。报告中最常见的疼痛来源是茧子和脚跟痛。(Ananova, 2001) 另一个2001年的报告显示,五分之一的女性承受脚痛是因为她们为了取悦伴侣或雇主而穿高跟鞋。该报告(BBC,2001)发现十分之一的人会“穿不舒服但好看的鞋子”。这个结果说明,尽管女性总是在追求时尚,但只有三分之一的女人喜欢穿高跟鞋。超过80%的人不会仅仅因为减轻脚痛而改变鞋子的种类。六分之一的人认为,一个恰当合适的鞋子是把脚趾挤在一起的。英国研究团队预计,四分之三的女性在60多岁时会有严重的足部问题。领导本项研究的足科医生说:“无论是否属于时尚范畴,只有当健康、舒适的鞋子成为社会的规范时,女性的足部健康才有可能得到改善,”但是他也认为,制造商并不会将足部健康作为优先项。(BBC, 2001)
穿高跟鞋带来的严重的健康问题如拇指囊肿、锤状脚趾,加上小腿肌肉缩短和跟腱损伤,都会让女人不穿这种鞋就无法行走,这使男性恋足者相当满意。J.J. Leganeur 的网站上一大部分详细说明了这些问题。该网站还包括来自其他恋物者的信息,一位通信者写道:"我想读一些关于妇女永久缩短跟腱的真实故事。你能告诉我在哪里可以读到一些吗?“ (Leganeur, n.d.b) 该网站的问题部分是,有些段落描述了最可能遭受这些健康问题的女性:“站街的妓女和BDSM女性顺从者,她们被严重捆绑着。”(Leganeur, n.d.b) BDSM(捆绑和惩戒,施虐狂)的顺从者很可能是由男性伴侣"制造":
(女人)一直或绝大多数时间都穿着高跟鞋。有人最终7*24h不间断地穿上了高跟鞋……高跟鞋也可以在这些女人身上连续锁上几天。有一些用挂锁和鞋锁制成的高跟鞋和靴子是为捆绑目的而出售的。穿着芭蕾舞鞋站立,将小腿肌肉和跟腱压到最短,通常会使肌肉酸痛。制作芭蕾舞鞋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对穿着它的人进行惩罚。如果没有足够的衬垫,穿着芭蕾舞鞋站立甚至会损坏脚趾,造成脚趾出血,导致坏疽,需要截肢或砍掉脚趾。(Leganeur, n.d.b)
在这里,Leganeur对男施虐狂的兴趣提供了有用的见解,用这种鞋子折磨女人的男人对她们的痛苦表现出令人咂舌的满意。这说明,在郊区一些近郊紧闭的房门背后,男人正极其残忍地控制女性“奴隶”。在2004年维多利亚州的一个案件中,一名男子因犯下了许多罪行而被起诉,他把一个女人作为奴隶关在车库里,每隔几天在院子里用冷水冲洗她。该男子被指控强迫女人在他的朋友面前吃他的粪便,裸体倒立,直到摔倒在精心放置的钉子上,……等其他令人痛苦、有辱人格的做法。(Silkstone, 2004)
整形外科医生正在开发一种新的、无疑是可盈利的专业技术,即切割或注射妇女的脚使其看起来更好——特别是当足部因穿高跟鞋而变得畸形时,或使她们的脚能穿上当下流行的高跟鞋。他们提供的手术包括:"缩短脚趾,缩小脚掌,在脂肪垫上注射胶原蛋白或其他物质"。(Surgicenteronline, 2003) 例如一个叫“CoolTouch”的医疗服务提供激光治疗,让女性穿易残的鞋时可以减少一些痛苦。这种治疗方法"通过刺激胶原蛋白的形成,使脚后跟变得更加丰满",因此一位医生这样描述:“`这是一种不影响表皮层,即皮肤顶层的激光,它在下面造成破坏。激光刺激胶原蛋白,刺激下面的皮肤[原文如此];因此你能够穿上鞋子。最大的问题是脚后跟下的烧灼感。”(USA Today, 2000) 治疗需要花费400美元,仅能持续3-6个月。
一个名为"美容外科资源 "(Cosmetic Surgery Resource)的网站为患者提供了详细的外科医生精通的手术特定做法的信息,它告诉女性:“足部整形手术不是玩笑。当凉鞋季节到来时,如果粗糙的脚趾让你不得不躲起来,你就很难享受它。有时,脚部手术除了使你的脚趾更有吸引力外,还可以缓解疼痛。”(Cosmetic Surgery Resource, 2004) 手术很可能是为了去除高跟鞋造成的畸形,如拇指囊肿。网站解释道,术后女人不得不“几天都抬高脚”,因为“并发症包括术后感染,肿胀或流血”。手术的花费是5,000美元。有时拇指囊肿是遗传性的,除非被迫穿入不舒服的鞋子,否则并不一定引起疼痛。它们也很可能是终生穿着高跟鞋的结果,但女性会寻求治疗,以便继续穿着这样的鞋子。
女性可能因为手术本身承受可怕的痛苦和残疾。《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一篇文章描述了一位六十岁语言病理学教授的困境,她接受了手术,以使自己能够在女儿的婚礼上穿上她过去因"撕裂般的疼痛 "而放弃的高跟鞋。她移除了一个拇指囊肿,但随之而来的是:“疼痛蔓延到我的其他脚趾,而且从未消失过……突然之间,我再也不能行走了。比喻地说,我的脚已经坏死了。”(Harris, 2003) 她预计,她将再也不能"赤脚走路或穿专门设计的鞋子"。文章解释,专业的足医术治疗组织,美国足踝矫形学会 (American Orthopaedic Foot and Ankle Society, AOFAS)在2003年12月公布了一个官方声明,谴责了不必要的足部手术。AOFAS警告女性,除了减轻疼痛外,不应出于任何原因对足部进行手术,因为脚的结构非常复杂,病人可能完全丧失行走能力。文章解释,在美国足踝矫形学会的175名参与最近的问卷的会员中,超过一半的医生表示,他们曾经治疗过因足部整形手术而引起问题的病人。英国也在进行足部美容手术,一位英国足部外科医生警告说,如果不疼的话,女性不应该寻求拇指囊肿的治疗:"切除拇指囊肿是一个严重的手术,需要切开骨头。会有巨大痛苦。所以在我看来,如果一开始就不痛,就不要制造更多的痛苦。”(Lane and Duffy, 2004)
然而,从残忍的习俗中获益的足病医生并不悔改。医生Suzanne Levine说,穿高跟鞋对女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可以取悦男性:“让你的普通女人穿上高跟鞋而不是平底鞋,她就会突然在街上听到口哨声……我在尽我所能让女人回到属于她们的鞋子里。”(Harris, 2003) 这样的外科医生不仅仅对拇指囊肿和锤状脚趾等病症进行手术,还对那些被女性本人认为形状不适合穿高跟鞋和凉鞋的,完全普通的脚进行手术。他们提出要纠正的一个问题是"莫顿趾",即第二脚趾突出于大脚趾。显然这是完全自然的,但在穿露趾凉鞋时却被认为是不雅观的,或者在被迫穿上显胖的鞋子时被扣住,因此外科医生切开第二脚趾使其变短。一些女性还希望切掉小拇指,因为她们穿不上时尚的鞋子。女人的脚被切开,以满足男性恋足者和恋鞋者的期望,这与中国的裹脚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手术的残忍之处在于,它会导致严重的终生行走困难,它是二十一世纪早期西方美容方法变得更残忍和更具侵略性的一个例子。
谴责女性 谴责女性是掩盖男权社会运作的一种常见的方式。它通常在针对女性的男性暴力中用得最多——男犯罪学家,男律师经常说,因为受害者穿了错误的衣服,因为妈妈太依赖或太疏远施虐的儿子,因为妻子比施虐的丈夫受过更多教育。(Jeffreys, 1982) 所有这些解释都是为了将公众的注意力从男性罪责转移开,而把责任推给次要的性别阶层。因此,占主导地位的男性阶层仍然是无辜的、不许批评的。即使是在男性权责很清晰的情况下,女性也会被追责。因此,在男性显然没有发挥直接作用的情况下,在美丽习俗方面对女性的指责尤其泛滥也就不足为奇了。
J.J. Leganeur,作为恋足者,采用谴责女性的方式来解释缠足。这"根本不是一个男性统治的问题",(Leganeur, n.d.a )事实上,它完全而且只与妇女有关:
缠足是由女人来实施的。母亲们通常会捆绑女儿的脚……中国的缠足背后都有一个女人的符号。缠足的过程是如此恐怖,解开裹脚布的脚也是如此怪异,任何男人都会被吓死。缠足最有可能是被一位希望她的女儿嫁给皇帝或富豪的母亲发明的。(Leganeur, n.d.a)
激进的女权主义学者Mary Daly解释道,谴责女性让男性的责任消失,是她称为“虐待仪式"的标准之一,这些指责为了男性的满足而跨文化地施加在女性身上。她这样评论缠足:”尽管这个习俗明显是男性为中心的,但礼法奖学金的从业者却允许自己把女人写作发起者,控制者,合法化者。”(Daly, 1979, p. 140) 她说,女人在“虐待仪式”中被当作"象征性的折磨者 "使用,其结果是 "仇恨和不信任 "在女性群体中长期存在。Daly将责任归于女性的男性学术称为 "虐待学者",这种学者在学校教科书、流行杂志和电视节目中向女性宣传,导致 "女性的自我厌恶以及对其他女性的不信任"。(1979, p. 141)
高跟鞋的复兴 作为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回应,高跟鞋在西方时尚中失去了一些重要性。女性当时取得的成果得到了保留。在商店里女人可以买到时尚的,可以穿着走、穿着跑的,“合理的”鞋子。然而,在2002年初,墨尔本的高街鞋店将其绝大部分空间用于销售鞋跟极高、鞋头极尖的鞋——让男性恋足者愉悦但会严重伤害女性的鞋。再一次地,高跟鞋成为了高级时尚,因为恋鞋癖设计师把高跟鞋带回来了。狂热的崇拜者包括时尚摄影师,如Helmut Newton,鞋类设计师ManoloBlahnik和时装设计师Tom Ford。在第五章我曾经引用了Tom Ford将穿高跟鞋的女人和猩猩的对比。当猩猩觉得自己性感的时候就会踮起脚尖走路。
一些男性设计师为振兴极端高跟鞋作为女性时尚的趋势做出了贡献,但最著名的是Manolo Blahnik。他的鞋在电视节目如荒唐阿姨(Absolutely Fabulous),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中得到了宣传。他对恋物癖的兴趣程度从他准备创造不能穿的鞋子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鞋匠制造了一双如此致命的鞋子,以至于它们实际上不会投入生产。”(Tyrell, 2001. p. 5) 这双无法穿戴的鞋有一个"三英寸半(11.67cm)高的钛合金鞋跟,逐渐缩小到只有十分之一英寸(0.25cm)的宽度"。(p. 5)对一个严重的恋足者来说,鞋比女人重要得多。对Blahnik来说,鞋子成为了女人。他描述他的鞋子时,仿佛它们是不同类型的女人:"现在这只……是相当别致的女人。她深深地受Marie Claire和Elle的影响……这是为地中海女孩设计的鞋子……她穿着一件青色的范思哲小礼服。胸部被挤出来…… 她来自斋浦尔……她来到了巴黎 ……一个适合我们时代的水性杨花的女人'' (McDowell, 2000, p. 125)
Blahnik说他需要精心设计鞋跟,不是出于对穿着者的关心,而是因为如果他不正确地制作,女人就会掉下来,鞋子就卖不出去。高跟鞋是如此时尚,以至于对于那些职业依赖代表男人性理想的高跟鞋的女人来说,这双鞋已经成为必需品,比如Madonna。很显然,对于欲望都市中曾因为穿Manolos鞋而被抢劫的Sarah Jessica Parker来说,痛苦和伤害并不重要。她说:“你必须学习怎么穿他的鞋,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但现在我可以飞奔出去叫一辆出租车。我可以全速跑到第六大道(Sixth Avenue)。我把自己的脚完全摧毁了,但我并不在乎。你到底需要你的脚做什么?”(Tyrell, 2001, p. 5) Joan Rivers 说Blahnik的鞋让她感觉自己像一个妓女。Joan描述他的鞋是“荡妇泵”,并补充:“只要你穿上Manolos鞋,你就会自动对每个路过大的男人说’嗨,水手’(Hi, sailor)”(Tyrell, 2001,p. 5)。Blahnik是脚趾沟的狂热爱好者,“脚趾沟的秘密——也鞋的色情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只能露出前两个缝隙”(McDowell, 2000, p. 156)。
尽管J.J. Leganuer 有能力为其辩护,但缠足如果持续到今天,仍有可能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一种有害的文化习俗。它满足了所有的标准:创造了男性和女性的刻板角色,产生于妇女的从属地位,是为了男人的利益,被传统方面是合理的,显然损害了妇女和女童的健康。尽管缠足和穿高跟鞋之间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但即使是那些承认西方文化习俗可以存在的人,也不太可能普遍将穿高跟鞋视为一个有害的文化习俗。这种区别可能取决于同意的问题。显然,与切割女性生殖器一样,对儿童实施的习俗是不能被同意的。六七岁的女孩没有地方可以去,她们依赖于那些残害她们的人。理论上,西方的成年女性可以像Eleanor Roosevelt那样选择舒适的鞋。然而,高跟鞋在女性时尚中持续的重要性反应了Mary Daly称为“虐待社会”的力量(Daly, 1979),这种力量要求女性自残。高跟鞋,像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的其他切割女性身体的做法——隆胸、整容手术、穿孔、切割一样,可以理解为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群体的一种自残形式。(Jeffreys, 2000)
© 本文版权归作者 曹难搞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投诉 有用 3 没用 0 3 0回应收起 曹难搞 2024-06-20 15:00:18 【翻译】结论:一种反抗的文化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PDF版本:https://pan.quark.cn/s/7154cd2ef0ba
我在本书中考察的习俗表明,与非西方文化相比,西方文化在对女性外表的文化要求方面并不 “先进(progressive)”。然而,执法体制可能不那么苛刻,因为女性通常不会因为不遵守规定而在街上或家里被殴打。但就其对女性健康和生活影响的严重性而言,西方的习俗很好地满足了联合国对有害传统/文化习俗的认识标准。尽管,承认这些做法是有害的并不能提供一个直接的解决方案,但它可以帮助清除那些神秘的面纱。这些面纱代表着西方女性被要求对自己的身体所做的事情仅仅是出于时尚,医学建议或个人选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些西方的习俗既是文化构建的,也是有害的。这种认知将促进反抗文化的发展。
西方的美丽习俗符合有害传统/文化习俗的第一条标准,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标准——对妇女和女童的健康是有害的。举例来说,毋庸置疑的是,美容手术习俗正在变得越来越野蛮,引发许多健康问题甚至死亡。美国的电影《前妻俱乐部》的原著小说作家Olivia Goldsmith的死亡表明,财富或社会特权并不能保护女人在服性别役的过程中免受伤害(Kingston, 2004)。在一次让颈部皮肤更紧致的例行手术过程中,她因麻醉剂的不良反应而心脏病发作。美国的社会学家Deborah H. Sullivan (2002) 在她关于美国整容业医学发展的书中解释道,很难确定因手术导致的伤亡数字。然而,她描述了佛罗里达州的《太阳哨兵报》(Sun-Sentinel)的一项研究,该报道统计了不当行为保险索赔、诉讼、验尸记录和报纸的数量,以确定仅在该州就有多少起因整容手术造成的严重死亡和伤害的事件(Sullivan, 2002)。他们发现,截至实验结束,也就是1999年第一季度,在26个月的实验周期内有18例死亡。因此,将这一死伤率与割礼等习俗造成的死伤率相比较,也不无道理。
与割礼(FGM)不同,整容手术并不普遍,但它在形式上变得越来越常见和多样。在二十一世纪,整容手术变得如此常态化,以至于主流电视节目《改头换面》(Extreme Makeover)在黄金时段有一大批忠实观众。在美国版本中,为了让自己的外表在文化上更容易被接受,人们竞相在自己的身体上进行大量严重的外科手术(Moran and Walker, 2004)。目前,澳大利亚版本正在计划之中。其他的美丽习俗也有多种伤害形式,如穿孔、切割、穿高跟鞋。锤状脚趾、拇指外翻、小腿和脚跟受伤是无可争议的伤害。在外出和工作中,女性由于不得不履行日常的美丽习俗并且穿物化女性的服装,可能也会有不容易识别的心理健康问题。
西方的美容习俗不仅产生于女性的从属地位,更应该被视为这种从属地位最公开可见的证据。举例来说,残缺的脚暗示男权的残忍力量。从无数的网站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的美丽习俗是为了男性的利益。男人们在网站上大喊大叫,要求女人实行割礼,并庆祝这给他们带来的性刺激。有些做法具有相当新的野蛮性,甚至是全新的种类,但它们和许多文化中要求女人的那些传统做法一样,都表明了女性的卑微地位。它们明确无误地创造了性别差异,而这正是有害文化习俗的一个重要功能。它们被传统所证明是合理的,就像流行的智慧一样,女人总是希望自己是美丽的,男人被 "美丽 "的女人所吸引是自然的。它们被归咎于女性,而男性在强制执行和强烈要求这些习俗上的角色却被掩盖了。
然而在西方,有害美丽习俗被篆刻在文化中并强加给女性的方法是一个主要的区别。一个事实是,美丽已经被构建成主要产业,为跨国公司赚取大量财富的同时,更是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力量。这些习俗对化妆品、性、时尚、广告和医疗行业的亲睐,给女性抵制甚至消除这些习俗的运动造成了重大障碍。在这些基于商业化有害文化习俗的行业中有如此多的利润,以至于它们构成了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要求女性的痛苦持续存在。例如,美国的整容手术行业每年的估值是80亿美元(Church et al., 2003)。虽然在非西方文化中,有害的习俗是由家庭和社区强制执行的,但这一外力通常并不是市场规模大、利润率高的产业的基础。因此,它们也许更容易识别,也更容易成为目标。在消除有害美丽习俗的运动中,可以利用教育来改变态度。在西方,这些产业具有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因此只有教育是不够的。在宗教和家庭中,强大的资本主义产业的全部力量占据了文化空间。
一个新的自信、主流化、利润越来越高的国际色情业是美丽产业中的一个相对新的参与者。但色情业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即文化的色情化,甚至它对美丽习俗提出了更野蛮、更具侵略性、更残忍的新需求。国际色情业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市场"领域(sector)"。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1998年的一份报告,估计国际色情业市值占一些亚洲国家经济的2-14% (Lim, 1998)。色情卖淫业与娱乐广告业交织在一起,在广告牌、音乐录像和主流电视节目(如《欲望都市》)中创造了穿着色情服装并摆出卖淫姿势的女性形象。这种将女性视作性玩物的文化渗透创造了一种强大的力量,迫使女性履行她们的性别役。是时候醒来了。越来越多"美 "的东西被察觉到其实来源于色情工作者的外观。
在西方,女性应该被赋予权力,拥有上一代人无法想象的机会和选择。然而,这些女人却被衣服和鞋子束缚,被手术残害,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者无法想象的。事实上,许多手术正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女人身上进行的。因为她们发现性别役是没有年龄界限的,这种艰苦的无偿劳动不再有退休年龄了。
美丽习俗越来越残忍的原因可能是,对男人来说,他们很难适应因女人的新机会所带来的两性关系的变化。从色情业的振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男性在适应女性更平等方面的问题。关于性旅游的研究表明,男性认为,他们与明显不平等的无权女性的性接触是对自己在西方失去女性主导权的一种补偿(O'Connell Davidson, 1995)。邮购新娘网站为西方男子提供逆来顺受、低声下气的女性,她们往往来自赤贫普遍存在的俄罗斯、菲律宾等国家。在西方,男性在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主导地位所面临的威胁,可以通过女性在街头和办公室履行有活力的、残忍的性别役来弥补。女人可能有在公共场合行走的权利,有在家庭以外工作的权利,但她们必须通过自己的不适和痛苦来表示对男权的尊重。这种代价太大了。
为了创造一种反抗文化,女性不仅需要认识到美丽习俗对自身健康和地位造成的伤害,而且要准备放弃这些习俗。即使是一些女权主义者也有充分的理由为美丽习俗寻找理由,或淡化其意义。她们可能像大多数女性一样将这些习惯持续了30年或更长时间:日常注意自己的饮食,定期脱毛,涂口红,好像天生就穿"女性化 "的衣服。尽管美丽"仪式"给女性造成了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但它们在生活中的普遍性可能让女性难以意识到这是痛苦的原因。美丽习俗在形式上的伤害性越来越严重:肉毒素取代抗衰老霜、吸脂取代束腰内裤、在脱去腋毛和腿毛的基础上增加了私密处脱毛。
女权主义哲学家Sandra Bartky(1990年)敏感地意识到,为什么一般女性很难批评西方的美丽习俗?她解释说,女人被锁定在对她所谓的"时尚与美丽情结 "的依赖上。因为这种情节向女性逐渐灌输了一种对自身缺陷的认识,就像 "以前的教会,把自己说成是唯一能够通过赎罪来消除它自己产生的罪恶和羞耻的工具"。(Bartky, 1990, p. 41) 它提供了像圣礼一样 的"身体护理仪式"。其结果是,那些被禁锢在“时尚与美丽情节“的女人认为,女权主义不仅威胁着”满足和自尊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攻击着“那些女性赖以减轻身体缺陷的的仪式、过程和组织”。(p. 41)
Bartky解释,女权主义者对美丽习俗的批评“让女性受到了去技能化的威胁,但这正是人们通常所抵制的”(1990, p.77)。女性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金钱去学习如何变美并实践这些美丽。特别是那些觉得自己在践行美丽方面已经做得很好的女性,可能很难接受这一切都是徒劳的,那些过去引以为傲的技能现在没有任何价值。此外,很多女性可能不愿意"放弃遵守美丽规则的回报",譬如男性的关注(p. 77)。如果这些女性对自己和他人的价值的理解是建立在美貌的基础上,那么女权主义可能会威胁到她们的"去性别化,甚至是彻底的毁灭" (p. 77)。Bartky看来,女性很有可能为此争辩,说化妆以及所有女性气质的做法都是她们的个人选择,因为并没有明显的制度要求女性服从于美丽的支配。因此,"女性气质的产生 "似乎是 "完全自愿或天生的" (1990, p. 75)。Bartky说,这种言论导致了一个"所有人都同意的谎言":化妆仅仅是一个巧妙的游戏;女性的第一双高跟鞋是成长过程中天真的一部分,并不等价于现代的缠足”(p. 75)。但Bartky不厌其烦地指出,没有正式的处罚并不意味着女性"完全不需要面对惩罚"。恰恰相反,女性在男权下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制裁”,即“拒绝男性帮助”(1990, p. 76)。这对异性恋女性来说,可能意味着"失去急需的亲密关系";同时对异性恋女性和女同性恋者来说,这意味着"拒绝了体面的生活" (p. 76)。女性可能会发现自己被排斥,无法进入赖以生存的重要社交圈层。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强大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整个西方世界的女性都在提高意识的团体中聚会,审视个人生活中的政治活动,尤其审视让她们憎恨自己身体的西方美容文化,并积极破坏社会上的美丽习俗。Bartky的作品正是诞生于那个时代。作为该运动的一部分,我在1973年放弃了美丽习俗,并得到了我周围成千上万的异性恋女性和女同性恋者的支持,她们也在拒绝这些习俗。我不再把头发染成"有光泽的金色",而是把它剪短。我不再去除腋毛和腿毛。我不再化妆,不再穿高跟鞋。最终,我放弃了短裙。” 尽管政治氛围已经改变,妇女解放运动的力量不再对反抗美丽文化行动提供支持,但我并没有回到这些做法中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政治文化是流氓资本主义的全盛时期。为了支持这一背景,政府放松了对商业的管制,减少了国家的作用,并告诉公民他们是消费者,拥有控制自己生活的选择权。当时流行的政治哲学恰恰反映了这些想法。以Naomi Wolf为代表的自由女权主义告诉女性可以 "选择 "成为强大的人。另一种是在学术界比较流行的版本,即后现代女权主义。它告诉女性可以通过选择拥有权力,并掌控自己命运(Davis, 1995)。Susan Bordo解释说,这两种平行的哲学与当时的消费文化相呼应,如Nike"尽管去做(JustDo It)"的广告。女性往往被强烈阻止关注制约其生活的重要力量。在这一时期,女人很可能说她们化妆是为了"自己 "或 "为了其他女人"。女性谈论到她们可能在践行美丽习俗是不礼貌的,因为在男性至上主义文化中,她们被要求为男性的利益服务,而不是自己的利益。
但时代变了。正如Susan Bordo在1997年表达的那样:“自由。选择。自主。自我。权力。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些都是强有力的词汇,是战斗的词汇。但它们也是在许多人看来变得越来越空洞的词”(p. 57)。在二十一世纪,一场强大的反全球化运动正在挑战公民通过消费"选择 "获得真正的权力的想法,并反对跨国公司以多种形式从压迫和痛苦中获利的权力,当然也席卷了美容行业。正在开始的新时代可能为女性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让她们拒绝美丽习俗,并获得力量来对抗可能面临的消极结果。Susan Bordo在谈到女性拒绝或接受美丽习俗的能力时说:“有意识并负责任的行动意味着理解我们所处的文化,即使它并不需要我们总是`负责任'”(1997, p. 51)。《美丽和厌女》一直试图帮助女性了解西方的美丽文化,并促成这种负责任的行动。Bordo鼓励女性采取行动,她说:"反抗文化规范的姿态即使看似微小,仍可以在我们周围人的生活中打下深深的烙印"(1997, p. 64)。她指出,相反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当女人鼓励她们的女儿去瘦身诊所时,这种"屈服 "的姿态会产生消极影响。当一个新的、支持性的女权运动以拥护这种反抗的姿态出现时,女性将更容易从西方美丽习俗的统治下走出来。但即使没有这一进步,女性仍可以拒绝性别役。女性越是反抗,越是进一步推动这种反抗,其他女性就更容易加入并一起反抗。这些反抗的姿态将有助于创造一个超越美丽的世界。
然而,对美丽习俗的反抗不应该仅仅是个人的责任。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要求各国采取行动,反对有害文化习俗的深层原因——文化态度。要抵制这种态度,就需要国家对那些在创造这种态度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的强大产业进行监管或淘汰。
政府有责任对医疗行业的做法进行监管。因为很明显,自我监管并不能阻止外科医生一步步加深对女性的伤害。正如Deborah Sullivan所言,那些提倡整容手术并从中获利的医学界人士是出于贪婪的动机。他们将医学带回到了十九世纪,那时的庸医为了钱可以故弄玄虚或者坑蒙拐骗,不惜对患者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Sullivan, 2002)。医学界通过整容手术参与了政治/文化监管,无论是为了美丽还是通常称为"变性"的手术。“变性”这一表述实际上很好地表达了这一政治目的。那些在某一个身份类别中不开心的人,被作为国家代理人的医生重新分配到一个新的类别。我曾在其他地方论证过,出于这个原因,“变性”手术必须被理解为对人权的侵犯(Jeffreys 1997a)。它是一种政治性手术,就像西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仇视同性恋者的时候,往往出于政治压迫目的对同性恋者进行脑叶切除手术。例如,人造处女膜的整容手术可以被理解为政治/文化调控,以满足女性地位下降的文化要求。但对西方女性进行的隆胸或阴唇切割手术的政治/文化作用似乎不那么明显,但其动机是相同的。
这可能是因为医学总是成为男权的有力助手,医学活动极有可能逃避批评性的审查和监管。然而,可以要求医学界将其活动限制在创造并维护健康方面,而不是允许其扩大在"时尚与美丽情结“中的作用。当然,监管可能会引起一些讨论:那些因想象中的身体缺陷而引起的精神痛苦,是否有必要通过整容手术缓解?在荷兰已经进行了这样的讨论。在那里,如果认为对精神健康有必要,允许用公费进行隆胸手术(Davis, 1995)。但承认精神痛苦是手术的一个原因会引出一个问题,医学恰恰是最先制造这种痛苦的一个因素。整容手术作为解决方案的推广导致了一种期望,即文化上不被广泛接受的身体特征应该被切除或改变。医学既遵循文化的规定,如修复处女膜或制造丰满的乳房,同时又创造了这些规定。当外科医生准备进行的手术让患者承受的痛苦达到一定程度,如植入乳房、阴唇整形、截肢或"变性 "手术时,有充分的理由通过推行相关法律以阻止他们的行为。
还有一个领域,国家可以通过干预来反对有害文化习俗的深层原因——文化态度。我在本书中一直试图证明,国际卖淫业,特别是以淫秽作品出现的卖淫产业,在过去20年中一直是外科美容手术野蛮生长的强大动力。但它同时也导致了有害的时尚和日常的美容做法。色情产业的正常化导致了一种时尚趋势,它要求年轻女性的衣着越来越像卖淫者的着装,因此可以在在公共空间为男性提供无偿的性刺激。
禁止生产色情作品有充分的理由,这超出了它在创造美丽习俗方面的作用。色情作品的危害包括演员的痛苦经历:投身情色行业的妇女或女孩往往情感上极度疏离甚至依赖吸毒生存,而她们的嘴巴、阴道和肛门则需要被男性的阴茎、手指、手臂插入好几个小时。色情作品本身就是性暴力的一种形式(Jeffreys, 2003)。危害还包括对所有女性地位的负面影响,以及对男女平等关系造成的损害。就美丽而言,色情业和更广泛的国际性产业对女性的面部、乳房、身体、生殖器、衣服和鞋子的外观都提出了当代的文化要求。这对女性的精神、身体健康以及妇女平等的可能性有着深远的影响。关注妇女平等的国家可以选择去监管这些行业,结束女人在色情业和卖淫业中遭受的商业性剥削。瑞典在1999年通过立法惩罚 "购买性服务 "的行为(Ekberg,2004),该法律可以扩大到包括色情制品。
通过惩罚男人的需求可以实现性产业的终结,并有助于创造一种女性可以有尊严地成长的文化。造成目前西方女性自我伤害文化的另一个因素是广告业,它依靠性别歧视向女性销售大量货品,例如美容产品和美丽习俗。女权主义理论家,如Susan Bordo(1993年),已经指出了这个行业对女性造成伤害的力量。文化的改变将需要各国严肃地监管广告,使那些有害的文化习俗的基础不再是《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中提到的态度的最有力的来源。
一个没有有害美丽习俗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在这样的世界里,通过外表创造的性差异将被淘汰。女性不再被要求去履行性别役。女性护肤健身等对身体的护理不再被指向满足男人的性兴趣。她们不再需要服从任何使女性遭受如此多的身体痛苦、金钱消费、精神内耗及时间花费的女性化习俗。脱毛和化妆将变得没有必要。女性可以穿上适合站立、行走、追公交车的鞋子。如果女人选择穿裙子,那么这显然是为了裙子所提供的舒适性,或者因为特定活动适合穿,而不是出于强制性。当穿裙子的人越来越少,女性不再花时间担心坐着时如何摆放腿才合适,不再担心是否有人能看到她们的内裤,不再担心在大风天或弯腰时是否会露出内裤。
事实上,在有害的美丽习俗之外,未来女性可能不必在一天中如此频繁地关注自己的服饰,关心是否露出太多的乳沟或太少的脚趾沟。她们在早晨照镜子时匆匆看一眼,然后就大步走出家门,并不在乎谁在看她们,也不在乎她们看到什么。目前这些都是男性的特权,但女性也可以拥有。素面朝天、双脚稳稳地在地上行走、摆动肩膀和手臂,双手在宽大的口袋里而不是拿着手提包,沉思的时候不会被监管部门的评论、男人的口哨和凝视打扰,所有这些都不应该是男性的特权。事实上,一些女性已经活得好像她们拥有了这种自由,因此帮助其他人创造这种自由。在《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和国际人权界,"尊严 "(dignity)一词被大量使用。值得思考的是,如果“尊严”被应用于女性的外表,应用于服装、鞋子、头发和面部,可能意味着什么。结束有害美丽习俗,为女性提供身体和精神自由是值得争取的。
消除有害美丽习俗需要颠覆性差异的文化。性差异是西方文化的基础,设想一个超越它的世界是具有挑战性的。男性统治可能无法在公开拆解这种差异的迹象中存活。因为对于男权来说,女性的从属性阶层是必须被识别的。正如心理学家Flugel在1930年指出的那样,可识别的性差异对男人来说也是一种乐趣。取消女性在公共场所为男性提供性服务的这一强制性要求,可能会遭到他们极大的反感和抵制。男人会失去一些价值,而女人则会有很大的收获。性别差异不是生物性的,而是显示并维持女性从属地位的文化要求。如果西方的女性地位要有很大的提高,那么男权的堡垒就必须被攻破。
© 本文版权归作者 曹难搞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投诉 有用 2 没用 0 2 0回应收起 噬可可 2023-12-25 16:37:24 学习女权的必读之书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从春天读到冬天,终于赶在2023年底把本书读完了。
作者开门见山地指出,所有令女人有别于男性的操作,都是在强调女性的从属和服从地位。全书围绕所谓“女性气质”标志着女性的从属地位而展开,对变性/跨性别、色情业、时尚业(由被传统男性气质排斥的男同性恋主导)、恋物性癖(恋物癖好发于男性,因为物化女性的缘故)、化妆、整形(自残)中的厌女一一论述。
读了这本书,我剃了寸头,扔了化妆品(没全扔,但也再没用了)、仅买合身舒适耐穿的服饰(男装较女装更多符合),淘汰不必要繁复、紧身或花哨的服饰。
所谓时尚业,一言以蔽之:色情业(物化弱化女性)+消费主义。
本书对于跨性别的论述值得专门拿出来说说,作者提出,性别认同本身就是强化男性地主导地位和女性地从属地位,用丰富的事例和证据表明,男跨女或女跨男并非所谓“生错了身子”,而是追求主导/从属地位,也就是所谓的施虐或受虐性癖。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变性手术中,女跨男多为女同变至异性恋男而非男同,而男跨女多为男同至异性恋女而非女同(有点绕,要多想两秒钟)。
© 本文版权归作者 噬可可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投诉 有用 1 没用 0 1 2回应收起
更多书评 6篇
读书笔记 · · · · · · ( 共 16 篇 ) 我来写笔记 按有用程度 按页码先后 最新笔记 momo 展开 THE “GRIP OF CULTURE ON THE BODY“ momo
关于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女权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主要包括福柯、拉康和德里达,其中福柯的思想对后现代女权主义影响最大。后现代女权主义者大多活跃于学术圈内,但她们也参与女权主义的政治运动。 福柯是一位怀疑主义哲学大师,是怀疑主义哲学传统在20世纪的重要继承人。他主张检验知识变化的实践,而不是用标准的认识论方法去证明独一无二的理性或科学。他对现存一切秩序体制的确定性和稳固性提出了质疑。 后现代主义女权的主... 2022-10-11 19:07:11 1人喜欢
MC Shady Diva 展开 3 TRANSFEMININITY MC Shady Diva (吵架收费标准:¥999/小时)
Feminists who want to dismantle gender, because they see it as a product of male dominance, do not "trans" gender, they simply get over it. Transgender politics are fundamentally conservative, dedicated to retaining the behaviours of the dominant and subordinate classes of male supremacy -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2024-04-23 09:56:18
噬可可 展开 结语 噬可可
In the west women are supposed to be empowered,possessed of opportunities and choices unimaginable only a generation ago,yet these same women are hobbled by clothing and shoes,maimed by surgery inways that the feminist generation of the 1970s could not have imagined. Men's problems in adapting to women'sgreater equality are clear from the invigoration of the sex industry.Research on sex tourism... 2023-12-25 10:23:34
噬可可 展开 自残行为 噬可可
The study found that body decoration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injecting drug use"(Colman2001,p.8),and injecting drug users"had their bodies pierced nine times oftener than the general population".This suggests that those engaging inone form of self-harm are likely to engage in another. 2023-12-24 22:21:18